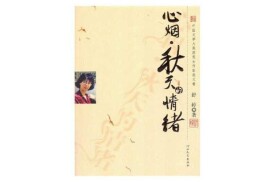心煙
心煙
《心煙》是詩人、散文家舒婷散文集,出版於2006年。本書共分七輯,皆以詩一般語言描繪作者自己的所見所聞。
第一輯
隨筆三則
無題
蝙蝠
回答
你不回頭
笑靨千秋
秋天的情緒
櫻花照
荒園筆記
鞋趣
春深夢淺
你丟了什麼
因為雨的緣故
第二輯
一朵小花
潔白的祝福
在澄澈明凈的天空下
夢入何鄉
心煙
房東與房西們
“神葯”
第三輯
到石碼去
童年紀事
在那顆星子下——記我的中學生時代
迷津不知返
“源源本本”
黑翼
一個人在途中
鷹潭流落記
第四輯
斗酒不過三杯
民食天地
傳家之累
好湯送苦夏
火柴詩人
瓷的遠行
“你給我下海去!”
第五輯
第六輯
第七輯
一
黃潭橋曲曲彎彎長長,約百來米,由兩塊木板左架右搭,從這山到那山。河面寬且急,不深,枯水時,挽起褲管能涉過。橋面離水十多米,往下望,身子不由要趔趄起來。
農人趕牛過河,先在橋頭吆喝一聲:“嗬--”那邊肩夫、牧童都止步等著。若是犟著上橋,到了橋中,挑擔的只好打轉回步。兩牛犄角相抵,轉身轉不成,退也退不了,就等著吃牛肉。
來插隊的知青妹仔只好揪著牛尾巴上橋,那橋因有了負載,便顫悠顫悠得有韻有味。妹仔小臉煞白,兩腿窸窸窣窣,一踏上青石板路,就又哭又笑邁不開腿。
進山出山都是這道橋。
橋這邊是公社,一字排開打鐵鋪、小糧站、飲食店和供銷社,還有醫院。每逢圩日,四鄉都來熱鬧。菜乾,蘿蔔,豬崽,炒毛栗子,應有盡有。最多是地瓜絲,拿米去換,一斤可換八斤。人人口糧不夠吃,就拿來和軍屬、幹部家屬換地瓜絲,多吃一冬。
橋那邊只有一座破祠廟,矮矮地窩在草叢裡,原先敬的不知什麼神,去向不明。紅土路繞過破廟,往深里去,是四十里老林。雖然是山裡和山外的交通要道,斷不了有人挑擔進出,但山高林密,仍鬼祟得很。
墟這邊沿河一溜青石板,媳婦仔和妹仔露著半截茁壯的小腿站在水裡杵衣,邊上捺一撮草木灰,用它去污。男人手團稻草,用力去搓鋤板上的泥巴,嘴巴不閑地和女人調笑。有個妹仔拿袖口抹抹逼出的眼淚,突然“咦”了一聲:“老公祠有煙火啦?”果然是。破廟門篩出些燈光,怯弱得撐不開從老林子摸過來的夜色。
有位老婦人扶著頹牆出來扑打草席子。
有個半癱男人,說不上年紀,鬍子倒是很多。左胳膊向後彆扭著,手掌斷了似的軟軟垂下,右腳板向後撇著,撇著撇著撇到河邊淘米。
小魚兒們都竄過去了,冒一圈水花。敢情不習慣,多少細米白白撒到河裡去。
後來,天色糊得不辨眉目,有個腰板筆直的後生佬,跨出門檻,看也不看這一溜全直起身愣著的山裡人,把一個扁扁的大葫蘆夾在頸窩,吱呀吱呀拉起曲子來。聲音活像二胡,比二胡酸些、軟些,勒人得很。鄉下人說不出所以然,只覺那聲音只往心裡鑽,不受用不受用!
趕緊收拾傢伙,各自散了。
有聲音自茸茸蛛絲的木窗傳出:“咳,飯哩。”那曲子不情願地頓了頓。
橋似乎伸直了。
撲地從蒿草間騰起一隻山雉,扇開長尾巴,姿態萬千地落入蒼茫之中。
後來。再後來。由老婦人(已知她是瞎子)和癱子和拉葫蘆琴(說是小提琴)的後生佬在河邊每晚必有的活動布景再沒有人看。只是有一天,搓泥巴的手有些遲疑,愛笑的媳婦仔煩得把杵衣棒這手遞那手總不得勁,連水也作怪,一改平日活蹦亂跳,有氣無力地打著漩兒。還是妹仔人心活些,嘟嚷了一句:“葫蘆琴啞了!”
二
河面被寂靜遮暗。水聲、松濤、蟲鳴和杵衣的起落,隔著這層寂靜顯得極為遙遠,極為飄忽,無跡可尋。
橋是唯一的真實,清晰可辨。
橋頭屋那糟朽不堪的木門敞開,粗壯了許多的燈苗把一片人影壓在門外的草地上。“灶雞”躲在牆根叫出一圈又一圈漪紋,小風似的一陣涼一陣。
他們在聽故事。
他們中有人讀過函數;有人正收聽外語廣播,偷偷地;有好些人打起架來一副拉茨相。拉茨也是故事中聽來的。
河上的風,扑打得小油燈挫身舞蹈。講故事的後生佬臉被燈影幻出許多怪樣,倒是嗓子好聽。那聲音暖和且有磁性,雖然有點兒低沉,因為那故事本身就很憂傷。
小提琴卧在抹得乾乾淨淨的破香案上。
挨著香案是一隻渾圓白皙的手膀,滑潤得很。燈苗忽兒傾過來,照亮一雙烏黑的大眼睛,活活是黃潭水,多望一眼便會淹死人。燈苗忽兒斜過去,斜映在堅決抿起的嘴唇,殷紅可愛,卻不知為什麼把眼中那一份專註加深為近似蠻橫的意志和慾望,彷彿強調著“要”和“不許”兩重絕然相反的意思。等燈苗拔尖了,所能看到的只有純潔的雙頰,升騰著發育得極為蓬勃的女性的血暈。
燈不倦地繼續各種把戲。
所有人一心一意在故事裡漂泊。
蜈蚣草的葉片上,已有了露水。
墊一塊斷磚坐在河邊的女孩還稱不上姑娘,她的輪廓過於纖細,撕掠草葉的手指蝶翼一般半透明。來這裡那年她還不夠插隊年齡,全體村民一直跟著知青叫她小妹。
只是聽那聲音,不是聽故事。
她愛好一切美的聲音。她吮吸它們就像植物汲取雨水出自不可理喻的本能。聲音之泉閃閃爍爍向她漫過來,將她輕舉又任她沉浮。晶瑩的卵石靜卧其中,星光碎在波濤上。
她想也不想。她知道講故事人在講他自己,他眼前沒有任何聽眾,如果那把琴不算。
橋彎成柔軟的弓。
三
姑娘先離開去嫁人,嫁鄰家婆婆的表侄子,是個著西裝系油條的香港佬。
她的行李很多,送她出山的農民油汗滿面。她親自將一麻包地瓜絲放在橋頭破廟外。為她開啟過的廟門疏遠地森嚴壁壘。
嘟著難看的臉色,她撇撇嘴。手從大衣口袋抽出,捏一板豆餅似的咖啡色糖塊,嚼著走了。印有稀奇古怪字樣的包裝錫紙從橋頭飄到水邊。正和母親撿青菜的小三子撿起玩著,他媽一手打掉它:“這是洋紙錢,呸!送喪。”全公社人懷著又欽佩又同情的期待,目睹那癱子如何用一隻好手配合一隻好腳,挪行二百多里山路,去縣城上告。
終於批下來,說這一家子原不符上山下鄉政策。又有個燒瓦廠的領導目光長遠,看中了那把提琴,要去廠宣傳隊拉二胡。從此,該廠的學唱樣板戲一直美名遠揚。
傳說他走時把提琴塞在廟后老樹的樹洞里。樹洞深不可測,且長年有嗚嗚的聲音,不知是琴,還是野蜂。
傳說他的崇拜者之一幾年後再見他,叫他卻渾然不知地掉頭走了。
說他煙抽得很兇,整個人都被熏黃了。
破廟空了。
最後走的是小妹。她是獨生子女照顧回城,還沒改造好,自然分配不到優等的工作,有一個食雜店等著她去賣糖醋、蚊香和衛生紙什麼的。
她走的時候就帶了兩本日記。一本是紅皮,封面畫著一個姑娘提著一盞光芒四射的燈;另一本也是紅皮,寫著“鬥私批修”. 留下一張小床,是那種統一規格的知青木床。墊著褥子,鋪著整齊雪白的床單,疊成斜三角的被上,垛著繡花枕頭。這一張雅緻潔凈的小床就擺在漆黑的大穀倉中央,村裡妹仔流水似地來參觀。
直到肥碩傲慢的老鼠成精,竟然爬到原先做為梳妝台的肥皂箱上,對著一面鴨蛋形的紅塑料鏡裝模作樣。
四
還是那道橋,彎彎曲曲長長。發桃花水那幾天,橋板被沖走了幾塊,又鋪上新的,像打了補丁似的,橋頓時顯老了。
廟門完全爛了,仍做千攔萬攔狀。木窗上的蛛網愈加精美絕倫。
有塊斷磚本已被坐得光鮮赤紅,吸盡日月精華,又翳了一層苔青。
再也沒有山雉,連愛在褲襠間蓬著尾巴打轉的小松鼠也驚逃遠方。
河這邊已打起一長排地基。老林子向後縮著,恐懼地對向它逼近的村莊發出無聲的、絕望的長嗥。
公路吃到這裡時,橋就要被拆了。
橋不是起點,也不是終點,僅僅是一段過程。小妹曾經在日記上這樣寫過。她和橋互相夢著。
月光下,橋很輕很薄,一柄菅草似的鋒利。
1986年10月20日
澎湖灣的水浸潤了這個才女的身心,她愛自然,愛人生,尤其語言的錘鍊更是常人所不能及。我起初以為這是天分使然,讀後才知她在成名前下的功夫之深、對文學如痴如醉的程度之驚人。她在知青時期過年時一個人在小屋裡廢寢忘食的讀書,窗外老鄉送的乾糧放的成了“盔甲”,自己也沒從書房裡出來過。她說自己在那個時期一天學五個生字,怪不得她的語言都那麼新穎奇崛,如珠璣一般讓人久久玩味不已。她眼睛近視達到了1000多度,怪不得她怎麼看都不是美女一個,但是她是那麼的被繆斯所鍾愛。一首首詩吟出來,一句句真情傳唱在中華大地。
《回答》一文中,她說自己是古老的大地,和俯就她的天空長相廝守,說自己和自然深深的一種默契:花鐘喑啞的鳴唱,嫣紅無比的晚霞。
對自然的熱愛讓她沉醉,讓她如吟詩一般吟唱出醉人的文章。我彷彿看到一古典女子流連在春天野外的綠綠蹊徑上,是李清照?是蘇小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