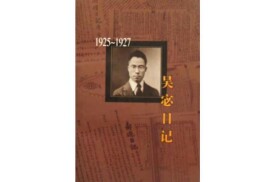吳宓日記
吳宓日記
吳宓(1894-1978),字雨僧,又字雨生。1916年畢業於清華大學。1917年赴美留學,初入弗吉尼亞大學,後轉學哈佛大學。回國后曾與劉伯明等人創辦《學衡》雜誌。從1926年起,在清華大學講學。1906年開始記日記,直至文革後期。

吳宓日記
《吳宓日記》是著名學者吳宓先生數十年學術生涯、個人際遇和在學界的活動與交往記錄,也是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史、教育史的珍貴記錄。
《吳宓日記》共十冊,收錄了吳宓1910年至1948年所寫的日記,1998年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發行。
學昭女士大鑒:奉
摘示
先師日記中道及不才諸節,讀後殊如韓退之之見殷侑,“愧生顏變”,無地自容。先君與先師雅故,不才入清華時,諸承先師知愛。本畢業於美國教會中學,於英美文學淺嘗一二。及聞先師於課程規劃倡“博雅”之說,心眼大開,稍識祈向;今代美國時流所譏DWEMs,正不才宿秉師說,拳拳勿失者也。然不才少不解事,又好諧戲,同學復慫恿之,逞才行小慧,以先師肅穆,故尊而不親。且先師為人誠愨,胸無城府,常以其言情篇什中本事,為同學箋釋之。
眾口流傳,以為談助。余卒業后赴上海為英語教師,溫源寧師亦南遷來滬。渠適成Imperfect Understanding一書,中有專篇論先師者;林語堂先生邀作中文書評,甚賞拙譯書名為《不夠知己》之雅切;溫師遂命余以英語為書評。弄筆取快,不意使先師傷心如此,罪不可逭,真當焚筆硯矣!承命為先師日記作序,本當勉為,而大病以來,心力枯耗。即就摘示各節,一斑窺豹,滴水嘗海。其道人之善,省己之嚴,不才讀中西文家日記不少,大率露才揚己,爭名不讓,雖於友好,亦嘲毀無顧藉;未見有純篤敦厚如此者。於日記文學足以自開生面,不特一代文獻之資而已。
先師大度包容,式好如初;而不才內疚於心,補過無從,惟有愧悔。倘蒙以此書附入日記中,俾見老物尚非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者,頭白門生倘得免乎削籍而標於頭牆之外乎!敬請卓裁,即頌近祉。
錢鍾書敬上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八日
吳宓(1894-1978),1894年(清光緒二十年)生,陝西省涇陽縣人。字雨僧、雨生,筆名餘生,著名西洋文學家,國學大師。國立東南大學文學院教授(1926-1928), 1941年當選教育部部聘教授。
三月二十三日(陰曆二月廿三日) 星期四
晴。風。晨七時四十分,偕葉、王、張諸君回北京。余等沿鐵軌步行至西直門內,始僱人力車乘之。余及張君至三原南館省爹爹大人(時郵人適以父書至),旋出,至東方洋行買物。又赴琉璃廠購墨水、紙、本及郵票等。乃歸三原館,已三點半矣。急赴漢中館,而王君未在。待至三點三刻,仍未歸,余等乃行。出廣安門(即彰儀門),遇一同學系廣東人,亦欲乘火車歸校者也。時鐘已四時,汽笛嗚嗚鳴不已,余等急奔至車站,而始知京張車已於二點鐘時開行。此火車只至西直門即止,乃即乘之,至西直門下車。余等三人遂仍沿鐵軌步行歸校。
今晨爹使羅升來校為余等送物,而余等侵晨即出,羅升直立俟余歸始去。
晚為父作稟,而校中電燈忽全熄滅,疑發電機關有所損失。自習室中黑暗莫睹一物,乃置之翌午始賡續而完其事。晚間又發布本校管理規則(吾陝所來六人俱皆錄取入學。前言榜上無馬君者,誤也)。
三月二十四日(陰曆二月廿四日) 星期五
晴。昨晚,葉君示余以陝西提學使接到余等電報后所復快信一紙,由西安至此,僅需六天。言“來電已悉。查此項學生,本公所只有保送之權,所云撥款接濟一層,礙難遵照辦理”云云。閱后亦無法,置之而言。
午間,教務處考驗第二格學生其已習過代數、幾何、三角者之數學程度。又言如能用英文問題為答案者,可於廿七日與第一格同考,不能者則於今日考驗。余答不能,遂即時受考。又問余所學科目,余以代數及平面幾何之全部對。主考先試余幾何,書問題於黑板,令學生一人就黑板演式作答。試餘二題,余答皆弗完。乃趨余至鄰室試代數,問題為(x十a)n展開之公式並證明,及二次方程二題。余勉強演畢而出。主考者又詢余是否能閱各種英文書籍,余對以恐現在力尚弗及云云。
三月二十五日(陰曆二月廿五日) 星期六
晴。晚小雨。晨,教務處又考驗第二格學生其已習過博物者之博物程度。余等皆往應試。共出問題四道。動、植物各二,令於動物、植物各作一題者為完卷。
午,無所事,閑談而已。第一格學生,今日舉行分班考試。又陝西第二格學生馬君,亦以是日移居校內。廿七日,第一格學生考試數學,第二格學生願同往試者,亦有十餘人之多。余則自以為英文程度太淺,況素未翻閱英文科學書籍,驟往貿然應試,未免資格有所不及,故昨日只得以漢文應試。乃今晨又與張君至管理室見某員,言願往與試,此舉殊似屬冒昧也。校中又給各生洗衣摺一個,每中衣百件費二元六角、西衣百件三元六角。
二月四日 星期三
陰。午前,至圖書室讀“Education in Sexual Physiology and Hygiene"(By Philip Zenner)一冊,著者為Cincinate School教員,因感然青年學子多溺於誘惑,陷於習慣犯手淫onanism;masturbation;self—abuse之病,誤以窒慾保身continence為有害,遂至肆行無忌,患不可言。種種病理的遺精seminal or nocturnal emissious;wet dreaw等事隨之而起,而世間種種花柳病social diseases(即梅毒syphilis及淋症gonorrhea)由是滋蔓傳染,貽害人群,禍烈無比,惻然憫之。乃就為其校學生特別開班,講授生物生殖之理及人生保身之要,俾諸生之有病者可以悔改,無者自可不染。此書其講義錄也,言最激昂動聽,其有助學界及一般社會豈淺鮮哉!
書中有謂人生品德之高下,皆成於習慣。Habits make character,故人當利用習慣,而勿為習慣所利用。“We should make habit our friend and not our enemy"。若不能自脫惡習慣之束縛,則日趨下流,生涯不堪設想矣。然既有惡習慣者,必當即速悔改。法諺有曰:It is the first step that counts,即謂從后種種譬如今日生,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故過而能改,不足為過,是在人之努力堅志、痛心疾首以殲除惡魔而已。
余讀之而憬然,自思居常著意修德,言論思想間處處不忘此點,而跡我所行,尚有數多之缺點,或竟反不如常人者,此可痛也。從今日起,余當立起一番新志願,事事改去舊觀,必期事均有合於道德,乃可算一人。余向來大病為思想多而實行少,故今當屏去一切無謂之思想,研究實學,練習純德。特書於此,以質之明神上帝,常茲鑒臨,以勗余眚。勉哉小子,其兢兢哉(余敬慎書此數語,余當常視此。余他年果能有一朝之成就,其毋忘此日哉)! 又翻閱Applied Mechanics。”余維修學不專,必鮮進步,故余並決定,將來至美必學Technical chemistry。此時有暇則力研英文,不遑他事,毋分心而歧志也。
五月二十二日
晴。風。上課如常。
羅君集義來,強邀同道入城,余雅不欲,且深知進城之無意味,頗為譬解。而羅君只強聒,乃於午飯後,乘火車同往。
至史君勛臣處敘別。三時許,至中華大學,仲侯以救國儲金事,赴中央公園大會,至夕始歸。
余閱其案頭生理衛生書數種,有云:人生莫不有欲,惟當學生時代,主屏除遐想,團聚精力,圖事業學問之成功。既生為萬物之靈,則當有戰勝欲魔之能力。不可借口於生人性分如是,自暴自棄,早年墮落,悔怨毋及。其言皆可為青年針砭。惟更有說者,即欲者,亦有形而上與形而下之別。精神之愛,至為高尚清潔;而形體之愛,則不足語此,然惟稟賦特異之人,能別擇於此間,故世殊不數覯也。
晚,與仲侯談。下榻其處。
五月二十三日
晴。風。晨謁李公孟符,公函仍未作,謂高公約今日可出場。余再三婉催而別。謁秦公,未遇。謁趙公,未見,以赴津為辭。謁張公雲亭。
晴。上課如常。
午後,見周校長,商《周報》臨時增刊事。校長議論頗多,大率重事實而輕道理,又不以詩文之歌哭為然。然必於詩文中,作深刻之繩墨,亦不可以已乎?
五月二十五日
晴。上課如常。
夕,在《周刊》事務所,開編輯會議,決定《臨時增刊》內容,及各人分任之部分。
晚,與瑤城談甚久。躑躅月光下,至十一時始寢。
談竟,余憤慨甚多,深感行道立品之難,與人情不平之況。苦衷難諒,盛事孰稱?余從此殆廢然矣。蓋余之與余友,平昔不以常人相待,亦謂相知以心,故除去藩籬,毫無爾我。吾友經濟之需,余不問力之能否,一力擔任。近以境況所迫,預算不給,然都不汁及,擬先將吾友支付完全,俾其回家省親,余然後步步設法,籌備現在與未來。乃假期在邇,秦公處即望兩度接濟,亦只能支付吾友而不及余。且事實上,無論如何催懇,似非略遲日期,不能收領。此種困迫情形,略告吾友,而吾友不顧一切,惟重視自己,謂今年必須回家,不能稍遲日期。責余何不早告,此時彼設法不及,誤乃公事,咎實非輕。且必余無心籌備,故藉此以自解。余之如何,彼皆不顧。彼必欲達回家之目的,且一日亦不可遲。嗚呼,吾友乃欲以社會事理相責繩,然何其不自反也?夫以社會事理論,吾之於吾友,行過篤矣。吾友得友如此,辛苦經營,忘己為人,在我無一金之儲,籌用無出,將罄所得以資吾友歸省,迫於實事,略緩期日,乃遽以惡聲相向。試問余果何負於人而如是者。且以手續論之,餘三年來,雖完全供給吾友,然固未嘗為一次之預約。不過隨余之景況,效管鮑之分金,亦未敢即有擔負一切之表示。若論實事,以過去種種證之,即余先事警告,吾友決亦無力籌出巨款。況此乃吾友切身之事,又何待人之警告,而始知為計哉?夫為德不卒,君子之所甚恥。余惟以道德觀念之趨迫,行必求高於人。故
本忠厚之意,盡心竭力,視吾友與己身無殊。比經艱難憂患,事益難而志彌堅。而吾友之以道德家自負者,對吾乃並常人之道理而不講,甚且有君子可欺以其方之意。上焉者猶如此,其下可知。茫茫眾生,劫將胡底。余無他憾,惟恐余行道濟人之意,從此減卻一分。則吾友之報我者酷矣。
近來所受之感觸,(一)覺得作事必當從世俗之分際,過猶不及。又(二)道理只可自講,與人當慎之又慎。即心服道理者,作事亦不講道理,況其以道理為口頭禪哉!(三)人皆重己而輕人,先己而後人,即服從道理者亦然。故人亦不能不為已,且不能捐已殉人。
余此後與吾友之關係,雖無變易,經濟仍竭力補助,而事實、手續、地步、方法,均不能不自占幾分,不再相望以道理可也。
是晚感觸過多,入夢甚遲。
五月二十六日
晴。上課如常。仍讀Carlyle文集Life of Burns。詩人之窮困,可為傷心也。然處窮困而安之若素,終不改其為詩人,則凡學為人者所當注意。又文中有云:“It is a mortifying truth,that two men in any rank of society,could hardly be found virtuous enough to give money,and to take it as a necessary gift,without.injury to the moral
entireness of one or both.”……今之友道,與昔日異其界說。社會 中,人必各自獨立,不可倚賴他人之輔助。此根據今日社會之道德所應為者。
實事上確是如此。昔聞之嚴親,朋友雖有通財之誼,然交道之壞,鮮不由於經濟關係者,故宜慎之又慎。年來閱歷,深知其然。即如余與堯臣之交涉,就事實論之,至簡明而易判決。余盡心於吾友之事,初未敢自以為功。吾友只持回家之理論,而不計事實之能否。平日又狷潔自高,以為對余非刻意冷傲堅執,不足表示取與觀念之異常人者。然萬事皆有自然之情理,倒行逆施,非常人之所喜為,而常人之所不任受也。故余能透見吾友之心思、之理論。而事實上之情況,吾友毫不置察,糾葛乃起。蓋只重理論、不重事實之人,每好責人以如些。吾友即其例,余亦或不免。此等事雖微細,固大有可研究之價值在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