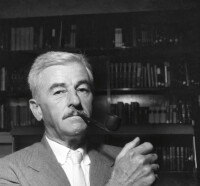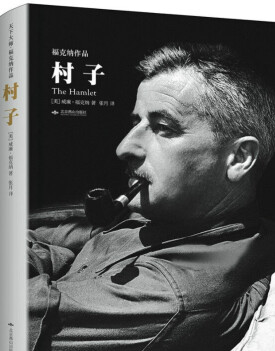共找到2條詞條名為村子的結果 展開
- 美國小說家福克納作品
- 2010年馮積岐所著的圖書
村子
美國小說家福克納作品
《村子》是斯諾普斯三部曲之一,小說以法國人灣的鄉村為背景,講述了主人公弗萊姆·斯諾普斯不擇手段地從一個無名小卒勝利改變為富有人士的發跡史。
《村子》是福克納後期的重要作品之一,福克納將這部作品獻給他的文學啟蒙老師菲爾·斯通。如同《村子》的編輯所註明的,這部小說最初始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期有關斯諾普斯家族的一組隨筆和片段,歷經十幾年的構思,最終成為斯諾普斯家族小說三部曲的第一部,其餘兩部依次為《小鎮》《大宅》。在斯諾普斯家族小說三部曲中《村子》是十分重要的一部。
主要講述了北方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代表人物弗萊姆·斯諾普斯(FlemSnopes)如何利用一系列狡詐、欺騙的手段逐漸從政治、經濟、倫理道德等方面征服了代表南方文化的村子,即老法國人灣(Frenchman'sbend)。弗萊姆於1902年來到傑弗生鎮附近的老法國人灣謀生。他先是在代表南方領袖人物的經營的雜貨鋪里做夥計並逐漸接管了店裡的帳目。接下來他又通過放高利貸、開鐵匠鋪等投機行為成了村裡的富戶,同時還威逼威爾·凡納已懷孕的女兒尤拉(Eula)結婚,從而成為村子里的權威人物。小說在結尾處入木三分地描述了弗萊姆怎樣把捕來的一群野馬假冒馴馬賣給當地居民,又把一塊荒地偽裝成有寶之地,高價賣給村子中的村民,然後離開村子進軍傑弗生。
在美國新南方向現代南方過渡的轉型期變革首先在《村子》文本表層的各種物質細節書寫中留下了印記,而各種物質細節不但表現了20世紀上半葉美國南方農業文明和工商業文明的相遇和衝撞時的物質文化,也折射了作家對於南方社會變革接受和排斥兼具的矛盾態度。《村子》文本中出現了很多和南方歷史轉型期相關的物品書寫,既有再現美國南方工業化進程中遭到破壞的環境的書寫、地理景觀物品書寫,還有現代工業文明影響下的技術物品書寫。這些在文本中反覆出現的不同層面的物品成為20世紀上半葉美國南方歷史文化的物質表達,呈現了南方城市化進程中社會轉型期的變遷圖景和文化結構。
親歷時代變革的福克納在《村子》中通過對南方文化的想象性再現從不同層面回應了20世紀上半葉新南方向現代南方過渡時的重大變革,傳達了他對轉型期南方社會文化的矛盾態度和對南方居民生存狀態的深切關注。《村子》中和物品相關的“微觀細節”書寫如同慢慢打開的一幅南方轉型期變革的畫卷,福克納似乎無意於提供任何確定的答案,他只專註於表現衝突過程本身。
弗萊姆斯諾普斯
在福克納的筆下,斯諾普斯整個家族,從阿比到他的兒子弗萊姆乃至幾乎所有的親戚都擁有一個代名詞:肉食群體。作為新興資產階級的代表,弗萊姆的身上完整地體現了斯諾普斯主義的精髓:道德淪喪、惟利是圖、恃強凌弱、貪婪狡詐、冷酷無情。福克納雖然精心刻畫了這個主人公,卻對之投以最大的輕蔑。儘管作者筆下的南方地主也做了不少壞事,但是他認為他們都是受感情驅策的奴隸,是可以理解與原諒的,而弗萊姆·斯諾普斯卻是徹頭徹尾的偽君子,全身上下都透露出令人厭惡的資產階級的銅臭氣味。他那對“死水般”的眼睛讓人感覺不到他是一個存活於現實世界的人,只是上帝失手製造的一具沒有靈魂的軀殼。即使在小說另一個主人公拉特利夫的意識流中,弗萊姆也是以魔鬼撒旦的形象出現的:弗萊姆身陷地獄,面對魔鬼撒旦的威逼利誘卻毫不恐慌,始終強調撒旦履行合約返還他的靈魂。最後連撒旦都對這個靈魂喪失殆盡的人無可奈何而甘拜下風。
威爾瓦爾納
在小說主人公弗萊姆·斯諾普斯來到村子之前,南方人威爾·瓦爾納是村子的真正統治者,也是整個法國人灣“傳統意志”的體現。但是威爾·瓦爾納只是單純地生活在繁榮的莊園經濟所提供的物質世界里,內心缺乏對生活和現實世界的敏銳觀察與思考,也正是這種精神世界的迷失才使得他被弗萊姆輕而易舉地打敗,眼睜睜地看著後者成功地從鄉村到城鎮,從城鎮到城市,肆意踐踏著古老的南方文明並最終達到個人的飛躍。
尤拉
小說中另一個讓人扼腕嘆息的主人公是善良純潔的尤拉。如果說,福克納通過塑造弗萊姆展現了西方社會對物質佔有的貪婪慾望,那麼通過對尤拉的塑造,福克納則成功地展示了人類原始的性慾的衝動。尤拉是老法國人灣孕育出的一個超凡脫俗的女性,是南方凈土上的聖女化身,她代表著自然本身,象徵著生命的繁衍。但是尤拉雖然神聖不可侵犯,她的性感卻足以引誘人類最原始的慾望,她“既腐敗墮落又純潔無暇,既是童貞處女又是武士和成熟男人之母”,幾乎使所有老法國人灣的男人們都為之著迷並試圖阻止他們心中的女神在物質世界里的墮落。然而人性最原始的衝動和慾望終究抵擋不了現代工商主義強烈的物質衝撞,尤拉最終還是屈從命運,嫁給了弗萊姆。在現代工業機器轟鳴的社會裡,尤拉的結婚馬車迷失了方向,越駛越遠,最終成為弗萊姆進軍傑弗生鎮的一個有利的跳板。馬車時代的結束,“彷彿已經成了……塵世的回返、歡樂激情、所有本能衝動放縱的結束”。福克納塑造的尤拉這個角色實際上代表了南方最原始的文明,雖然貌似高貴,但是在現代工業的衝擊下,骨子裡已經透露出腐朽的跡象,無可葯救。
拉特利夫
小說中最富戲劇性的人物是商人拉特利夫,一個老法國人地盤裡有寶藏的謊言竟騙得拉特利夫深信不疑,從而犯下了一個致命的錯誤——貪慾蒙蔽了他的理智——慘痛地敗在弗萊姆的腳下。拉特利夫的失敗,不僅、意味著南方文明企圖挽回頹勢希望的破滅,也意味著南方鄉村面對被顛覆的命運回天無力。從福克納看似平淡的敘述中不難發現作家在以一種怎樣無奈和惋惜的心情悲嘆南方文明的不堪一擊。
在《村子》中,福克納主要塑造了兩類人物,一類是唯利是圖的人,他們受利益驅動,其中以弗萊姆為代表;另一類則是情感的奴隸,這類人為數眾多。在前者與後者的爭鬥中,後者無可挽回地失敗了。在作品中,福克納象徵性地預告了在傳統農業經濟向現代經濟轉型的過程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將戰勝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資產階級將取代地主階級。
從種種和弗萊姆相關的物品書寫來看,福克納筆下的弗萊姆是一個時刻追逐物質利益、極其渴望成功的人物形象。“物質主義”是理解弗萊姆的關鍵詞。掙錢是弗萊姆“終極和恆定不變的參照點”,是最終的目標。這一終極目標的實現使得弗萊姆的人生變得非常專一,甚至到了冷漠的地步。可以說,弗萊姆的發跡史基本上就是財富積聚史,正如小說中加文的話:“對弗萊姆而言,錢對他的誘惑就像女人的性對大部分男人的誘惑一樣”。從最早在老法國人灣騎的騾子,到通過婚姻交易擁有老法國人灣舊庄園的土地,再到在黃銅事件中通過欺騙手段獲得在傑弗生鎮的第一桶金,最後登上銀行行長的寶座,並成為斯潘大宅的主人,這些標誌著他一步步走向財富的巔峰,也喻示著他的美國夢成功實現。在文本中,他獲得的權力和成功的標誌也和很多重要物品相聯繫,“水站”、“墓碑”、“大宅中的旋轉椅子”在文本中不斷被敘述者強調是弗萊姆邁向成功的三個紀念碑。
如果將弗萊姆置於南方歷史轉型期的歷史語境中來看的話,他只不過是物慾橫流的社會中追求物質成功的芸芸眾生中的一分子。當時美國盛行的物質主義才是弗萊姆悲劇的真正源頭。鼓吹白手起家的物質主義帶來的一個負面影響就是社會道德風氣的急轉直下,很多人為了發財不擇手段,互相傾軋,弱肉強食。在拚命掙錢、追逐美國夢的過程中,不少人失去靈魂,價值觀發生轉變,在追逐物質利益的過程自身也異化為物質客體,呈現為物化的身份特徵。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福克納和這一時期的很多作家一樣,通過塑造具有物化特徵的人物來捕捉美國夢在社會中的陰霾,其筆下的弗萊姆可以被視為一個在現代社會中為了追逐物質利益而丟失靈魂的現代人的隱喻,他的悲劇和阿瑟?米勒筆下的洛曼、奧尼爾筆下的詹姆斯?蒂龍、德萊塞筆下的克萊德等人物一樣,都是美國夢破滅的重要範本。
雖然福克納對南方傳統價值的解體感到失落,但是他並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他在懷念南方光榮往昔的同時也表達出對人類的信任,他堅信人類只是暫時迷失,終有一天他們能撥開雲霧見月明。而作家的職責就是幫助人類重建優秀的價值觀值,這個思想在福克納那篇著名的諾貝爾獎演說詞中有明確的說明:
詩人和作家的職責就在於寫出這些東西。他的特殊的光榮就是振奮人心,提醒人們記住勇氣、榮譽、希望、自豪、同情、憐憫之心和犧牲精神,這些是人類昔日的榮耀。為此,人類將永垂不朽。詩人的聲音不必僅僅是人的記錄,他也可以是一個支柱,一根棟樑,使人永垂不朽,流芳於世。
福克納並不是信口開河,而是在身體力行他所提到的作家的神聖職責。在寫給朋友的信中,福克納也多次提到這個問題:“一直以來我都是在寫榮譽、真理、憐憫、體諒、耐心以及忍受悲傷、不幸、不公並且繼續忍受的能力。我著眼於那些人,他們遵循和堅持這些美德並非是想獲得報酬而是因為他們是美德。”在他的作品中湧現出許多這樣的人物,他們為了維護人類的美德不斷地努力和奉獻著,比如迪爾西、朱迪絲、契克、斯蒂文斯等等,在《村子》里,同樣也有這麼一批充滿希望的村民。雖然由於自身的局限性村民也有不少的弱點,他們自私、貪婪,愛看熱鬧,有時也缺乏同情心,因此,他們常常落入弗萊姆的圈套,成為受害者,但是他們不像弗萊姆那樣失去人性。在福克納看來,“一個人做壞事並不特別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否還具有人性。只要他還是一個人,他就有可能變得好一點。一個人最壞的是失去人性。”在村民的身上,能看到愛的光芒,這是弗萊姆所缺少的。福克納在《村子》中描述了3對村民的愛情,他們的愛雖然很少用語言來表達但是卻通過行動來傳遞。這和弗萊姆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雖然弗萊姆娶了瓦爾納的女兒尤拉為妻,但並不出於愛,這場婚姻本身就是一個交易,瓦爾納為了保存家族名聲(尤拉未婚先孕),而弗萊姆為了往上爬。通過村民們對愛的追求和弗萊姆愛的缺失的對比,福克納傳遞了一個信息,即心中有愛的村民定能夠戰勝無愛的弗萊姆,這在《大宅》中得到印證,弗萊姆最終被明克殺死。弗萊姆被殺象徵著人性的勝利,這也是福克納完成南方價值重建的重要步驟。
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南方作家,福克納從不掩飾自己對家鄉傳統的經濟結構和文化價值觀的讚賞。對南方固有的淳樸自然的鄉土氣息及傳統美德的嚮往和深切眷戀成為他一生中都割捨不斷的南方情結。然而,面對物慾橫流的現實世界,福克納無所適從,惟有在作品中潑墨抒發自己的鬱悶和對構建精神家園的渴望,小說《村子》就是體現這一情結的代表作之一。作者“站在與都市審美相對的鄉村視角上觀察和描寫他的家鄉的美和魅力”,鄉村的綺麗風光和南方泥土所散發的特有的清香氣味,還有那安謐的田園氛圍和舒緩的生活節奏,以及人們在故園上所能獲得的安全感在小說中表現得淋漓盡致。這種強烈的浪漫主義傾向經年累月凝固成一種對靈魂歸宿和精神家園的呼喚情結。但是從北方洶湧而至的工商勢力卻毫不留情地摧毀了人們的嚮往和渴望。小說《村子》恰如一個視窗,完整透視了20世紀初期南方社區所經歷的歷史變革。這個時期正是南方經濟逐漸從內戰中恢復過來並得以發展的時期,與此同時,北方工商勢力及其價值觀也開始南下,無聲地衝擊著南方古老的傳統和文明。在這個變革過程中,福克納作為南方作家的先鋒代表,一方面為捍衛家鄉的傳統文明不遺餘力地奔走呼號,另一方面也開始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所摯愛的南方社區,對南方社會中的問題進行痛苦地剖析。他雖然抨擊現代機械、金錢文明對人性的摧殘和異化,但是也無情地揭露祖先的罪惡,譬如奴隸制度給後代留下的歷史負擔。從這一點上說,福克納不僅僅是一個描繪地方色彩的鄉土作家,更是一位放眼全社會的偉大作家。他滿懷內心的痛楚用手中的筆狠狠刺向南方的痼疾——不是政治、經濟上的而是精神、心理狀態上的痼疾。他感慨弗萊姆之流的卑鄙無恥,但是也清醒地意識到,那曾經創造奇迹的南方土地如今不得不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更迭,這是一種無法挽回的趨勢,法國人灣的敗落是必然的。老法國人地盤的失落,尤其是落入弗萊姆的手中,意味著南方的經濟基礎在那些工商主義和資產階級的不斷侵蝕下早已垮台,它的殘存的上層建築也搖搖欲墜,它註定要不斷走向敗落,最終成為歷史的塵埃。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儘管福克納面對他筆下的悲劇人物,如尤拉、拉特利夫,在“看似客觀的描寫之中透露出他作為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者的憐憫與同情心”,他卻不是一個宿命論者,他相信人類有所作為,在抨擊北方工業主義的冷酷無情的同時也用睿智的頭腦思考南方文明敗落的根本原因,從這一點上說福克納不是通常意義上的舊傳統的衛道士。他已經清醒地看到了南方文明正走向敗落。但是福克納不想看到人性的真摯與淳樸也隨之失落,他渴望人性的復歸,正如他在接受諾貝爾文學獎金的演說中所說的那樣:“我不想接受人類末日的說法……他(詩人和作家)的特殊光榮就是振奮人心,提醒人們記住勇氣、榮譽、希望、自豪、同情、憐憫之心和犧牲精神。最後一個詞`犧牲精神'非常重要,要有犧牲精神,‘真、善、美’,才能戰勝‘偽、惡、丑’,光明才能戰勝黑暗”。
小說《村子》的成功之處在於福克納沒有把自己放在一個旁觀者的位置上客觀敘事,而是將自己作為村子中的一員,在嬉笑怒罵中已經把自己的命運同那些淳樸的村民們的命運牢牢地拴在一起。小說中隨處可以聽見他的聲音。在他的聲音里,你不僅能聽到淳樸的鄉音,爽朗的笑聲,更能感受到“粗重的喘息,憤怒的斥罵,嘶啞的喊叫,痛苦的呻吟”。總之,福克納用自己的全部身心感受著對故鄉的執著眷戀的同時,也深深思索著社會變革對人類精神家園造成的衝擊,他在割捨不下的南方情結中孤獨地尋找著人性賴以生存的鄉土文化及其孕育的真正意義上的人性。
《村子》的敘事與前期代表作有很大的不同,看似鬆散的結構下蘊藏著縝密的設計。通過多聚焦多層次的敘事方式,福克納把看似毫無相關的故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刻畫了村子中兩股對立的勢力。聚焦者和敘事者在聚焦和敘事的同時不斷完善中心人物的形象,同時也揭露了他們的性格特徵。福克納通過這樣的方式描繪了色彩斑斕的鄉村生活景象。揭示了作者本人對新經濟勢力入侵的矛盾心理也表達了他對現代人走出精神荒原的思考和探索。
威廉·福克納的創作的《村子》作為斯諾普斯三部曲之一描繪了美國南方社會物慾橫流,社會道德風氣直轉急下的場景並總結了社會中的種種問題。雖然《村子》的某些篇章帶有些許悲觀色彩,但是從整體上看,《村子》始終洋溢著積極向上的精神。福克納用反襯的手法批判了斯諾普斯主義,讚揚了人“勇氣、榮譽、希望、自豪、同情、憐憫之心和犧牲等”的精神。對約克納帕塔法世系具有很好的強調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