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找到5條詞條名為巴比特的結果 展開
- 美國作家辛克萊·劉易斯著長篇小說
- 一款專註於做區塊鏈資訊的APP
- 電影《雨人》中的人物
- 美國金屬學家、發明家
- 日本著名動漫《玩偶遊戲》中的角色
巴比特
美國作家辛克萊·劉易斯著長篇小說
《巴比特》是美國小說家辛克萊·劉易斯在1922年發表的長篇小說。是一部反映美國商業文化繁盛時期城市商人生活的小說。它不僅塑造了一個典型的商人形象“巴比特”,還漫畫式地表現出美國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商業文化的方方面面,具有文化觀照和藝術欣賞的雙重價值。
巴比特是一位成功的房地產商人,過著富足而又平板的中產階級生活。然而作為一個人,他受到虛空的襲擊,於是企圖尋找另一種“真正的生活”。為此,他外出漫遊,嘗試過一種玩世不恭的生活,甚至染上了革命情緒。但巴比特又沒有勇氣去承受接之而來的社會冷落,於是,他重新投入了家庭生活和商人生涯的懷抱,在小說的結尾,巴比特將希望寄托在他的兒子身上……作者通過巴比特這一形象,把唯唯諾諾而又沾沾又喜的美國人的特性拒絕得淋漓盡致。“巴比特”這個名字從此成為鼠目寸光的庸俗市儈的同義詞。

封面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開始,美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科學進步促進了工業生產飛快發展,消費行業控制了美國的經濟,美國成了世界強國。隨著美國經濟的這種變化,社會結構和國家觀念也發生了變化。工業增長帶來了商業繁榮,白領中產階級數量急劇增加,控制了官僚政治和公司以及分配與市場的日漸增大的功能。除了社會結構的變化外,美國的價值觀念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以節儉、勤勞為特徵的清教主義式生活方式已趨於沒落,代之而起的是一種宣揚享樂與滿足的消費享樂主義為特徵的新的生活方式。
進入20世紀后,中產階級逐漸放棄了清教傳統,摒棄了節儉自律的生活方式,以“娛樂道德觀”代替了“行善道德觀”,享樂主義成為生活信條。正如貝爾所說“文化不再與如何工作,如何取得成就有關,它關心的是如何花錢、如何享樂”中產階級代表巴比特的生活正是一幅大眾文化的寫實照。以他的休閑方式為例,小說中多次出現“電影”,這儼然已經成為中產階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電影”作為大眾文化消費的產物,“據統計,1919年,美國人花在娛樂上的費用約為25億美元,到1929年達43億美元,其中用於電影、戲劇和體育等的佔到21%。”巴比特一家熱衷於看電影,“每星期至少去看一次電影”。巴比特喜歡看光腿美女、西部片或警匪片,這類題材恰好符合中產階級的消費心理,不需要花費多少時間和金錢,卻能夠獲得娛樂效果、滿足心靈享受。大眾文化除了為中產階級帶來豐富的娛樂樣式,更重要的是間接培養了中產階級的欣賞品味。中產階級愈來愈按照大眾文化的要求去打磨自己,把自己變成絕對的大眾文化人。
在這種情況下,一種沾沾自喜、自鳴得意的心態在美國油然而生。羅伯特·莫斯特·洛維斯這樣描寫這種心態:“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確的,因為是我們做的。我們所有的戰爭都是正義的,所有的政治家都是純潔的,所有的商務活動也都是誠實的。我們的國家是自由、寬容、布滿機遇以及充滿正義的國家。”美國人為自己的國家以及享有的自由感到無比自豪。他們把自己的國家看成是世界上最好的國家。由於盛行沾沾自喜、自鳴得意的心態,實利主義也風行一時。每個人似乎都成了拜金主義者,全都熱衷於賺錢發財。同時,他們還樂於炫耀他們的資產。擁有現代化消費品變成了某人所處社會地位的象徵。這已成了普遍的社會現象。再者,隨著注重生產階段向注重消費階段的轉化,注重生產階段的一個主要特徵—個人主義變成從屬於集體主義。加入一個隊、成為某一群體的一員變得尤為重要。這些社會現象合在一起提供了一個極好的諷刺時機。
縱觀全書,作者集中筆墨塑造了巴比特這個“普通人中的一個”的形象。巴比特一睜開眼,立刻就被商業化的美國所包圍:喚醒他的是一個造價不菲的最新式樣的鬧鐘,鬧鈴的聲音甚至模仿美妙的教堂鐘聲,富有諷刺意味的是它並不是提醒巴比特去敬拜神聖的上帝,而是催他起床去掙錢,或敬拜財神。在他這個時代,精神已被物質所取代。接下來巴比特陷入了塵世間一個又一個繁瑣的決定中。戴眼鏡、穿衣、梳頭、洗臉,這些本是人人每天經歷的再簡單不過的過程,卻讓巴比特煞費苦心:他的裝扮必須符合他的殷實公民的身份,必須體現他是一個體面的標準公民。而他的洗漱過程,則彷彿是對他所擁有的豪華浴室的展示,以及他對全靠自己養活的不知感激的一家人的抱怨。看到這裡,巴比特瑣碎、空虛的生活狀態簡直到了令人同情的地步。
巴比特在生意上小有成就,起初他還對通過奮鬥多年所獲得的經濟地位很是自得,然而隨後隱隱覺得他的生活中缺了點什麼,他本能地想去尋找。他發現本應為人們提供精神食糧的教會竟淪落成“商會”,已不能給他精神上的安慰。巴比特試圖從他的社交生活和朋友中獲得樂趣,末了卻對那些和他一樣平庸自滿的商人朋友不勝厭煩。
巴比特畢竟只是一個平庸的普通人,他無力走出自己內心的空虛,他的反叛也顯得那樣軟弱和可笑。他企圖用婚外戀來逃避乏味的家庭和生活,企圖退隱到大自然中去,這些都註定不會成功。而在政治上,當他企圖反叛他的階級,為爭取正當權益的罷工組織說幾句公道話時,他的叛逆立刻就讓“商業同盟”感到了恐懼。巴比特一個人的力量無力抵抗“商業同盟”對他的圍攻,在面臨被驅逐出那個階層的威脅時,他別無他路,只好重新返回他原來的商業圈,繼續扮演商業社會的標準公民的角色。
巴比特只是他所處時代的一個典型代表。在當代美國,還有千千萬萬像巴比特這樣在勢利上無比熱衷,在思想和精神上充滿困惑,在文化和知識上茫然無知的人。巴比特不僅僅是劉易斯小說中的一個人物,而是現實社會中的一個群體,是一種現象。巴比特本人就是當代美國盛行的實利主義及商業主義等思想的集合體。
《巴比特》可以毫不誇張地稱為商業文化的經典之作。它使人看到了那個時代美國的物質崇拜,看到了商業文化怎樣發展和風行起來,看到了美國文化與商業文化有著怎樣的淵源。它還使我們看到了商業文化走向異化后的種種弊病,看到了發生在那個年代末期席捲美國及至西方世界的經濟危機的部分起因。
在《巴比特》中,辛克萊·劉易斯以小城澤尼斯為例,首次披露了美國整個國家都盲目遵從標準化與一致性。所有的戒律和道德準則都標準化了。人們必須遵守它們以成為標準公民,從而使自己變成一群頭腦空空、完全喪失個性的人。“他們唯一的存在就在於群體中,自然而然要為群體的清規戒律而奮鬥拼搏。除了標準化及與人一致之外,他們不可能有別的東西,因為他們個性的源泉已經乾涸了。”一旦離開群體而生活,他們就會感到不安全、不穩定。這樣一個階層的價值標準左右著其他人。如果有人想在這社會中生存下去,他就必須拋棄他原有的價值標準和處事態度,與大眾的價值標準保持一致。他將變得更加毫無保留、更加坦率,最後趨於失卻所有的個人觀念而與其他“隊”員享有一樣的東西。他必須遵守社會規則,從而與人們的期望相符,因為每個人都在這麼做。不然的話,他就會受到孤立。
辛克萊·劉易斯在小說中諷刺並抨擊了這一社會現象。他把喬治·福·巴比特及其同伴成功地塑造成這一社會現象的典範。澤尼斯,即巴比特及其同伴們的居所,是個徹頭徹尾的標準化城市。由於巴比特住在澤尼斯,屬於澤尼斯,所以他無疑就會被局限於與人保持一致的陣營內。書中大部分情節中,巴比特都是個十足的標準公民和傳統觀念的遵奉者。他必須做個標準公民、遵奉傳統觀念、憎惡波希米亞主義、忠於共和黨,同時反對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及激進主義。他還必須是個標準商人,工作勤勉、努力賺錢,使生活更加美好。他也必須做個標準父親,對孩子要慈愛有加。甚至連他的私有物品也是標準的,應該足以顯示出他作為一個成功商人的身份。巴比特還是個傳統觀念的遵奉者。他沒有任何主觀創造性及獨特的思想,所以,要他形成自己獨特的見解簡直比登天還難。他所有的思想和觀點都和其他人一樣。如果其他人沒有給他提供思想和觀點,他就喪失了他雄辯的口才。因此,他的政治是集體的政治,民眾的政治,而他的信仰則是一種不帶任何主觀主義的公共慣例。他的所思所感正是其他人的所思所感。所以,他的所有活動都是同其他人分不開的,同時也得到其他人的證明。他的聲望及事業都與其他人的緊密聯繫在一起。他們可以把他推向榮譽的頂峰,如選舉他當促進會俱樂部的副主席、推舉他在澤尼斯房地產委員會上發言,而這也確實使他出了些名。同時,他們還能把他驅至孤獨與沒有朋友的地獄以及提心弔膽、優慮如焚的牢囿。因為他的生命線——生意已受到威脅。馬克·斯柯勒把巴比特這一形象歸結為:“他自己全然不是個創造者,他的成功依賴於社會關係。他沒有控制權,只有通過參與而使自己平安無事。他和他的同伴們一起大肆吹噓、大聲吹棒,為整個群體大唱讚歌、大聲叫好,嘲笑所有的不同論點,否定所有的不同意見—只是和眾人一起往前爬行而已。”所以,標準化和一致性是一種很強的社會習慣。任何人都不可能擺脫它們。詩人瓊·弗林克只能在喝得爛醉的時候才能透露出他那已慘遭挫敗的抱負。推銷商保羅·賴斯林全然的反抗卻只招致謀殺妻子的罪名,並因此銀擋入獄。巴比特也試圖逃離群體,用自己所喜歡的方式生活。於是,他便開展了一系列反抗性的活動。他比家裡其他人早幾天跑到緬因州去,好讓自己快活幾天。他還和指甲修剪師調情,跟一個寡婦做愛,還與波希米亞人瞎混、跳舞、喝酒、性交。他甚至變得有自由主義傾向。然而,就算他的朋友們能容忍得了他與婦女調情及狂喝濫飲,但是,他們也絕對受不了他哪怕是很溫和的自由主義思想。於是,他們立即採取措施以使他回心轉意。他們勸他參加“優良公民聯盟”。他對此加以拒絕,卻遭到朋友們的全然孤立。他似乎還失去了他曾為之洋洋得意的所有聲譽。一年一度的市商會午餐會上不再邀請他發表演說,不再邀請他去參加奧維爾·瓊斯舉辦的打牌晚會。每個人都在低聲議論他。更糟的是,他的生意也受到了影響。由於迷了途,他將在生意上失去很多。巴比特被置於如此不利的境地。每個人,包括他的妻子都站在他的對立面。他已無力承受這種壓力。事到如今,他已別無選擇,只得與其他人妥協,向一致性舉手投降,回到他的朋友們當中。他再次變成標準化和一致性的楷模,既贏回了朋友們的愛戴和尊敬,又贏得了自尊。
標準化和一致性是當時的一種不良社會現象。像巴比特這樣的人根本無法擺脫它而只能追隨它,這就是為什麼曾有意成為自己的巴比特最終卻完全失敗的原因。雖然他向兒子說明了這一點,希望他兒子會比他做得更好,但對他自己來說,他想逃脫的努力已完全失敗。辛克萊·劉易斯在此以巴比特的經歷作為例子,有力地攻擊了標準化與一致性。它們的勢力如此之強以致成了人們的精神枷鎖。有些人受其束縛卻毫無感覺,反而樂在其中,其他人呢,雖然意識到這令人討厭的限制,卻又無路可逃,只好忍受著。這正是辛克萊·劉易斯的抨擊目標之所在。
其次是利潤或利益原則成了帶普遍意義的指導原則通行於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作品的主人公巴比特在業務和生活交往中忠實地奉行這個原則。在業務上他有一個長期的夥伴澤尼斯公交公司,雙方維持長期業務關係的根本原因是利益。巴比特先是借公交公司的名義購下了金鶯谷高級住宅區的地皮(見第四章第四節),從中賺了一大筆;後來又是公交公司的頭頭把林頓大道公交線路要向前延伸的消息提前告訴了他,使他能在這個消息公布之前在那一塊地方低價搶購地皮,不用說又能賺上一筆;再後來公交公司要在郊區興建修車廠,跟巴比特發生的地皮糾紛,又是了無聲息地解決了,只是隨後巴比特和公司頭頭的賬戶上各自增加了幾千美金。在社交生活中也是如此。能給自己帶來好處和利益就積極交往,逢迎巴結;反之就敷衍,就迴避,甚至拒絕,這樣的例子在作品中是很多的。比如巴比特對利特菲爾德和多普爾布勞這兩位鄰居完全不同的態度,比如巴比特的會友們在巴比特出名前後判若兩人的態度。
一次大戰後社會繁榮的現象之一便是實利主義在美國的流行。當然,這一點也逃不脫辛克萊·劉易斯敏銳的觀察力。通過巴比特這個典型人物,辛克萊·劉易斯揭示了一個沉溺於商業主義和實利主義的國家。在這塊物質富足的土地上,金錢與富裕成了最重要的東西,而真誠、真理、神聖則退居次要地位。一個人的社會地位是用金錢和財產來衡量的。只要你富有,你的社會地位便高,你也就會受其他人的敬慕,成為一個人人都想與你交往的人。在這種情勢下,人人都挖空心思去賺錢,而要達列這一目的,生意興隆便被當作一條最好的捷徑。主賺錢這一動機驅使下,商人們甚至把商業道德棄置一邊而不顧,賄賂、欺騙、威嚇、共謀等手段無所不用其極。這就是巴比特為什麼冒險和一個投機商做生意,逼迫房屋出售者以低價賣出房子而從中嫌取傭金的緣故,而通過支持盧卡斯·普勞特競選澤尼斯市市長,他接受了一條秘密信息作為回報,這又為他點得了一大筆收入。難怪巴比特會被他的夥伴之一譴責為“不誠實的人”。
澤尼斯的人們熱衷於實利主義及商業主義,但在文化上卻有很大的局限性。幾乎沒有一個人被描繪成是真正的學者。以巴比特為例,他是個無知的人。“除了知道善於投機的營造廠商那幾種房子式樣以外,他對建築一竊不通;除了懂得曲徑的功用、草地、以及六種常見的灌木以外,他對園林景觀也是一竊不通;甚至連最普通的一些經濟學原理,他也還是一竊不通。”他對警力、教學等等都一無所知,更為可笑的是,身為房地產商,他居然對一所居室至關重要的衛生設備也一無所知。他把沒有燕尾的晚禮服叫做“塔克司”。儘管他很欣賞一切機械設備,卻對它們所知甚少。他的閱讀面極窄玉最喜歡的文學和藝術僅僅是(鼓吹晚報)上面的連環畫,上面記錄著這類平庸瑣事,如“馬特先生向傑夫先生扔臭雞蛋,媽媽用拼麵杖來教訓爸爸別說粗話。”他的卧室中確實有一張英國狩獵圖的複製品,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對音樂和畫畫真有興趣,而只是因為這是大多數住在芙蘿崗的家庭中都有的裝飾品。他結婚時收到的禮物——三本書籍,以及客廳中擺放的鋼琴也都是裝飾品,而非有用之物,因為在所有的家庭成員中,只有年僅十歲的小婷卡才讀過那些書、彈奏過那架鋼琴。如此文化局限只能導致個人樂趣的局限。可悲的巴比特在尋找樂趣方面簡直不知所措。他覺得自己和太太之間沒有真愛;和朋友們則缺乏理解。他甚至沒有一種自己真正全身心投入的嗜好。雖然他很熱切地尋找娛樂和消遣方式,可他並不能得到真正的娛樂和消遣。文化局限加劇了像巴比特這樣的人的頭腦空虛,而由這些頭腦空空如也的人們組成的社會就只能是空洞的社會。
在大眾文化的消費對象中,青少年所佔比重在逐漸增加,因大眾文化能帶給人們感官上的愉悅感受,更迎合青少年追求快樂、刺激的個性。小說中出現的三個青少年分別是特德,17歲;婷卡,10歲;尤妮斯,17歲,在他們身上大眾文化所產生的影響更深遠、更廣泛、也更徹底。婷卡要求至少要和別的女孩一樣,一周看三次電影;尤妮斯則除了有關電影明星的年齡和報酬之外對其他的數字一律不感興趣,並且潛心研究各種電影雜誌,關註明星新聞;特德唯獨對汽車表現出極大的熱情。他們都是在大眾文化氛圍中成長的青年一代的典型代表,由此我們可以察覺到劉易斯更關注青少年的發展,對美國未來表示擔憂。這一代人從小就植根於大眾文化的土壤中,空氣中也無處不存在大眾文化的氣息,他們身上已然沒有昔日父輩們的傳統,他們能否擔當起今後的重任,能否繼續實現當初美國的夢想,這些憂慮都隱含於劉易斯的字裡行間。儘管劉易斯對美國現實進行深度甚至是無情的批判,但是正如他所說,在他自己看來“美國永遠是希望。他愛美國,但是不喜歡它,因為它仍舊不過是希望”。他不願意看到美國的希望消失於大眾文化中的下一代身上,他更不願意看到他“愛的美國”在轟轟烈烈的大眾文化中演變成一出鬧劇,劉易斯運用他所擅長的言語將他的憂慮傳遞給大眾,以此來引起大眾清醒的自我認識。
雖說文化局限是個次要主題,但也加強了小說中辛克萊·劉易斯對社會的批判力,而對社會的批判正是辛克萊·劉易斯小說的主題。
在小說《巴比特》中,辛克萊·劉易斯最成功的抨擊之一便是出色地描繪了一種被稱為巴比特們的中產階級商人的形象,而他們的代表人物便是主人公巴比特。巴比特們於是成了中產階級市儈階層的代名詞。辛克萊·劉易斯儘可能生動地描寫了他們的生活,並揭示了諸如自鳴得意、勢利與虛偽等他們固有的特點。
像巴比特這樣的巴比特們在某種意義上說缺乏自知之明,而自鳴得意即是他們的一個顯著特點。生活在澤尼斯這樣的小城裡,他們為自己的小城感到無比自豪,相信澤尼斯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它完美無瑕,全世界都得效仿它。無疑,它有光輝燦爛的前景,而所謂澤尼斯精神——“為勝利而鬥爭的決心”鼓舞著它的居民們。他們也認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而他們作為這樣的一個完美無缺的名城的居民則是好公民,是百分之百的美國人。在這個城市裡,“男人威武豪放,女人溫柔嫻靜,孩子聰明活潑。”澤尼斯如此完美,任何譴責都是不懷好意的。事實上,不道德的風流韻事、謀殺犯罪就發生在他們的眼皮底下,可是他們不願承認。他們也不承認澤尼斯只是美國的一個小城,而且是一個世界上不值一提的無足輕重的地方。他們更不承認自己思想狹隘、沾沾自喜。所有這一切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人的心態是相符的。當時,美國人認為他們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民族是放射出銳氣、力量、進步以及支撐及教導世界的哲學原理的中心。”這也許就是辛克萊·劉易斯抨擊澤尼斯人自鳴得意的隱含目的。
與中產階級自鳴得意和勢利的特點結伴而行的是虛偽這一惡習。他們經常想,均是一套,做的卻是另一套。表面上,他們是標準公民、守法人士、有道德的正派丈夫,而背地裡卻與此截然相反。在禁酒年代,這些標準公民本應是這一戒律的衛護者,可他們卻在家自製啤酒大喝特局。他們對釀酒法非常感興趣,聚在一起的時候使互相交流。不僅如此,一有晚宴或聚會的時候,他們便想方設法弄到酒來招待客人,雖然這是違法的,而且價格比平時高得多。然後,在酒性掩飾下,他們大發勞騷,包括禁酒令,說這侵犯了他們的個人自由。但在公開場合,他們虛偽地贊成禁酒令,似乎在堅決執行。正如辛克萊·劉易斯對巴比特所指明的:“他贊成禁酒,但他自己並不身體力行;他稱讚限制汽車超速行駛的法令,但他自己並不遵守。”這一斷言對巴比特們的每個成員都是適宜的。被稱為標準公民的虛偽還從其虛假的道德上得到體現。外表上他們都是道德家——對妻子很忠誠,對孩子很慈愛,似乎沉浸在家庭生活帶來的幸福當中。而在內心深處,他們卻覺得受到家庭的限制,經常有逃脫的傾向。這就是為什麼巴比特要在他家人到達之前早幾天到緬因州去度假的緣故。在性生活方面,雖然他們的妻子很忠貞,可他們總在尋找與其他女人的風流韻事。在這方面,巴比特也可充當典型的例子。雖然他對妻子幾乎沒有愛情,但表面上還是很忠於妻子。而在內心深處,他經常沉溺於與想象中的夢中情人幽會做愛,還總是把這一夢中情人與自己周圍的女人對號入座。離開澤尼斯到外地去參加房地產董事會聯會時,他和其他標準公民一起去喝酒、看錶演、甚至到街頭去尋找“女郎”。最後,他揭開了虛偽的面紗,背叛了妻子,和寡婦丹尼廝混。通過保羅·賴斯靈的嘴,辛克萊·劉易斯揭示了巴比特的虛偽:“我的天哪,你對道德問題竟然看得這樣認真,老喬吉,我真不樂意去想,你骨子裡必然是不道德的。”
以上這些便是二十年代美國中產階級商人的特點,他們既標準化又一致化;既注重實利主義,又帶文化局限;既自鳴得意,又勢利虛偽。他們形成了標準城市澤尼斯的居民。應該注意的是,辛克萊·劉易斯在此用了提喻法,即以局部代表了全體。澤尼斯代表著全美國的小商業城市,而巴比特不只是一個人,而是所有中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巴比特)講述的不只是巴比特一個人的事,而是所有的巴比特們。一句話,辛克萊·劉易斯的抨擊帶有普遍性的意義。它是具體的,但在全美國國土上又是共同的、普遍的。
”在《巴比特》中,成段的細節描寫將人物的習慣行為生動而具體地展示給讀者,要諷刺生活就是要描寫生活,被嘲笑的東西必須同時被展現出來。作者總是自覺力求最大限度的真實可信,一字一句地向讀者提供生動詳盡的細節。他繼承發揚了以美國幽默藝術大師馬克·吐溫為代表的現實主義傳統,同時也吸收採用了英國文學諷刺大師狄更斯在小說中常用的縝密細緻、生動逼真的描寫手法。商人康拉德·萊特的外貌是這樣描寫的,“他眼睛底下有兩塊半圓形的凹窩,像是被銀元壓過之後留下的痕迹。”在描寫巴比特如何戒煙時,作者寫道:“他戒煙每月不少於一次,這一戒煙的過程和他身為殷實的市民,真可是相映成趣,他承認煙草有害,發了狠心,訂出了戒煙計劃,逐日減少吸煙次數,逢人必說修養德行的樂趣。兩個月前他畫了一張時間表,規定抽每一支的具體時間,欣喜若狂地把相隔的時間拉長,結果見到每天只抽三隻雪茄。可惜後來他的這張時間表也不翼而飛了。一星期前,他發明了一個新花樣,那就是把雪茄盒放在辦公室不常使用的抽屜里。”可過了不到三天,他又動不動就離開自己的寫字檯,走到柜子前,取出一支雪茄,就這樣,他總是故態萌發,還不停地找借口來安慰自己:“事實上,他樣樣都做到了,就是沒有戒煙。”
反語、幽默,本屬與諷刺相提並論的美學範疇,這種平行關係決定了它們之間具有彼此互相影響、滲透、交融的特點。反語、幽默可以輔助諷刺來更好地完成瓦解丑的任務。劉易斯的諷刺不是單一技巧的孤軍奮戰,而是充分調動一切可能的積極因素來共同抗敵。他常常在不同的場合,視不同的對象採用不同的藝術手段,使得以諷刺所達到的批評具有語氣上的或輕或重,否定程度上的或深或淺,充分表現出了統一性中的多樣性。反語往往是用讚美的肯定形式來表達批判的否定內容,不是鋒芒畢露,而是比較含蓄間接地傳情達意。“巴比特正如澤尼斯絕大多數市民一樣,認為他的汽車就是詩和悲劇,愛和英雄主義。”商人驕傲自滿,為自己有新建的洋房、新式的汽車和豪華的家居而沾沾自喜。正話反說的方式使尖刻的嘲笑戴上了含蓄的特點,語氣緩和而不失殺傷力。同時幽默做為“緩衝劑”在指責中加入了愛憐,那笑就像是大海的泡沫一樣閃亮卻苦澀。立體的、多面性的人物形象展示出來,讀者也將譴責的目光從人物個體轉向社會制度自身。
在小說中人物的自我暴露經常以這樣的可惡形式表現:他們不停地高談闊論,講述自己的觀點,聽起來好像有根有據,可講到最後往往是自相矛盾,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巴比特在一次演講中這樣表述自己對勞工問題的看法,“一個好的工會,它之所以有價值,就是因為它拒不接納那些破壞財產的激進工會。不過,可不應該強迫人家加入某個工會。所有企圖強迫人家加入工會的勞工鼓動者通通都得絞死。事實上,咱們關起門來說句話,任何工會都不應該單獨存在,與工會作鬥爭的最好辦法,就是每一個商人都應該參加僱主聯合會和商會。聯合起來就是力量嘛,所以我說凡是沒有參加商會的自私鬼就是非得強迫他參加不可。”讀者讀完這一段后想到的是巴比特本人的確應該被絞死。
劉易斯創作《巴比特》時,傳統斯文的現實主義和那種高雅、只供人消遣的浪漫主義文學創作方法已經過時,許多年輕作家紛紛另闢蹊徑、推陳出新。在《巴比特》中,他一方面力圖用自己文獻式的現實主義方式揭露批判現實生活的醜陋和虛偽;一方面大膽探索人性的內涵,在作品中表現為對巴比特行為的諒解同情,從而使作品帶上了明顯的復調特徵。小說到結束一直保持了這兩種矛盾的聲音,但正是這一復調特徵使作品獲得了不斷強化的情緒和震撼人心的力量。“巴赫金指出,一個作家,作為一個敘述人,也就是一個講故事的人,他不是一個全知全能的上帝,不可能把一切事情看得那麼清,把一切線索都理得那麼清,把一個個故事都講述的那麼完整,因為他自己的靈魂深處也有可能是割裂的,自相矛盾的,在他進行人物設計和情節講述中,可能會無意識地把自己的內心的矛盾在故事中流露出來,這樣不僅不是什麼壞事,因此也就可以把自己表露的更加深刻。復調小說,其實,就是指作者自己多個人格的對話。小說創作者樹立這種復調式的小說創作理念,其作品必然更能反映人性在現實社會的真實的狀態。”換言之,劉易斯這種復調敘述方式在再現人的矛盾和複雜的思想感情方面表現出獨特的魅力,使小說更加真實,從而讓劉易斯在當時美國多樣化的文壇中獨樹一幟。
這種復調敘述方式所具有的模糊性和泛指性遠比確定表達更具時空廣延性和藝術張力。“從藝術語言來看,未定性與空白就是一種無表達的表達,是對不可表達植物的反向表達,是通過對可疑表達之物的表達來暗含對不可表達之物的表達。”小說《巴比特》發生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美國。人們肯定當時的價值觀,都想發大財,想被人羨慕,想成為上流的一份子,這就導致了價值觀的單一性,從而導致社會只有一種話語,那麼只有受這種話語寵愛的少數幸運兒才會感到自我價值的實現,大多數人都會被這種價值觀所否定,而他們又找不到其他的價值觀讓他們得到精神上的依託,所以人們既愛之又恨之。對於這種模糊的心態,如果仍然要把它直接具體化,就會減弱作品的真實感。劉易斯的敘述方式就是對這種不可表達的的一種反向表達,儘管有時這種敘事方式不免有些模糊,但卻較好地襯托出人物內心世界的豐富性和複雜性,引導讀者在閱讀中去體驗這一複雜模糊的意境。
《巴比特》精確細膩地再現了美國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真實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刻畫出大眾文化對當時美國人生活方式的影響。真實生動地展現了20世紀20年代美國社會與文化。對美國小城市商界生活進行了有力的抨擊。
《巴比特》一書出版以來,影響極廣,主人公巴比特成了美國家喻戶曉的人物,一般字典都把“巴比特”作為新詞收入,用來形容當代美國典型的自以為是、誇誇其談、虛榮勢利、偏頗狹隘的市儈實業家。
英國作家沃爾坡而曾經說過:“劉易斯的勝利在於它成功地刻畫了巴比特,在毫不袒護他的愚行、勢利、誑騙等卑鄙行徑的同時,把他塑造成具體與我們自己同樣材料的人物。”
辛克萊·劉易斯的諾貝爾文學獎作品《巴比特》被稱為“美國經濟膨脹年代的史詩”。美國著名評論家亨利·路易斯·門肯評論道:“據我說知,還沒有哪一部小說能更準確地呈現真實的美國,這是一部高度有序的社會文獻。”
辛克萊·劉易斯(Sinclair Lewis,1885—1951)於1885年2月7日出生在明尼蘇達州的索克薩特鎮。父親是鄉村醫生,母親是一位醫生的女兒。劉易斯自幼性格內向,勤于思考,酷愛狄更斯、司各特等人的文學作品,長於細心觀察社會生活,這為他日後的文學創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他的業餘時間全在公共圖書館里看各種書籍,他從小還喜愛偷偷地記日記,把他對家鄉古老小鎮上的印象和見聞記錄下來,這些對他以後走上文學創作道路帶來了極大的影響。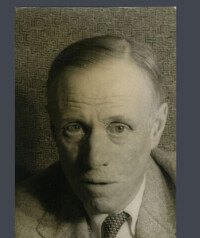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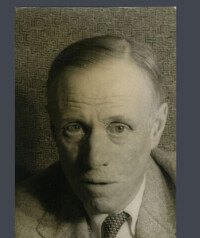
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