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誠
原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顧誠(1934年11月-2003年6月25日),男,江西南昌人,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原教授,博士生導師,明清史專家。1949年前,分別就讀於江西省立吉安中學、南昌一中。早在建國初期,顧誠先生就參加了革命工作。1957年9月,顧誠考入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1961年畢業留系任教,此後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會副理事長、顧問,中國明史學會常務理事。
顧誠(1934.11-2003.06.25),男,江西南昌人,有國際聲譽的當代明清史專家,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原教授、博士生導師。生前僅有兩部專著面市:《明末農民戰爭史》獲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南明史》獲國家圖書獎和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顧先生生性耿直,視學術為生命,孤燈長夜,治學謹嚴,是當代考實之學的傑出代表,在明帝國疆域管理體制(衛所制度)、人口、耕地及明清易代史事(南明史)等領域均有精深獨到的研究,學術成果和歷史結論在明清史學界具開創和奠基意義。先生還是學界公認的“三好”學者:外語好、學問好,文筆好。翻開一部專著或論文,即開啟了一段美好而難忘的史學歷程。
他在《明前期耕地數新探》(註:《中國社會科學》1986年第4期。)、《明帝國的疆土管理體制》(註:《歷史研究》1989年第3期。)和《衛所制度在清代的變革》(註:《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8年第2期。)三篇文章中詳細闡述了明初全國土地分屬於行政系統和軍事系統的觀點,認為明代軍事系統的都司、衛所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也同行政系統的基層組織——州縣一樣是一種地理單位,管轄著大片不屬於行政系統的明帝國疆土。洪武二十六年官修《諸司職掌》中所載近850萬頃土地包括軍事系統管轄的土地,軍事系統管轄土地包括軍士的屯田和代管民籍人口耕種的土地。軍事和行政兩大系統之間具有可轉換性,總的趨勢是從都司、衛所轄地內劃出一部分設立州縣,但衛所轄地行政化在明代進展有限,這一進程直到清代才告完成。部分衛所轄有大片疆土的觀點最早由解毓才在《明代衛所制度興衰考》(註:《說文月刊》1940年第2卷。)一文中提出,解先生稱之為“實土衛所”。顧誠的研究將此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在此基礎上,顧誠又發表了《談明代的衛籍》(註:《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9年第5期。)一文,對衛所管理的衛籍人口以及衛籍人口與州縣軍戶之間的區別與聯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顧誠教授對明代衛所制度的基本觀點主要體現在四篇文章,即《明前期耕地數新探》(《中國社會科學》1986年第4期)、《衛所制度在清代的變革》(《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8年第2期、《明帝國疆土管理體制》《歷史研究》1989年第3期和《談明代的衛籍》《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9年第5期)這四篇文章系統論證了明朝疆域管理的“兩大系統”理論,即行政系統(縣、州——府、州——布政使司、直隸府州——六部)和軍事系統(衛、直隸都司的千戶所——都司、行都司、直隸衛——五軍都督府)各自管轄兩種不同的“地理單位”,都司衛所是具有獨立管轄權的“地理單位”,管轄田地、人口不隸屬於司府州縣。這一理論涉及到明代社會經濟領域中的許多重大問題,一是明帝國的耕地數,二是明代的官田數,三是清代耕地數與明代田畝數的比較,等等,並涉及明代人口管理,尤其是軍戶管理問題(衛籍)等。顧先生曾計劃圍繞衛所制度對明朝相關領域的影響到清代的改制進行綜合研究,形成一部專著(顧誠:《我與明史》,載《顧誠先生紀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91-404頁),惜不幸病逝,未克完成。可以說,顧誠先生以四篇論文揭示了明代衛所制度的基本屬性及其在明朝管理運行中所處的地位和作用。他的明朝疆域管理理論,對把握明清兩代田地、戶籍等管理體制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明末農民戰爭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10月。
《南明史》,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5月。
《南明史》,光明日報出版社,2011年8月。
《明末農民戰爭史》,光明日報出版社,2012年1月。
《明朝沒有沈萬三:顧誠文史札記》,光明日報出版社,2012年10月。
《隱匿的疆土:衛所制度與明帝國》,光明日報出版社,2012年10月。
《李岩質疑:明清易代史事探微》,光明日報出版社,2012年11月。
《李自成起義軍究竟從何處入豫?——同姚雪垠同志商榷》,《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78年第4期;
《李岩質疑》,《歷史研究》,1978年第5期;
《再談李岩問題》,《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79年第2期;
《“古元真龍皇帝”試釋》,《歷史研究》,1979年第8期;
《從永昌元年詔書談到李自成何時稱帝》,《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0年第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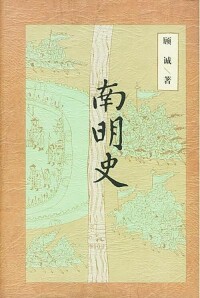
顧誠著《南明史》
《明初的兩道諭旨》,《紫禁城》,1982年第2期;
《清初的遷海》,《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3年第3期;
《論大順政權失敗的主要原因》,《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3年第6期;
《王世貞的史學》,《明史研究論叢》第二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頁331-346;
《關於夔東十三家的抗清鬥爭》,《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5年第3期;
《明前期耕地數新探》,《中國社會科學》,1986年第4期;
《衛所制度在清代的變革》,《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8年第2期;
《明帝國的疆土管理體制》,《歷史研究》,1989年第3期;
《談明代的衛籍》,《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9年第5期;
《靖難之役和耿炳文、沐晟家族——婚姻關係在封建政治中作用之一例》,《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92年第5期;
《順治十一年-明清之爭關鍵的一年》,《清史論叢》1993年號;
《沈萬三及其家族事迹考》,《歷史研究》,1999年第1期;
《南明史》(英文)》,《SocialSciencesinChina》,1999年第1期;
《我與明史》,《社會科學評論》,2003年第1期。
陳梧桐《顧誠印象》
得知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顧誠教授病重住院,正值北京非典型性肺炎高發時期,一直未能前去探望。非典疫情解除后,我和王春瑜先生約好在6月25日下午去北醫三院看他。沒想到當天中午接到電話,說顧誠先生已在十一點零五分去世,我們失去了在他生前再見一面的機會,心情極為沉痛。
我認識顧誠先生,緣起於1981年西安召開的中國農民戰爭史學術討論會。在會上聽他發言,聲音低沉平穩,不急不慢,像個老學究,但條分縷析,有理有據,令人信服。會下交談,覺得他書讀的多,學識淵博,而又胸懷坦蕩,為人正直,值得信賴。返京后,開始同他來往。當時我正研究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他則研究明末的農民戰爭,涉及到明朝的一頭一尾,有許多共同感興趣的話題,接觸慢慢就多了起來,彼此互相熟悉,成為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在二十多年的交往中,顧誠先生給我最深的印象,是他刻苦的治學精神。正如他所說的:“在學術問題上要取得真正的進展,需要經過研究者長年累月的辛勤勞動。”任何學者的每一項成就,都離不開“刻苦”二字。但顧誠先生的治學,不是一般的刻苦,而是長年累月、異乎尋常的刻苦。他曾同我談起,說自己年輕時,白天經常一大早就騎著自行車,到城裡各大圖書館和檔案館去看書、查資料。為了節省時間,中午啃個自帶的干饅頭充饑,直到閉館才回家。不管是盛夏還是嚴冬,從未停止。寒冬臘月,有時朔風怒吼,雪花飛舞,握著車把的雙手凍麻木了,就到街邊商店裡的火爐邊烤烤。去的次數多了,許多圖書館和檔案館的管理人員都認識他。到了晚上,他則在燈下整理抄回來的資料,或者撰寫論著。干著干著就忘了鐘點,常常是到了後半夜,周圍的宿舍都早已滅燈,他才就寢。由於長期白天黑夜連軸轉,腦子高度亢奮,很早就落下個失眠症,起初是要到夜裡三四點鐘才能人睡,後來則要待到東方發白才能入眠,而且還得服用安眠藥才能睡著。久而久之,生物鐘完全顛倒,形成了晚上工作、上午睡覺的習慣。系裡知道顧誠先生的這種習慣,把他的課都安排在下午或晚上來上,以免影響他的休息。開夜車對許多知識分子來說是家常便飯,但一般是開到十二點或一、二點,長年累月地通宵開夜車,誰也受不了。記得有一次到香港大學參加明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我和顧誠先生同住一屋。第一個晚上我還能陪他聊到夜裡四點,第二個晚上我只能陪他聊到夜裡二點,第三個晚上聊到十二點我就睡著了,但他仍然在燈下看書,直到四點才熄燈就寢。
顧誠先生治學還有一個突出的特點,那就是學風極其嚴謹,富有樸學精神。不論研究什麼課題,顧誠先生都力求將有關的資料搜集齊全,做到“竭澤而漁”,沒有遺漏。他不僅跑遍北京各大圖書館和檔案館,還利用各種機會到外地去搜尋資料,其足跡遍及於大江南北。為撰寫《明末農民戰爭史》,他僅方誌就查閱了近千部。他撰寫的《南明史》,僅引用書目就達到579種,查閱而未徵引的書目則是此數的幾倍。所引之書,有不少是謝國楨先生《晚明史籍考》列為“未見之書”或未加記載,系由顧誠先生首先發現並首次徵引的史籍。我幾次拜訪顧誠先生,在他書房見到桌子上擺著幾大摞一尺多高的稿紙,他告訴我那都是從圖書館和檔案館摘抄下來的資料。他不用卡片抄資料,說卡片抄不了幾個字,而是用稿紙抄,一張稿紙不夠就再加一張二張,可以完整抄下一大段資料。想想看,這幾大摞一尺多高的資料,用筆一個字一個字地抄寫,得花費多少時間和精力啊!也就因此,顧誠先生的論著不僅資料豐富、紮實,真正做到“言必有據”、“無一字無出處”,而且每每有新發掘的資料,和基於這些新資料而提出的新見解。但是,顧誠先生決不是個文抄公,他的論著也決不是資料長編。顧誠先生具有深厚的學術功底,特別是具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素養。他並不滿足於“言必有據”、“無一字無出處”,而是志在創新和突破,力求解開一個個歷史謎團,探明歷史事實之真相,闡述社會發展之規律。因此,他對搜集到的資料,都下功夫逐一進行認真的審核、辨析和考證,做到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然後以此為基礎,運用唯物史觀進行深入的分析和論證,進而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在顧誠先生的筆下,許多史籍記載的訛誤得到了訂正,許多前人不曾解開的謎團被解開,許多流行的觀點被否定;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條條確鑿可靠的資料,清晰明朗的歷史發展線索,獨到新穎而又令人信服的觀點。也就因此,顧誠先生的許多論著成為學術精品的典範,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廣泛讚譽。他的《明末農民戰爭史》,榮獲了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他耗費十餘年功夫的嘔心瀝血之作《南明史》,更被譽為南明史研究的里程碑,而榮獲中國國家圖書獎和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顧誠先生的史識和史才令人欽羨,他的史德更是令人敬佩。顧誠先生一生淡泊名利,甘於寂寞,專心治史,任憑商品大潮如何衝擊,坐冷板凳的決心從不動搖。自從1981年我到他家拜訪起,二十多年來他都住在校內那套只有七十多平方米的舊樓房裡。那套住宅沒有門廳,只有三間房子,其中一間小屋僅有六平方米,兩間稍大點的各有十幾平方米。他的書房是一間稍大點的房子,裡面除了擺放一張單人床、一張書桌和一張短沙發之外,就沒有多少空餘的地方,靠牆的書櫃和書架塞滿了書,就連床上挨著牆邊的地方法也擺了不少書。顧誠先生曾告訴我,說學校曾分給他校內一處較大的房子,他去看了,是處舊房,四壁斑駁,門窗破爛,要搬過去,得先花幾萬元進行裝修;他拿不出這麼多錢,只能作罷。後來學校又分給他校外一處寬暢的新房子,但考慮到那裡離學校較遠,一旦搬過去,就無法泡學校的圖書館,他還是放棄了。由於顧誠先生學識淵博,享有盛譽,海內外許多大學和研究機構,紛紛邀請他去講學。在許多人看來,這是名利雙收的大好事,但他把名利看得很淡,都以生活習慣特殊為由婉言謝絕,繼續埋頭從事自己的研究工作。可以說,顧誠先生真是全身心地投入他所鍾愛的史學研究之中,治史之外,別無所求。他這種清苦自持、安貧樂道、與書為伴、專心治史的精神,在當前人慾橫流、風氣浮躁的社會轉型時期,尤其顯得難能可貴。
顧誠先生頗為重視史德。招收研究生,開門第一課,就是教學生坐冷板凳的功夫,於純潔學風多所致意。他一直強調,做學問是一件苦事,非甘於寂寞,肯下苦功者不能為。他言傳身教,常雲自己過去經常出入圖書館,中午帶一饅頭充饑,直至閉館收書才回家。冬天寒冷,騎自行車雙手常被凍得麻木,為了不影響看書,就到附近商店的火爐烤火取暖。他為國家培養了不少博士、碩士研究生,堪稱“學為人師,行為世范”的楷模。
在《南明史》寫作和修改的過程中,顧誠先生曾發表過《明帝國的疆土管理體制》、《明前期耕地數新探》、《談明代的衛籍》、《衛所制度在清代的變革》四篇重要論文,就明代的疆土管理體制、衛所制度和耕地面積、人口數字,提出了自己的新見解。他曾對我談起,他在研究明末農民戰爭和南明史的過程中,曾從大量史籍、檔案特別是地方志中,搜集到許多有關明代衛所的資料,涉及明代疆土管理體制的問題。而明代的疆土管理體制,正史和政書的記載卻又含混不清,引起許多人的誤解。有關明代的疆域、耕地面積和人口數字,學術界之所以看法不一,爭論不休,皆與此有關。這是明史研究中不可迴避而又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他的四篇論文就這個問題提出自己的基本觀點,準備先聽聽學術界的反映。待《南明史》付梓之後,將集中精力再寫一部專著,系統地闡述自己的看法。但天不假年,長年累月的刻苦鑽研,損害了顧誠先生的健康。他僅得中壽便與世長辭,未能實現完成第三部大作的願望,實在令人痛感惋惜。
原載《博覽群書》2003年第9期,頁48-50。
顧誠先生刻苦治學,學風嚴謹,富有樸學精神。他興趣廣泛,既對中外歷史多有涉獵,又學有專門,是我國享譽海內外的明清史專家。自1978年在《歷史研究》發表《李岩質疑》一文之後,他寫了多篇關於明清史研究方面高質量的學術論文,受到史學界的矚目。他著有《明末農民戰爭史》、《南明史》(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出版)等專著,均為明清史研究領域最高學術水平的著作。《明末農民戰爭史》一出版,為農民戰爭史研究別開實證蹊徑,獲得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尤其是他所著的《南明史》一書,是他花去十多年時間的嘔心瀝血之作,是南明史研究的里程碑,在海內外已有廣泛的影響,並榮獲了中國國家圖書獎和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他很少去探討那些比較偏僻的問題,所作大多是既利於科研的進展,又利於課堂教學這方面課題的研究,其目的是為了提高歷史教學的水平,諸如《明帝國的疆域管理體制》、《明前期耕地數新探》、《談明代的衛籍》、《順治十一年--明清相爭關鍵的一年》等文章,所涉及到的明帝國的版圖、明帝國對疆域的管理、明朝究竟有多少耕地、人口多少和人口的分佈情況,以及明清易代等問題,都是在歷史教學中必須解決的問題。
他為了寫《明末農民戰爭史》一書,長期沉浸於圖書館的書海中,查閱的地方志,幾達1000多種,另外還包括很多正史、野史、文集、筆記、檔案方面的資料。
回顧顧誠先生一生,道德文章,擲地有聲。天不假年,僅得中壽,但其人其事當隨其著作之長存而永駐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