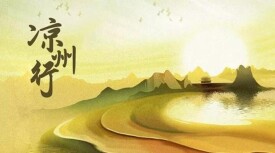涼州行
涼州行
《涼州行》是唐代詩人王建創作的一首樂府詩。此詩描寫當時被回紇徠侵踞的涼州的邊防情況,同時批評了洛陽城中的達官顯貴,表達了詩人對昔日大唐王朝國勢日趨衰落而國人沉迷歌舞宴樂的擔憂,同時客觀地反映了胡漢民族的經濟、文化交流情況。全詩語言通俗,用韻講究,韻腳轉換與詩意段落嚴格對應。
涼州行
涼州四邊沙皓皓,漢家無人開舊道。
邊頭州縣盡胡兵,將軍別築防秋城。
萬里人家皆已沒,年年旌節發西京。
多來中國收婦女,一半生男為漢語。
蕃人舊日不耕犁,相學如今種禾黍。
驅羊亦著錦為衣,為惜氈裘防斗時。
養蠶繰繭成匹帛,那堪繞帳作旌旗。
城頭山雞鳴角角,洛陽家家學胡樂。
皓皓:曠達貌;虛曠貌。《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常以皓皓,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漢桓寬《鹽鐵論·西域》:“茫茫乎若行九皐未知所止,皓皓乎若無網羅而漁江海。”唐裴鉶《傳奇·陶尹二君》:“凌虛若有梯,步險如履地,飄飄然順風而翔,皓皓然隨雲而升。”
旌節:古代使者所持的節,以為憑信。《周禮·地官·掌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鄭玄註:“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孫詒讓正義:“《後漢書·光武紀》李注云:‘節,所以為信也。以竹為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為其毦,三重。’……《司常》云:‘析羽為旌。’旌節,蓋即以竹為橦,又析羽綴橦以為節。其異於九旗者,無縿斿也。漢節即放古旌節為之,故鄭舉以相況。”唐楊炯《建昌公王公神道碑》:“乘使者之輶車,掌行人之旌節。”
蕃人:中國古代對外族或異國人的泛稱。蕃,通“番”。唐姚合《窮邊詞》之二:“箭利弓調四鎮兵,蕃人不敢近東行。”明茅大方《送李曹公出鎮西域》詩:“紫駝白馬蕃人貢,赤黍黃羊漢卒屯。”
涼州城的四周已是廣袤無垠的茫茫黃沙,因為朝中沒有驍勇之將開拓西域通道,開疆拓土。
涼州城所屬各縣都已為胡兵所佔據,守邊將士只好另外建築秋天防禦的城堡。
萬里從征的人都已戰死在邊塞上,可是京城裡還在年年發令輸兵。
入侵的胡人都從中國擄去婦女,其中有半數婦女生了男孩,還能說漢語。
這些胡人從前不懂農作,不犁地耕種,如今卻學漢人種起禾稷稻麥等糧食作物來了。
胡人現在牧羊的時候也穿了絲織的錦衣,卻愛惜他們原來的毛氈和獸皮而把它們收藏著,為了預備作戰時用。
他們現在也能養蠶繰絲,織成一匹一匹的絹帛,卻是用來做旌旗圍繞在營帳四周。
城上的山雞已經在角角地報曉,而洛陽城中,家家都還在演奏胡樂呢!
唐大曆年間,河西節度使治所涼州(今甘肅武威)州城被回紇所侵踞。當時藩鎮割據嚴重,軍閥們擁兵自立,朝廷無力收復失地,淪陷區人民被同化奴役。王建深入了解了當地的人民的疾苦后,有感於此,憤而作此詩。
第一、二句是倒裝句,“漢家”即指唐朝。“舊道”是指開元、天寶年間的西域通道。因為現在無驍將能開拓邊疆,以致涼州城外又是黃沙浩浩。
下四句說涼州所屬各縣都已為胡兵所據,守邊的將軍只好另外建築防秋的城堡。西北胡人常常在秋季入侵中國,唐朝在每年秋季都要向河洛、江淮一帶徵發兵士,到西域去增防,當時稱為“防秋”。這些萬里從征的人都已戰死在邊塞上,可是京城裡還在年年發令輸兵。“旌節”指發兵的符節,“西京”即首都長安。張籍有《西州》詩一首,也描寫這些情況。
下四句說入侵的胡人都從中國擄去婦女,其中有半數婦女生了男孩,都能說漢語。這些胡人從前是不懂農作的,如今卻學漢人種起禾黍來了。“蕃人”即“胡人”,唐宋人寫作“蕃”,明清人寫作“番”。
再下四句說這些胡人,現在牧羊的時候也穿了絲織的錦衣。他們本來是披毛氈或獸皮的,但現在卻愛惜氈裘,把它們收藏著,預備作戰時用了。他們現在也能養蠶繰絲,織成一匹一匹的絹帛,卻是用來做旌旗圍繞在營帳四周。這裡的“那將”二字用得較為少見,不知有無誤字。“那”,大概可以作“挪”字講,“那將”,猶言“拿來”。
最後二句說,城上的山雞已經在角角地報曉,而洛陽城中,家家都還在演奏胡樂呢。
這首詩的主題是表現涼州淪陷、回紇入侵之後,胡人日漸漢化,而漢人卻胡化了。胡人的漢化,是學習漢人的農桑生產,以加強他們的武備;漢人的胡化,卻只是學習胡人的音樂歌舞,作長夜荒淫的宴樂。
這首詩的韻法也真有些“出格”。全詩共十六句,如果四句一韻,可以使韻法很整齊,但作者卻以開頭二句為一韻,末尾二句為一韻,中間十二句用三個韻。這樣,使讀者不能在開頭的時候就依照四句一絕的規格讀下去,似乎有些不順口。但是,如果仔細研尋詩意,可以體會到作者是按詩意配韻的。首二句點題,用一個韻。次四句描寫涼州之荒蕪和胡人的猖獗,也用一個韻。以下兩組各四句,分寫胡人也從事農耕和蠶織,各用一韻。最後寫洛陽城中漢人之胡化,以為對比,又另用一韻。韻腳的轉換,應當和詩意的段落配合,這個原則,作者沒有違背,但如果首韻和尾韻的詩意,都能擴大為四句,這首詩的韻法就整齊了。尤其是尾韻,如果有四句,則詩意的對比性可以更為明顯,現在,作者匆匆以二句表過,讀者往往會忽略了它的諷喻意義。
《唐風定》:
此篇氣骨頓高,諷刺深婉。
《載酒園詩話又編》:
《涼州行》曰:“驅羊亦著錦為衣,為惜氈裘防斗時。”《溫泉宮行》曰:“禁兵去盡無射獵,日西糜鹿登城頭。梨園子弟偷曲譜,頭白人建教歌舞。”……亦透快而妙。
王建(約767-約830年),唐代詩人。字仲初,潁川(今河南許昌)人,出身寒微。大曆進士。晚年為陝州司馬,世稱王司馬。又從軍塞上。擅長樂府詩,與張籍齊名,世稱“張王”。其以田家、蠶婦、織女、水夫等為題材的詩篇,對當時社會現實有所反映。所作《宮詞一百首》頗有名。有《王司馬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