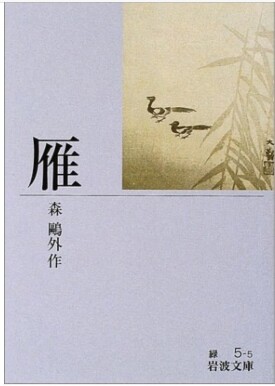共找到9條詞條名為雁的結果 展開
雁
森鷗外著中篇小說
《雁》是日本作家森鷗外創作的中篇小說,連載於明治四十四年(1911)九月號至大正二年(1913)五月號的《昂》雜誌上,1915年以單行本刊行。 《雁》描寫明治年間一個貧苦的少女淪為高利貸主的情婦;她渴望擺脫這種屈辱的境地,暗自愛上一個每天從門前經過的大學生,但由於一個偶然的原因,失去了表白愛情的機會,她追求幸福的努力終於化為泡影。作者懷著同情寫出一個普通婦女的不幸,但卻把這種不幸歸結為偶然性的惡作劇,最後用一隻碰巧被飛石擊斃的雁來象徵她的命運。日本評論家認為,作品的心理刻畫細膩,人物、場景描寫逼真。
《雁》描寫的是少婦阿玉的愛情悲劇,阿玉原是天真無邪、容貌秀美”的少女,早年喪母,與其老父相依為命,因生活所迫,她先是受騙嫁給了一個有妻室的警察,后又嫁給高利貸者末造為妾,兩次不幸的婚姻給她純潔的心靈帶來了極大的創傷,由於境遇的不斷改變,以及世態炎涼的折磨,使她逐漸認識到了自己的價值,她開始自我覺醒,尋求自己的生活道路。這時,一位醫科大學的學生岡田偶然間闖入了她的生活,阿玉從對岡田一般的好感逐漸轉為深深的愛慕,從岡田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希望,急切盼望岡田把她從感情的苦海中拯救出來。然而,由於一些仍然事件的干擾和岡田的“不覺”,使她失去了一次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幻想破滅,結束了這一場沒有“戀愛”的愛情故事。
《雁》創作於明治時代末期與新時代交替期,小說中的事件與人物取自鷗外青年時代的見聞。森鷗外本名為森林太郎,他不僅作為大戶人家的長子,承載著家族未來的希望,而且身負要職,由此放棄了德國的一段戀情。他當時考慮的是家族和國家的利益,放棄了個人的自由權力。但其內心並不能接受這些。正是那段異國生活體驗使他逐漸萌生了近代自我意識。森鷗外在遺言中談到死後想以森林太郎為名,墓碑上也只要求刻上森林太郎之墓幾個字。可見他想以真實的自我結束人生。《雁》中阿玉與森鷗外的思想軌跡存在重合之處,他在刻畫阿玉的同時發出了壓抑於內心深處的吶喊聲。 1911年,感情的折磨使森鷗外操筆創作小說《雁》的創作。
阿玉
貧民的獨女阿玉,是一個富有自我犧牲精神的女性。其母早亡,她和靠做糖泥人糊口的老父相依為命。阿玉自幼立誓:將來若能時來運轉,定讓父親晚境幸福! 為盡孝,鮮活水靈、天然美貌“勝於出水芙蓉”的阿玉,繼被無賴警察欺騙之後,又違心地做了所謂“出色實業家”末造的小妾。阿玉住進了“無緣坂”的妾宅,由此而讓父親享上了清福。然而 ,阿玉卻痛感“自己的這種喜悅中,混進了一滴苦汁”。阿玉出賣了不該當商品出賣的自己,阿玉苦澀地抹消了人生欲求和人的權利,將自己下而降至與金錢等價交換的“物”。
她搬至“無緣坂”第三日,魚店老闆罵道:“我的魚不賣給放高利貸者的小老婆!”阿玉此時才察覺:自己竟是被人嫌惡的放高利貸之人的小妾!精神遂受刺激,開始怨恨自己的命運。此後,平素“含羞臉紅、謹慎而面帶微笑地給末造斟酒”的阿玉,對末造的印象漸趨複雜。
阿玉的覺醒,發生在察覺末造乃寄生式金融業者之後,她滿腹苦水無處吐 ,極端苦惱的結果,“奇妙地精神振作起來”,覺醒之青芽悄然萌生,“她飽受世間壓迫,走投無路。走投無路促使她逐步覺醒”。阿玉恣放想像 ,嚴密思索,周密籌劃,以期實現改變自己命運的願望。
秋季到來,阿玉敏感的雙目捕到了一個理想目標——風度翩翩、充滿自信又具文學氣質的醫學部大學生岡田。阿玉和窗外的岡田偶然目光相撞,遂送去嫣然一笑。然而,阿玉萬沒想到,由於最後一次“偶然”和自己的命運,她的理想徹底破滅了。
岡田
岡田是醫科大學的高材生,他立於明治文明開化的潮頭,肩負日本社會發展的未來。
關於岡田的性格小說開篇處有所揭示“至於品行如何,我想,當時很少有人像岡田那樣過著規規矩矩的學生生活”。由此顯現出嚴格遵守規則的讀書人形象。這種氣質正是吸引阿玉傾慕之心的緣由。而且也可看出他屬於思想傳統保守的書生。這種個性與其選擇留學的結局如出一轍。
阿玉生存於日本近代社會的他者境遇中。自我,只有在於某些對話者的關係中,我才是自我。因而,“自我”體現於與周圍人的關係中,《雁》中阿玉的命運與父親、末造及岡田的意識形態有直接關聯,阿玉的“自我”在這種關係中受到抑制。
阿玉由最初對於身世命運的屈從轉變為積極追求幸福的姿態,對於幸福的內涵理解逐漸明晰化。這種轉變本身展示了女性自省中的內心蛻變。文中通過自由直接引語敘述了其心理轉變:“自己固然沒受過什麼教育,身無一技之長,但成為末造的玩物,心又不甘。看著來來往往的學生,心想:難道就沒個可靠的人,能把我從眼前的境遇中救出來嗎了。”當岡田解救了籠中的紅雀,阿玉由此確信看到了希望之光,於是積極尋找契機與岡田交往,但冷峻的現實最終讓她處於無望的等待中。小說中刻畫的是一個生活於沒有人去大聲呼籲女性人權、解放女性的歷史年代,卻意識到自我並開始追尋自我的女子形象。文本結尾處描述到“她的面容如同石頭一般凝然。睜得大大的一雙美目,蘊含著無限的遺憾”。可見,阿玉是美麗的,也是孤獨的。其美麗不僅在於外表,更在於在他者境遇中自我追尋的人生態度。明治10年左右的時代,封建意識仍舊籠罩於民眾的心頭,作為一名普通弱女子敢於改變自己的命運追求幸福,令人感嘆。
同時,該作並非旨在僅描寫阿玉一人,而是通過其命運展現出日本近代女子的悲劇性人生軌跡。那隻不幸喪命的大雁不僅象徵了阿玉命運的悲苦,還代表了生活於困境中的女子群像。
小說中交織有江戶風俗文化的社會場景描寫,如關於明治10年(1876年)左右的本鄉、下谷、神田一帶的地理風俗人情等都做了細膩描繪。這正暗示著當時所處的交替時期的歷史背景。明治維新之後不久,民眾思想中仍殘留有傳統落後觀念的烙印。據資料記載,江戶時代中期之後,開始廣泛流行淺顯易懂的女訓書,並普及於民間。該書作為女性必讀的修身書,其基本思想是從男人立場出發,告誡女性丈夫的家才是真正的家。一個女性一旦結婚為人妻,丈夫就成了她的世界,她就成了這個家的女僕。近代日本女性地位雖比封建社會大為改觀,但從根本上說尚未擺脫被壓迫的境地。婦女在法律上處於無權地位,《明治民法》維護男尊女卑的原則,婦女在法律上的人格受到蔑視。可見,雖進入明治時期,民眾心中仍存有傳統的男權思想。阿玉的悲苦命運正是那個時代女子追求自由戀愛的“個人主義”與保守的封建觀念之間矛盾尖銳性的反映,即顯現出“近代與封建”矛盾性。
隱喻
小說的題目以“雁”為名,暗示著雁的命運即人物的命運,雁的死象徵著小玉愛情的破滅,追尋自我的失敗。同時,有學者指出:日語中“雁”的發音與“癌”相同。對放高利貸的人也可稱其為“癌”。因為他們和這種病一樣執拗,很難醫治。因此,作者對於題目可以說是獨具匠心。除此之外,與“雁”發音相同的“癌”同樣象徵著封建社會思想中的毒瘤。它逐漸地侵蝕著人們的思想,壓迫女性的獨立自主,這也是釀成這場愛情悲劇的根源所在。
小說以一個有些荒謬的故事切斷了小玉與岡田之間的姻緣。岡田在朋友石原的慫恿下拿起石子打遠處休息的大雁。雖然有些不情願,可是石子卻真的意外擊中了一隻大雁。這隻死去的大雁象徵著小玉追求幸福的失敗,對岡田的愛情的隕落。大雁有著翅膀,沒有前文中紅雀的鳥籠,有自由、廣裹的天空飛翔。然而,命運的偶然卻折斷了這自由的翅膀,使得振翅覺醒的大雁隕命。為了這隻意外死亡的大雁,岡田、石原和“我”三人不得不將其掩藏好帶回家。回去的途中,發現小玉正站在門外等待著岡田。可是顧忌身邊有其他人,亦或是岡田決心赴德留學從此切斷與小玉之間的聯繫,岡田沒有理會她。小玉錯失了最後的機會,同時也更加清醒地認識到她與岡田之間註定擦肩而過。
景物描寫
《雁》中的景物描寫具有象徵性表現效果,凸顯出悲劇性宿命的暗淡。文本中敘述到岡田每日傍晚外出散步,且路線幾乎固定不變,其中一條小道名為“無緣街”。該名稱里似乎隱含有悲戀結局。岡田是近代知識青年,他通往的道路面向未來的光明,與阿玉的人生境遇形成對照。而那條街暗示二人無緣的關係,似乎兩者之間存有難以逾越的鴻溝。
起初岡田見到阿玉的場景中有如此描述:“正當他走到門前時,萬年青的花盆上,深鎖在灰暗的背景中,浮現出一張白凈的面龐”。這一情景似乎呈現出兩人各自所處不同身份背景的差異性。文中描述了阿玉居住的環境氛圍,如“只記得在無緣街的一側房屋中,最熱鬧的裁縫家隔壁,總是打掃的很乾凈的那戶冷冷清清的人家,在下水道蓋子總壞的那一帶,有一戶光線昏暗的人家,常年門半掩著”。小說原文中的“寂寞”及“薄暗”、“微暗”等詞語正顯現出她所居住的環境充滿孤寂和黯淡,那種微暗色彩象徵著近代日本的黎明。即從江戶時代過渡到明治時期生存於社會底層的人們生活中籠罩著的灰暗之色。這種灰暗也與寂寞感交織著。因而,有日本學者將阿玉的人生境遇定位為“阿玉是從江戶以來處於底層民眾的微暗,孤寂的世界里開放的美麗孤寂的花朵”。
巧合
森鷗外在作品中,把一個個偶然事件同表現作品主題緊密聯繫起來,極其自然地構成了作品的主線,推動情節的發展。貌似偶然,實則必然,必然寓於偶然之中。
“我”與岡田的接近就是由一個偶然之事促成的。“我”在古舊書攤買到了一本岡田也想買的《金瓶梅》,並說好看完之後借給他,從此“岡田和我開始有了來往”,而這本書後來又成為岡田幫助阿玉斬蛇的誘因。岡田因整個半天都在讀那本《金瓶梅》,感到頭腦恍惚,便習慣地到無緣坡散步,正巧遇見蛇要吃掉阿玉飼養的一對小紅雀,他便奔向前去章刀砍死了蛇,救出了小紅雀,從而導致了阿玉與岡田相識已久后的第一次交談,使阿玉對岡舊更加迷戀。這是一個偶然事件帶來的巧合。“無巧不成書”,《雁》中充滿了這種巧合。
日本文學評論家吉田精一:這部作品是“鷗外長篇現代小說中的唯一完成之作,寫作手法之巧妙在鷗外所有的作品中是屬一屬二的”。
森鷗外,日本明治、大正年代作家、翻譯家、文學評論家,與夏目漱石並稱為“日本近代文學雙璧”。森鷗外同時是一名軍醫,曾擔任日本軍醫最高職位陸軍省軍醫總監,晚年擔任日本帝國美術院院長。他的一生跌宕起伏,閱歷豐富。幼年時代即在私塾學習四書五經等漢文經典,少年時代學習醫學、德語,後進入東京大學醫學部,畢業后成為軍醫。青年時代受陸軍省派遣留學德國,接觸到當時最先進的醫學技術和文學、哲學領域;回國后擔任軍醫教官,同時活躍於日本文壇,並參與文壇的幾次重大理論論爭,是日本近代文學的奠基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