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找到2條詞條名為多元文化主義的結果 展開
- 美國一種政治和社會理論
- 李麗紅所著書籍
多元文化主義
美國一種政治和社會理論
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是近二十多年來活躍於美國學術界、教育界和政治界的一種政治和社會理論,對美國的傳統信條(American Creed)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從而引起兩種價值觀的激烈交戰。
它們不僅挑戰了美國強勢群體的威嚴,而且打到了美國傳統勢力的痛處。更重要的是,它們觸動了美國主流文化的根基,踩到了美國WASP的尾巴。不管是出於政治考慮還是出於社會正義,也不管是出於群體利益抑或是反叛心理,上至政府機構、公眾輿論,下至草根社區、家庭學校,人們都大談特談多元文化主義,真有點言必稱“多元”的味道。於是,什麼東西都多元起來了:價值觀多元起來了,道德標準多元起來了,生活方式多元起來了,授課語言多元起來了,婚姻形式多元起來了,家庭模式多元起來了,性行為多元起來了,等等,不一而足。
文化多元和多元文化主義

相關資料
那麼,什麼叫多元文化主義呢?也許是由於該詞被用得太多、太泛、太隨意,它直到目前為止尚未有一個界定分明、一致公認的定義。可以這麼說,“多元文化主義可以指任何東西,也可以什麼都不指”,它完全取決於使用該詞的人在談論什麼問題,以及在什麼語境下談論有關的問題。所以,使用該詞時,人們必須說明該詞具體指涉什麼以及它的相關含義;不然,不同的讀者對多元文化主義會有不同的理解,導致誤會。舉例來說,根據側重點不同,多元文化主義可以分為保守多元文化主義、自由多元文化主義、多樣化多元文化主義(pluralist multiculturalism)、左傾本原多元文化主義(left-essentialist multiculturalism)和批評性多元文化主義(critical multiculturalism)。但從內容範疇來說,多元文化主義涉及政治理論、文藝理論、女性主義、民族主義、歷史研究、文化研究、教育、宗教和社會學等學科領域。由於本文討論的多元文化主義主要指涉當代美國社會和文化思潮,所以它的定義範圍比較寬泛,涉及階級、性別、種族、家庭和性傾向等社會和文化問題,旨在考察它對當代美國政治的影響。
至於多元文化主義的思想理論基礎,我認為可以從三個方面加以概括。一是哈貝馬斯的憲政民主思想;二是查爾斯·泰勒的“政治承認”(politics of recognition);三是解構主義理論。具體而言,哈貝馬斯指出,僅僅由法律來提供平等保護仍不足於構成憲法民主;只有當人們把自己看作是法律制定者時,民主才可能在憲政政體里得到體現。這樣,“權力系統就會既注意不平等的社會條件,又考慮文化差異。”換言之,只有當社會(弱勢)群體介入到公共討論並充分闡述自己的要求時,他們才可以說享受到了憲政民主賦予他們的公民平等權。泰勒的“政治承認”源於他對自由民主政體的解釋。一般來說,西方政治哲學家把自由民主政體歸結成一條原則:“把所有的人都看作是自由和平等的人”(Treat all people as free and equal beings)。不過,如何貫徹和執行這一原則,民主政體一直存在著兩種觀點。一種認為,當公民在社會運作問題上發生意見衝突時,政府應保持中立態度,不偏向任何一方。另一種認為,只要所有公民的權利得到保護,且沒有一個人被迫接受某種價值觀,那麼政府就有權干預,提高某一社會群體的文化價值。泰勒認為第二種觀點更民主,並由此提出其“政治承認”一說,即人的自我認識和社會身份與社會給予的政治承認有直接關係,“不承認或錯認會造成傷害,甚至成為一種壓迫,使人陷於虛假、貶低的生活困境”。把泰勒的“政治承認”理論用來分析美國社會的話,那就是美國主流社會沒有給予婦女和少數民族政治上的承認,致使他/她們無法享受平等權利,陷於困境。至於解構主義對多元文化主義的影響,主要在於它否認建立共同思想文化標準的必要性。在解構主義看來,任何共同一致的標準,都是掌握政治權、佔有話語權和控制社會資源的群體行使它們權力的面罩,因而是為社會強勢群體服務的,社會邊緣群體不僅無法從中受益,反而會成為它的受害者。由於多元文化主義所強調的,正是不同社會群體共處一個社會時的政治承認和文化權利問題,所以,解構主義對話語霸權和正統理論的挑戰自然成了多元文化主義的重要理論武器。歸納起來,哈貝馬斯強調關注社會條件和文化差異的憲政民主思想,泰勒要求民主政體承認社會群體文化特性的觀點,以及解構主義有關社會強勢群體擁有政治和文化話語霸權的理論,為多元文化主義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

相關資料
在這些思想指導下,多元文化主義圍繞少數民族和其他亞文化群體的“承認”和“平等”問題提出了種種要求。比如,在中小學教育方面,它要求實施雙語教育,以“消除拉丁裔人語言障礙所造成的不利條件”,體現知識傳授上的公平性。不然,強行用英語教拉丁裔人,不僅會挫傷他們的學習熱情,而且還會傷害他們的自尊性。再比如,在大學招生方面,多元文化主義要求美國高校對黑人等社會弱勢群體實行傾斜政策,以低於錄取分數線的標準錄取他們。其理由是,黑人、拉丁裔人和印第安人長期受到壓迫和歧視,高等院校如果不“承認”這一“先天不足”,用千篇一律的標準套在他們頭上,那這種貌似客觀的做法顯然有失公允,這些少數民族也因此而難有出頭之日。唯一能糾此偏向的是“高抬貴手”,低標準錄取他們。除此之外,多元文化主義還要求高等院校和公司企業在人才錄用政策上體現“承認”和“平等”精神。多元文化主義者指出,在美國教育界和商界里,白人男性占絕對主導地位,婦女和少數民族鳳毛麟角。這種對社會弱勢群體的“不承認”,顯然是對他們的嚴重不公,是社會強勢力量的霸權行為。多元文化主義認為,不改變這種狀況,社會弱勢群體將無翻身之日,文化多元也將成為無稽之談。基於這一認識,多元文化主義對“肯定性行動計劃”(affirmative action)極為支持,希望藉助政府行政令和國會立法,讓少數民族和婦女在就業、晉陞、銀行貸款和獲取合同方面得到優先考慮。多元文化主義認為,只有通過這類政府介入強硬措施,弱勢群體的不平等局面才有可能扭轉過來,實現羅爾斯所說的“公平平等機會”(fair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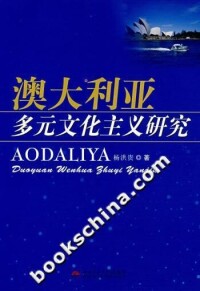
相關資料
討論了多元文化主義的“承認”和“平等”這兩個核心概念之後,它對主流文化話語霸權的解構就容易理解多了。就挑戰美國主流文化話語霸權而言,多元文化主義的一個主要論點是,WASP長期以來以主流文化自居,主宰著美國的話語霸權,使得非WASP群體難以發出它們的聲音。從人類學到政治學,從歷史課本到文學作品,從藝術創作到體育運動,從科學技術到工農業建設,從公共教育到社會改革,幾乎所有一切都以白人男性,尤其是WASP男性為主,好像美國歷史上只有華盛頓、林肯和林伯格等英雄;美國文學家中只有霍桑、愛默生、馬克·吐溫;美國音樂家和藝術家只有……。多元文化主義對此提出挑戰,認為這種把參與美利堅共和國建設、為美國現代文明做出重要貢獻的其他社會群體遮蓋起來或者排除在外的做法,說得輕一點是不尊重歷史事實,說得重一點是撒謊和騙人。多元文化主義認為,黑人的奴隸經歷、婦女的“半邊天”作用、移民遭受排擠的痛苦、窮人在“血汗工廠”的勞作、少數民族的掙扎和同性戀在社會上受到的歧視等,都是美國歷史、文學、政治、經濟和社會的一部分,理應得到他/她們的那部分話語權利。帶著這種為社會弱勢群體爭取話語權的一腔豪氣,多元文化主義要求對傳統文本重新解讀,用話語理論將其一一解構,剔除其貶低和歪曲的部分,添進過去被排除在外的部分,力爭把被WASP顛倒的一切再顛倒過來。與此同時,為了提高社會弱勢群體的自我意識,發展自己的獨特文化,多元文化主義在對WASP文化大解構的同時,還積極構建亞文化群體的話語體系,以贏得社會的承認和平等的話語權。於是,在二十世紀七十至九十年代期間,非洲裔學、亞裔學、拉丁裔學、女性學、性別研究、族裔研究和同性戀研究等學科在美國高校紛紛開設,一時成為教授們和學生們追捧的“顯學”。多元文化主義希望藉助於這些新興學科來打破“歐洲中心論”、消解“白人優越論”,為社會弱勢群體確立話語權力,最終走向所有文化平等相待、和諧共處的自由民主社會。
綜上所述,多元文化主義是近二十多年來活躍於美國學術界、教育界和政治界的一種政治和社會理論,對美國的傳統信條(American Creed)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從而引起兩種價值觀的激烈交戰。概括地說,這兩種價值觀的衝突主要表現在下面三點。
⑴傳統信條認為,個人潛能的最大化是人活在這個世界上的最終目標,因此,包括政府在內的一切都必須為這一目標的實現服務;多元文化主義針鋒相對地提出,人類不應把個人成就看成是人生的最終目標,而應以集體福祉作為人類的追求目標,所以,個人的自我實現不應成為衡量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標尺。
⑵傳統信條認為,自由社會裡,政府的職能是制定相關的法律和政策,創造一個機會平等的環境,不對任何個人或團體偏倚;多元文化主義反駁道,政府的職責在於確保社會的公正和公民的平等。當某些社會群體因受歧視和排擠原因而無法享受平等機會時,政府必須干涉,讓所有社會成員,尤其是弱勢群體享受充分的平等權利。
⑶傳統信條認為,美國的政治理念和價值體系源於猶太-基督教和古希臘、羅馬文明,美國的核心文化是WASP。它們是美國文明的基石,不容許任何人動搖它們;多元文化主義指出,這是一種典型的“歐洲白人中心論”,也是一種話語霸權的表現,既無視美國曆來是多種族、多民族的事實,又抹殺了其他社會群體對美國文明的貢獻。為此,多元文化主義提出“差異政治”一說(politics of difference),不僅拒絕融入WASP主流文化,而且要求承認文化差異性的存在,並平等對待這些差異。
毫無疑問,多元文化主義的這些理論威力巨大,具有很大的殺傷力。它們不僅挑戰了美國強勢群體的威嚴,而且打到了美國傳統勢力的痛處。更重要的是,它們觸動了美國主流文化的根基,踩到了美國WASP的尾巴。由於美國少數民族人數增長快速,社會弱勢群體政治意識不斷增強,再加上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反主流文化思想至今仍“陰魂不散”,多元文化主義由理論轉換為一種社會思潮之後,便在美國社會的各個領域產生反響,找到“知音”。不管是出於政治考慮還是出於社會正義,也不管是出於群體利益抑或是反叛心理,上至政府機構、公眾輿論,下至草根社區、家庭學校,人們都大談特談多元文化主義,真有點言必稱“多元”的味道。於是,什麼東西都多元起來了:價值觀多元起來了,道德標準多元起來了,生活方式多元起來了,授課語言多元起來了,婚姻形式多元起來了,家庭模式多元起來了,性行為多元起來了,等等等等,不一而足。面對這鋪天蓋地、來勢兇猛的“多元主義”,篤信美國傳統信條的保守主義勢力如坐針氈。他們先是困惑迷茫,不知所措。待清醒過來,看到自己心目中的文明大廈在各種“多元力量”的攻擊下出現劇烈搖晃時,他們便以“天降大任於斯”的氣度出擊,向多元文化主義發動反攻。
新保守主義的攻擊

相關資料
二戰後不久出現在美國的新保守主義之所以被叫作新保守主義,主要是為了區別於傳統上的老派保守主義。它主要由兩股勢力組成,一是視共產主義思想為不共戴天之敵的反共勢力,二是視羅斯福“新政”為洪水猛獸的自由市場經濟鐵桿派。這兩股勢力儘管竭力兜售其思想,但在五十年代時期都不怎麼得勢,“被當時的美國主流思想擠出門外”。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極右反共勢力因追隨麥卡錫主義和組建“約翰·伯熙社團”(John Birch Society)極右組織而名聲掃地;另一方面是自由市場經濟鐵桿派因三十年代經濟大危機而使其放任自由理論(laissez-faire)不攻自破。然而,這兩股勢力並不就此罷休,輕易地退出政治舞台。眼見自由主義力量日益龐大,欲攬媒體、思想庫、基金會和高等院校的思想資源於一體,保守主義派們坐不住了。他們決定反擊,與自由主義搶佔思想宣傳陣地:用《華爾街日報》對抗《紐約時報》,用“美國企業研究”與“布魯金斯研究所”抗衡,用“經濟教育研究”對付“福特基金會”。所有這些努力只為一個目的,即從自由主義者手中奪回政權。從短期來看,這股保守勢力使重量級保守人物Barry Goldwater贏得共和黨1964年的總統候選人提名,從長遠來看,他們的新保守主義思想在當年新當選的加州州長里根身上產生了共鳴,從而為保守勢力重掌大權作了準備。
需要指出的是,儘管反共意識形態和自由意志論(libertarianism)構成了五十年代美國新保守主義的主要思想框架,但傳統觀念也對新保守主義的興起起了重要的作用。這些傳統觀念主要包括個人倫理道德、個人自我約束和個人理性思考。比如,保守派歷史學家彼得· 維爾瑞克認為,新保守主義之所以新,就是因為它強調回歸基督教道德觀和傳統倫理觀。新保守主義幹將拉塞爾·柯克(Russell Kirk)說得更直截了當:一個真正的保守主義者必須堅信先驗道德秩序,相信社會的連續性,堅持精英主義,信守除了上帝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外其他什麼都不平等的原則。他特彆強調年輕精英的人文教育,因為美國傳統價值之“薪火”要靠他們來傳遞。此外,保守派社會學家羅伯特·尼思貝特和保守雜誌《國民評論》主編威廉·布克利也對戰後新保守主義的發展提供了不少思想。然而,讓這些為新保守主義興起搖旗吶喊的保守派們深感失望的是,新保守主義在宣傳媒體上的氣勢沒辦法轉換成實質性的政治權力。畢竟,五十年代的美國仍生活在羅斯福“新政”的陰影之下,而六十年代則基本上是自由主義思想獨步天下。所以,在這一時期,新保守主義除了從新成立的“自由美國青年”(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這一保守組織中得到些許慰藉之外,已沒有什麼戲可唱,更別說有什麼大作為了。
然而,令人驚訝不已的是,當new conservatives還在苦思冥想如何與如日中天的自由主義力量展開較量時,自由主義陣營中突然衝殺出一小群知識分子,組成了一支人數不多但能量可觀的neoconservatives力量,其時正值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按照“新保守主義之父”歐文·克里斯托的說法,之所以用neoconservatives來指涉這群為數不多但知識超群的學者和知識分子,是要突顯他們從自由主義轉向保守主義的過程。而他們之所以改弦易轍、更換門庭,照美國新保守主義核心刊物《旗幟周刊》(Weekly Standard)特約撰稿人麥克斯·布特的解釋,是因為他們對民主黨自由派處理國內社會矛盾不力、對付蘇聯不夠強硬感到極度失望,有“受到現實重創之感”。事實上,他們除了仍贊同福利政策和政府干預外,其他方面與保守主義無甚區別。但據人文科學教授保羅·高特福萊德的理解,這批新保守主義者中,既有冷戰方面的自由主義者,也有對“黑人權力”政治(black power)不滿的自由主義者,但更多的是對“反正統文化”(counter-culture)所宣揚和追求的“另類生活方式”(alternative lifestyles)感到厭惡的自由主義者。儘管上述解釋新保守主義產生緣由的側重點不一,但它們的共同點還是顯而易見的,即新保守主義早期骨幹力量大多對美國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社會文化問題深感憂慮,惶惶不安。
那麼,美國六七十年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使這些新保守派如此大動肝火,以致非要從自由主義一邊“跳槽”到保守主義陣營去呢?眾所周知,六十年代是美國現代史上最多事、最混亂、最令人迷茫的歲月。民權運動、女權運動、反戰運動、反正統文化運動、新左派運動和環保運動,像滾滾波濤,一浪接著一浪地衝擊美國價值體系,沖刷美國社會肌體。狂濤駭浪沖刷之後,不僅城市大街上留下了片片殘痕,而且人們的心靈中也出現了一大片空白。用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威廉·奧尼爾的話來說,六十年代的美國已到了“分崩離析”的地步,價值體系失去支撐中心,社會結構缺少凝聚力量。這樣的局面顯然不是執意保守住美國傳統價值觀念的人所願意看到的。

文化多元
那麼,就新保守主義者而言,哪些美國傳統文化價值具有永恆意義,因而需要“嚴防死守”呢?這個問題比較難回答,因為保守主義種類較多,重心點各自相異。比如,拉塞爾·柯克列出六條保守主義信條,柯林頓·羅錫特則認為有十二條,而鄧恩和伍達德堅持認為,十條已足以概括美國的傳統文化價值。這裡僅以鄧恩和伍達德所列的十條為例。⑴連續性:秩序和變革速度;⑵權威:權力與政府許可權;⑶社區:分散社會結構;⑷虔誠:人與道德;⑸責任:義務大於權利;⑹民主:限權政府與憲法;⑺財產:經濟作用;⑻自由:平等的兄長;⑼任人惟賢:領導階級;⑽憎恨:反共激情。
根據鄧恩和伍達德,這“十項基本原則”概括了美國傳統文化價值的精髓,任何保守主義者都視它們如生命重要,並竭盡一切所能保護它們。限於篇幅,這裡不可能就它們一一展開討論。但即便如此,僅把它們與美國六七十年代出現的性革命、反正統文化、新左派、“另類生活方式”等所追求的價值觀念作一比較,兩者之間的對立是昭然若揭、不言自明的。可見,新保守主義是在“十項基本原則”遭到戲弄嘲笑、肆意踐踏的情況下,才憤然“挺身而出”,捍衛自己信仰的。正是基於這一點,新保守派常被稱作理想主義者。
既然有理想必須捍衛,新保守主義者自然要對任何威脅這一理想的思想和行為進行抵制、批駁和反擊。在美國,習慣上來說,保守主義的對手是自由主義,兩者幾乎是一對“天敵”。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前,美國政壇上始終貫穿著保守派與自由派的鬥爭與較量。然而,羅斯福開創的“新政”式自由主義經杜魯門的“公平施政”、肯尼迪的“新邊疆”和約翰遜的“偉大社會”等自由主義政策演繹之後,已大為走樣。一是政府機構日益龐大,雄心勃勃的福利計劃使政府不堪負重;二是自由主義思想極度膨脹,導致自由權利濫用,社會道德下滑。新保守派認為,正是六十年代的極端自由行為,“種下了當今西方社會問題的禍根”。然而,當新保守主義準備與自由主義捉對廝殺時,後者卻因其眾多社會和經濟政策的失誤而不再叱吒風雲。在今日美國,“自由派”作為一種政治標籤已具有政治自殺性質,而作為一種執政思想則已“壽終正寢”。不過,雖然作為一種政治黨派力量自由主義已難成氣候,但它的許多價值觀念仍頗有市場,時常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在新保守主義者眼中,近二十多年來活躍於美國社會的多元文化主義就含有諸多自由主義思想的成分。既然“老對手”自由主義“缺席”,而多元文化主義又如此咄咄逼人,新保守派自然而然地將其攻擊目標鎖定在多元文化主義這一新敵手身上。明乎於此,新保守派領軍人物之一塞繆爾·亨廷頓呼籲新保守主義兩條線作戰:外“反西方普世主義”,內“反多元文化主義”。
新保守主義對多元文化主義的攻擊
▲劍出鞘后,新保守主義的第一個攻擊目標是多元文化主義在教育界掀起的一場教育革命,從而點燃起“校園戰爭”的烽火。新保守派急先鋒艾倫·布盧姆單刀直入地指出,多元文化主義在課程設置中砍掉西方經典,換上非經典及女性作品,是對美國傳統精神的肢解,是對美國文化基礎的破壞,是對美國文明的嘲弄。他要求抵制多元文化主義染指教育界,確保以WASP為代表的美國主流文化“江山不變”。與其相呼應,美國保守報刊《華爾街日報》在斯坦福大學改革其“西方文明”課程內容時,以嘩眾取寵的語言大聲驚呼:“西方思想文化今天在斯坦福大學遭受審判。”事態如此之嚴重,新保守派們於是紛紛出場參戰,一方面竭力為“西方文明”辯護,說它是人類追求“真理、理性和客觀性”的代表,另一方面對多元文化主義猛烈抨擊,斥之為“美國的垃圾堆”。新保守派對多元文化主義在教育領域裡的改革措施如此激怒、如此破口大罵一點也不難理解。這是因為,作為一個移民國,美國各民族的文化背景和傳統習俗都不一致,所以一般家庭承擔不了向下一代傳授“正宗”美國傳統文化的使命,只有學校能向移民後代灌輸美國的傳統精神。換言之,“美國人是通過學校正式教育來取得美國(傳統價值)認同感的”。教育領域對承傳美國傳統精神如此至關重要,新保守主義豈有輕易讓出這塊陣地之理?!
▲新保守派對多元文化主義攻擊的第二個目標,是多元文化主義所強調的種族多元論。眾所周知,六十年代民權運動之後,美國少數民族意識普遍增強,出現了各民族對自己民族文化追尋和認同的熱潮。順應此潮流,多元文化主義提出了“雙承認理論”:承認種族差異和承認差異平等。在新保守派看來,“雙承認理論”至少存在兩大危險:一是要動搖盎格魯-撒克遜為主體的社會精英領袖地位;二是威脅美利堅民族的凝聚力。保守主義“十大基本原則”中有“秩序”和“權威”兩條,在新保守派看來,WASP價值觀為美國社會“秩序”提供了最好的保障,其“權威”性不容置疑。如果實行多元文化主義所說的“種族多元論”,那美國將必然走向“種族多中心論”,WASP的“權威”將喪失,社會道德“秩序”將出現混亂,而美國本身則將因缺少核心文化價值觀而加深種族分離,最終導致合眾國的“分化瓦解”。新保守派堅持認為,西方社會及其支撐它的價值體系,“優越於所有其他社會及它們的價值體系”,因此,多元文化主義的主張不僅是多餘的,而且是有害的。為了維護西方價值體系的優越地位,新保守主義要求堅決抵制“承認種族差異”和“承認差異平等”之類的“奇談怪論”,確保以它為核心的“共同文化”(common culture)之權威地位。

文化相對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