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羅斯特
佛羅斯特
佛羅斯特(1874—1963)美國詩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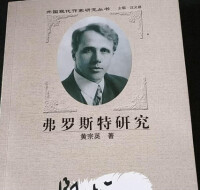
佛羅斯特
弗羅斯特,常被稱為交替性的詩人,意指他處在傳統詩歌和現代派詩歌交替的時期。他與艾略特被視為美國現代詩歌的兩大中心人物。
生於加利福尼亞州。父親在他11歲時去世。母親把他帶到祖籍新英格蘭地區的馬薩諸塞州。中學畢業后,在哈佛大學學習兩年。這前後曾做過紡織工人、教員,經營過農場,並開始寫詩。他徒步漫遊過許多地方,被認為是“新英格蘭的農民詩人”。弗羅斯特16歲開始寫詩,20歲時正式發表第一首詩歌。他勤奮筆耕,一生中共出了10多本詩集,其中主要的有《波士頓以北》(1914),《山間》(1916),《新罕布希爾》(1923),《西流的小溪》(1928),《見證樹》(1942)以及《林間空地》(1962)等。弗羅斯特的詩可分為兩大類:抒情短詩和戲劇性較強的敘事詩,兩者都膾炙人口。弗羅斯特的抒情詩主要描寫了大自然和農民,尤其是新英格蘭的景色和北方的農民。這些詩形象而生動,具有很強的感染力,深受各層次讀者的歡迎。他的敘事詩一般都格調低沉,體現了詩人思想和性格中陰鬱的一面。弗羅斯特的世界觀是比較複雜的,他把世界看成是一個善與惡的混合體。因此,他的詩一方面描寫了大自然的美和自然對人類的恩惠,另一方面也寫了其破壞力以及給人類帶來的不幸和災難。弗羅斯特詩歌風格上的一個最大特點是樸素無華,含義雋永,寓深刻的思考和哲理於平淡無奇的內容和簡潔樸實的詩句之中。這既是弗羅斯特的藝術追求,也是他事業成功的秘密所在。
佛羅斯特的詩歌最初未在美國引起注意,1912年舉家遷往英國定居后,繼續寫詩,受到英國一些詩人和美國詩人埃茲拉?龐德的支持與鼓勵,出版了詩集《少年的意志》(1913)和《波士頓以北》(1914),得到好評,並引起美國詩歌界的注意。1915年回到美國,在新罕布希爾州經營農場。1924、1931、1937、1943年四次獲得普利策獎,並在幾所著名的大學中任教師、駐校詩人與詩歌顧問。他晚年是美國的一個非官方的桂冠詩人。在他75歲和85歲誕辰時,美國參議院作出決議向他表示敬意。他的詩歌在形式上與傳統詩歌相近,但不像浪漫派、唯美派詩人那樣矯揉造作。他不追求外在的美。他的詩往往以描寫新英格蘭的自然景色或風俗人情開始,漸漸進入哲理的境界。他的詩樸實無華,然而細緻含蓄,耐人尋味。著名的《白樺樹》一詩,寫一般人總想逃避現實,但終究要回到現實中來。《修牆》寫人世間有許多毫無存在價值的有形的和無形的牆。除了短篇抒情詩外,他有一些富於戲劇性的長篇敘事詩,刻畫了新英格蘭鄉間人物的精神面貌,調子比較低沉,亦頗有特色。在格律方面,弗羅斯特愛用傳統的無韻體和十四行體的各種變體,在節奏上具有自己的特色。
佛羅斯特常被稱為“交替性的詩人”,意指他處在傳統詩歌和現代派詩歌交替的一個時期。他又被認為與艾略特同為美國現代詩歌的兩大中心。
佛羅斯特出版過十多部詩集其中包括他的成名作《波士頓以北》集,另外還有《山罅》、《新罕布希爾》、《西流的小溪》、《見證之樹》、《林間空地》等。他的詩歌獨具風格,以口語入詩,生動樸實地描寫了田園風光和農村日常生活。他的詩充滿了美國的鄉土氣息,流傳廣泛,深為人們喜愛。
美國詩人佛羅斯特大概是一個凡事都愛挑剔的人,但有一次他卻這樣講過:“讀者在一首好詩撞擊他心靈的一瞬間,便可斷定他已受到了永恆的創傷——他永遠都沒法治癒那種創傷。這就是說,詩之永恆猶如愛之永恆,可以在傾刻間被感知,無需等待時間的檢驗。真正的好詩……是我們一看就知道我們永遠都不可能把它忘掉的詩”。
顯然,佛羅斯特這裡談的並不是“讀者”而是他自己生命中的某種刻骨銘心的經驗。當我回顧我對茨維塔耶娃的認識,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老佛羅斯特的這句話。其實,對於這位巫女般的、水銀般好動的俄羅斯女詩人,我們哪裡談得上什麼高深的認識!我們有的,只是一瞬間被“攫住”的經驗。我承認,我就是這樣一位深深中過魔法的人。
那正好是在十年前的倫敦,我去泰晤士南岸文學藝術中心聽一場詩歌朗誦,散場后我的心裡似乎仍有一陣陣涌動,於是在踏上晚風中的泰晤士橋時,忍不住在路燈下翻開了詩歌節的節目冊,沒想到只讀到卷首詩的前兩句,我便大驚失色:“我將遲到,為我們已約好的相會;/
當我到達,我的頭髮將會變灰……”這是誰的詩?我在黑暗中問,一個英國人怎麼可能寫出這樣的詩?
再一看作者,原來是茨維塔耶娃!這位痛苦的天才,不可能再來英國讀她的詩了,她早已安眠在遙遠而荒涼的俄羅斯的某個地方。此時,我才知道詩歌節的開場是一個紀念她誕辰一百周年的專場,而我錯過了它!好在詩人的詩仍在“等待”,供我忘記一切地讀著;“活著,像泥土一樣持續”,我讀著,我經受著讀詩多年還從未經受過的哆嗦和顫慄,我甚至不敢往下看(往下看,最後一句是“在天空之上是我的葬禮”);最後我合上書,像一個虛弱不堪的人,走上了夜幕下的燈火閃爍的泰晤士河上的巨大鐵橋……
從此我知道了什麼叫做詩歌的力量,什麼叫著對靈魂的致命一擊或深刻抵達。就像一個深知自己中了“毒”但又不想把那根毒刺拔出來的人一樣,我守著這樣的詩在異國他鄉生活。我有了一種更內在的力量來克服外部的痛苦與混亂。現在想一想,那些日子是多麼讓人懷念!在倫敦的迷霧中,是俄羅斯的悲哀而神聖的繆斯向我走來。
人生的這麼一個階段就這樣過去了。現在,即使我不感嘆時光的飛逝,也不得不驚異“自然規律”在我們自己身上所起的物質作用。似乎轉眼間,已到了如老杜甫所說的“老去詩篇渾漫與”、“潦倒新停濁酒杯”的時候了;或者說,是到了與這個世俗的、肉體的世界達成某種妥協的時候了。再說,像我這樣的人,讀了一輩子的詩,還有什麼可以激動的?還有什麼可以再次攪動我的血液?我們自己,早已“麻木不仁”了。
然而,也正是在這種情形下,偏偏有一個你早已忘記的人向你走來,我想大家已知道這裡說的是誰了。看來她出現一次還不夠,她還要再出現一次。大約在半年前吧,我偶爾翻開一本雜誌,上面恰好有一首茨維塔耶娃的《普賽克》,我開始還不怎麼在意,但接著,彷彿一種不由分說的力量拉住了我,彷彿死者在驟然間復活,“過去的一切”全回來了:
你穿著——我的甜心——破爛的衣服,
它們從前曾是嬌嫩的皮膚。
一切都磨損了,一切都被撕碎了,
只剩下兩張翅膀依然留了下來。
披上你的光輝,
原諒我,拯救我,但是
那些可憐的、滿布塵埃的破爛衣服——
將它們帶到教堂的聖器室去。
正是這樣的詩讓我“留了下來”。這一次,雖然沒有上次那樣強烈,但也許更深刻:它不僅使我再次感受到一種語言的質地和光輝,感受到愛、犧牲、苦難和奉獻的意義,重要的是,它令我滿心羞愧。在那一刻,我理解了為什麼愛爾蘭詩人西穆斯·希內會說曼傑斯塔姆、茨維塔耶娃這樣的俄羅斯詩人在二十世紀現代詩歌的版圖上構成了一個“審判席”。是的,面對這樣質樸、傷痕纍纍、無比哀婉而又不可冒犯的詩,我唯有羞愧。它使我被迫再次面對自己的內心。它使我意識到像我這樣的人註定要和某種事物守在一起,要和它“相依為命”。正像人們說的,想不愛它都不行。
這就是我心目中的茨維塔耶娃。我曾對另一個俄羅斯女詩人阿赫瑪托娃有過一點研究,如果說她的詩是“歷史的”(尤其是她中後期的詩),茨維塔耶娃的詩就是“神話的”。要描述這樣一種詩歌,我們需要另一種語言,而這種語言在當今似乎已經失傳。我們就生活在這樣一個江河日下、離本源愈來愈遠的時代里。
然而,文學和詩歌是承載記憶的。茨維塔耶娃的詩讓我感動並驚異,不僅在於她寫出了俄羅斯心靈的苦難和渴望,更在於她通過特有的激情、靈感和語言,有力地復活了詩歌的那種似乎比一切語言更古老、也更神秘的力量。這不能不說是現代詩歌的一個奇迹。是的,它讓我在今天再次意識到出自詩歌本源的力量何在。這種力量何在呢?它肯定不在當今那一片錯把慾望本能當作藝術本能的熙熙攘攘聲里,恐怕也不在我們自己的機巧或雄辯里。然而這種力量確實存在。它曾被人類一再觸及,但又被一再遺忘。這一切,正如茨維塔耶娃的友人、同時代詩人曼傑斯塔姆早就寫到的那樣:
也許在嘴之前,低語已經存在,
遠在樹木出現之前,葉子就在飄旋,
那些我們奉獻經驗的對象,
遠在彼時之前即已成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