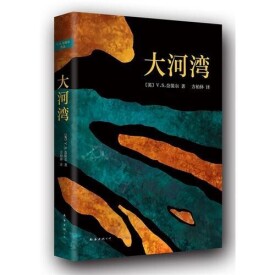大河灣
大河灣
《大河灣》為V.S.奈保爾創作的長篇小說,被媒體譽為“最後一部現代主義的偉大史詩”。奈保爾在《大河灣》中表現出的強韌的精神一如既往,亦一如之後:黑暗就是黑暗,奈保爾從來不屑為之描上光明的花邊,以符合所謂的政治正確。
徠小說包括四個部分。第一部描述叛軍起義的動亂時期小鎮上發生的事。第二、三、四部展現了平叛后的和平時期里,國家從繁榮到崩潰的過程。
殖民者走了。國家獨立了。
徠薩林姆千里迢迢跑來到大河灣上的小鎮,在這裡呼吸的每一口空氣和接觸到的每一顆塵埃上,都似乎散發著夢想和未來的芬芳。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朝這裡奔來,都像那滿河的水葫蘆朝小鎮漫卷而來。水葫蘆開著紫色的花,默默無語。
但眨眼之間,薩林姆發現繁榮里總透著無邊倉皇,無論他怎麼掙扎,他永遠是一個兩手空空的異鄉人,他已經完全失去了可以回去的地方。
只有水葫蘆依舊在黑色的大河上默默無語。
| 第一部 第二次反叛 | 第二部 新領地 | 第三部 大人物 | 第四部 戰鬥 |
1965年奈保爾首次造訪非洲,之後寫就了兩部以非洲為題材的重要小說,《自由國度》和《大河灣》,並留下了兩篇隨筆,收錄於《我們的普世文明》,其中《大河灣》是以剛果的真實歷史為背景的作品。
小說主人公薩林姆是一位出生在非洲東海岸地區的印度裔移民,這裡是一個阿拉伯人、印度人、波斯人、葡萄牙人混雜的地方,在地理位置屬於非洲的外圍,居民卻多是印度洋人,這點恰與奈保爾身世極為相似,某種程度上薩林姆確實正如奈保爾自己的投影,只是對無根性的逃離,作者本人選擇了能夠容納並且使之發聲的歐洲國家英國,卻把小說的主人公安排在了第三世界的非洲國家剛果。
剛果舊稱“扎伊爾”,是當地語言中“河流”一詞的葡萄牙語變體,又被用來指代貨幣,所以它具有了三重意義:國家、河流和貨幣。這個曾經隸屬於比利時殖民地的國家1960年獨立,小說的故事就是起始於獨立后首次動亂之後的恢復期。對於一個來自古老民族卻把歷史遺留在時間隧道的移民者來說,薩林姆為了遠離自身的虛無決定深入到非洲腹地,在一處位於大河河灣處的內陸小鎮開啟新的生活,卻沒想到最終陷入進更大的虛無中。在小說中,奈保爾以細膩而獨具韻律性的語言刻畫出形形色色的人物,不安於現狀一直在尋找出路也是把河灣雜貨鋪賣給薩林姆的外鄉人納扎努西,移居到河灣後面對風起雲湧卻不為所動的印度夫婦舒芭和馬赫什,因為戰亂投奔薩林姆的已由僕人反客為主的梅迪,在變革中成長起來的新非洲人費迪南,對非洲古老文明執著而敬畏的惠斯曼斯神父,到歐洲找尋出口卻失望而歸的薩林姆舊時友人因達爾,以及他所代表的“領地”和大人物身邊的白人寵信:作家雷蒙德和他的妻子椰葦特。雖然大人物在小說《大河灣》中並未親自登場,卻為情節的推波助瀾起著重要作用,他的人物原型是剛果新王蒙博托,一個普通百姓的兒子,在軍變中登台,奈保爾在前面提到的《我們的普世文明》中專門的章節中形容“他是公民、酋長、國王、革命家;他是非洲的自由鬥士,他佔據了意識形態的各個位置,其王權基礎不容置疑”,但是事實上,蒙博托在排斥與踐踏西方文明痕迹后重建的非洲新文明不過是一種不倫不類的模仿,如同剛果一直以來的歷史書寫,他們總是以斷裂的方式跳過殖民者的歷史,試圖把非洲還給非洲,但是卻忽視了非洲的歷史唯有在西方的文明下才得以保存,才能不斷的前行,這即是惠斯曼斯神父關於小鎮的重建和歐洲人回歸的先見性預言,更是奈保爾一直以來在政治立場上被人詬病的所在,他在《大河灣》中再次藉由惠斯曼斯神父之口為之蓋棺定論“對於未來,抱有一種很宏大的看法,他認為自己站在這一切的終點,覺得自己是最後一個也是最幸運的一個見證人。”
惠斯曼斯神父所謂的見證是奈保爾對非洲及第三世界國家歷史進程的預見,他在1975年對蒙博托政權虛無主義的定性經過近半個世紀的驗證被證實確如其所言,而在《大河灣》中奈保爾也藉由因達爾之口為困擾他和許多后殖民主義移民者的精神出路問題給出了一種答案“要學會踐踏過去”,從文明的邊緣走向中心,在這場文明的遷徙中尋找到普世文明的真諦,這也正是奈保爾自我人生的寫照。
2014年,該書入選新浪2014年度中國好書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