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豐年
辛豐年
辛豐年(1923年—2013年3月26日),原名嚴格,江蘇南通人。作家。1945年開始在軍中從事文化工作,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老戰士,1976年退休。20世紀80年代以來,為《讀書》《音樂愛好者》《萬象》等雜誌撰寫音樂隨筆,馳譽書林樂界。著有《樂迷閑話》《如是我聞》《處處有音樂》等十餘種作品。
辛豐年22歲加入了新四軍,先做文化教員,後來又到文工團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間,辛豐年本來是個逍遙派,後來因看不慣一個林彪在他們軍區死黨的飛揚跋扈,說了幾句話,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又因出身不好,被開除黨籍軍籍,撤銷一切職務,發配回他的老家監督勞動。
1973年,隨著林彪的倒台,辛豐年恢復黨籍,就地複員安排工作。1976年,粉碎“四人幫”前夕,辛豐年終於徹底平反了,複員改轉業,完全恢復原來的待遇。但53歲的辛豐年提出退休。
1980年代中葉,辛豐年的生平好友章品鎮先生推薦他為三聯寫一本關於音樂的小冊子《樂迷閑話》,在這過程中,就結識了三聯的宋遠先生,後來就開始為《讀書》寫稿,開設了“門外讀樂”專欄。
辛豐年是個嚴格而嚴肅的人。辛豐年做事情相當認真,寫文章要改很多遍,但是不是像現在的人用電腦改,每改一遍就是抄寫一遍,有的文章他甚至抄寫了五遍。除了寫文章,辛豐年做其它事情也相當認真,那時下放在廠里,被安排去做煤球,辛豐年做的煤球也非常細心和追求完美,每個煤球都要做很圓,而且還要一樣大小。後來辛豐年還做過磚頭,剪過草根,工作完成得都讓人非常滿意。
辛豐年(嚴格)先生2013年3月26日中午去世,享年91歲。昨天,他的小兒子放了《薔薇處處開》幾首歌給他聽。因突發疾病在江蘇南通醫院中去世,當天下午,辛豐年的兒子、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嚴鋒向外界證實了父親去世的消息。
我生於1923年,我原本完全不愛好音樂的,只是在上個世紀40年代初,我十幾歲的時候,第一次聽到貝多芬的《月光》,那是我聽音樂的第一課,當時我還完全沒有聽過其他的外國音樂,連一部小品都沒聽過,比如現在很容易聽到的《致愛麗絲》,小孩都懂——就這樣,我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喜歡上了《月光》,我聽不懂它,但是我相信它沒有欺騙我,不是在糊弄,那音樂一定是想說些什麼。
似乎很多人都是從小從《命運》開始了解了一個粗獷有力的革命的貝多芬,而不是《月光》。可貝多芬其實多麼複雜啊——你如果把他的交響曲1至9號認真聽一遍,就有9種不同的面目和性格,他還有32首鋼琴奏鳴曲,另外還有數十首弦樂四重奏,還有些不重要的作品——那一共有多少個貝多芬呢?一個聾子有這樣的創造力,也使你不得不讚歎西方音樂是個了不起的東西。
聽音樂一定要認真。現在許多音樂愛好者很滿足於隨意性地去聽,不想去儘可能地去了解創作背景和樂理方面的知識,沒有辦法深入進去,明明可以弄懂,卻不去弄懂。就這麼聽聽而已,再看看一些很膚淺的介紹,甚至就是看書,並沒有聽。
以前我常常勸人,要麼就不愛,要麼就準備為“聽音樂”付出一定的代價,就是時間和精力。因為音樂並不是“背景音樂”,當背景來聽也必然是膚淺地聽,我很不贊同一邊聽音樂一邊做別的事情,我習慣專門地去聽它,完整地聽下來,不能做別的事情,有時候為了集中精力,我站著聽,我知道國外很多人聽音樂會,買不起票,買站票,站著聽,不覺得累。像瓦格納那樣大演三天三夜,你站著也不會喊累。
辛豐年先生的忘年交嚴曉星,他說:“辛豐年先生近半年來身體不好,一直由兒子照顧,當天中午吃飯時呼吸就感覺到不順暢,非常虛弱,後來送往醫院沒能搶救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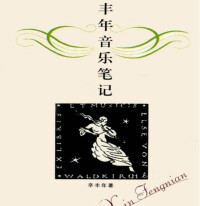
title
韓猛表示,晚年的辛先生和藹樂觀同時也有點孩子氣,“最後做的一本書是《請赴音樂的盛宴》,裡面羅列了十大必聽音樂等,當時辛老說,他還想寫一個一生都不必聽的十大音樂。不過最後他自己想了想還是放棄了,說有點不妥”。
韓猛認為,辛老的音樂評論文章深入淺出,很多細節往往能打動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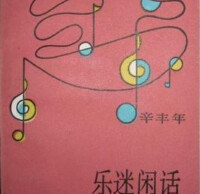
title
對於父親對古典音樂的主張,嚴鋒寫道:“辛豐年是古典音樂原教旨主義派。對‘流行音樂’從一開始就是抱著強烈的反對態度,但是也有罕見的例外的時候……有一天不小心把一段他最討厭的‘外國輕音樂’錄了進來。可是,這段當時還不知道名字的‘外國輕音樂’卻使他大加讚歎……後來才知道,那段音樂就是電影《愛情故事》的主題曲。”
“老人家是一個傳奇。愛樂者的驕傲”,樂評人劉雪楓說。《三聯生活周刊》主編朱偉在微博中說:“老先生選此花香月圓之日,願一路都有他一生喜歡的音樂相伴。我不認識辛先生,他自八十年代起在《讀書》雜誌漫談古典音樂的《樂迷閑話》是影響了無數人的。身在南通這樣一座小城,因古典音樂而聯通了那樣大一個天地——他被音樂溫暖的一生是幸福的。”
樂評人、《讀書》音樂專欄作者李皖發表博文紀念辛豐年,其中寫到,“在《讀書》的一次紀念活動中遇到王蒙,老王激情澎湃地講辛豐年,像回到了他‘青春萬歲’的年華。那一次《讀書》作者的聚會,他最期望的是能見到辛豐年,但是辛豐年沒來,是為王蒙的遺憾。後來,我每次看到王蒙、辛豐年、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這四個詞中的任意一個詞,我就會想到另外三個。音樂已經把一些東西連到了一起,那是聲音,也是生活、情感、人、時間、永恆的生命。”
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楊燕迪也在微博上深切致哀,“昨天剛剛做完錢仁康先生告別儀式,今日又一位具有“五四后”風範的知識老人仙逝!辛豐年,相信中國的愛樂人和知識界不會忘記這個名字!”
辛豐年曾給自己的定位是古典音樂的“導遊人”,他也的確引領了無數愛樂者和讀者走進古典音樂的美妙世界,他的去世令愛樂者們非常悲痛。愛樂者“米蘭小良”說:“愛讀辛老的樂評,那篇西方音樂必讀、選讀曲目是對我這個門外漢的啟蒙,當時還有谷歌音樂,我按圖索驥一個個曲子找來聽。“
一位樂迷在自己的微博中深情回憶辛豐年對自己的的影響,“我這套音箱還是當年結婚時買的,當年的我算是個小發燒友,記得當時為了這套音響不知看了多少書,逛了多少音響店才選了這麼一套音響,除了天龍功放和ELAC音箱外,還有SONY的LD,到現在快20年,效果還好得很,昨天驚聞辛豐年先生去世的噩耗,想起當年先生的書帶我進入音樂殿堂,斯人已去,唯有書籍永存。”
一位名叫“南通行者”網友和辛豐年的兒子嚴鋒相識,他回憶,“和嚴鋒剛認識的那幾年,經常在他家見到嚴老先生,留在我記憶中的是一個很小的屋子,擺滿了書,一架鋼琴旁經常轉著幾位長者,是這屋中唯一的奢侈品!和老先生最多的交流是進門的“伯伯好”和出門的“伯伯再見”,叫的聲音很低,他的回應也是很輕。在這屋中就像置身在圖書館或是音樂廳。”
嚴鋒曾在前年寫了一篇篇幅很長的名為《我的父親辛豐年》的博文,如今再次被眾多網友推薦,其中有一段話非常感人,“在辛豐年牽著我的手去田野里散步講魯迅文章的年代,辛豐年是我最崇拜的偶像。後來,改革開放了,我去上了一所名牌大學,碩士博士一路讀上去,名公巨匠著實見識了不少,福柯哈貝馬斯也生吞活剝了不少,少年氣盛,漸漸地就有些不把辛豐年看在眼裡了。老頭子過時啦,跟不上形勢啦,太保守(太激進?)啦,等等等等。但是,現在我早已過了而立之年,逐漸對這個世界,對這個世界上的人有了更深入一點的看法,我好像又有要回到童年的意思,用哲學上的說法就是‘回到辛豐年’。我冷眼看來,熱眼望去,看來望去,左看右看,竟發現,在這個偌大的世界里,就做人而言,就對知識和真理的純真熱愛和無止境的追求而言,就對待名利的冷漠態度而言,還沒有多少人能同我的辛豐年相比。發現這一點,我既覺得悲哀,又覺得寬慰,還感到驕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