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誥
明朝法令
明太祖朱元璋親自寫定的刑典,明初洪武十八年(公元一三八五年)十一月,發布《大誥》,也就是整理這一年審判貪腐方面的重大案件,以誥文的形式向全國發布,告誡官吏們,不要重蹈覆轍。包括《大誥》《大誥續編》《大誥三編》《大誥武臣》四部分,統稱《御制大誥》。洪武中期,官吏貪贓枉法、豪強兼并、脫避糧差日趨嚴重。朱元璋為維護統治,遂將“官民過犯”典型案例輯錄成帙,仿周公《大誥》之制,於洪武十八年(1385)冬刊布《大誥》七十四條,十九年春刊布《大誥續編》八十七條,十九年冬刊布《大誥三編》四十三條,頒行天下,誥戒臣民。反映了明太祖治亂世用重典的思想。因為過於嚴酷和過多體現明太祖個人特徵,故《大誥》在洪武之後基本不再行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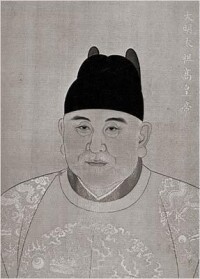
朱元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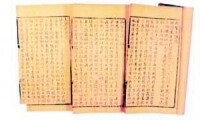
《大誥》內頁
明太祖規定:《大誥》每戶一本,家傳人誦。家有《大誥》者,犯笞、杖、徒、流之罪減一等;無《大誥》者,加一等;拒不接收者,遷居化外,永不令歸。學校課士和科舉策試也以《大誥》為題。據說其時各地講讀《大誥》的師生來京朝見者達十九萬餘人。
《大誥》有明刻本傳世。
朱元璋十分重視其親制四編《大誥》,他將之作為對天下臣民進行政治教育的課本,依憑專制主義的絕對權威在民間強制推行。《大誥》頒行時,他宣告:“朕出是誥,昭示禍福,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戶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徙流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觀為戒。”頒行《大誥續編》時又進一步說:“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寶,發布天下,務必家家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遷居化令歸,的不虛不。”頒發《大誥三編》時又重申:“此誥前後三編,凡朕臣民,務要家藏人育,以為鑒戒,倘有不遵,遷於化外,的不虛示。”朱元璋又要求軍官們全家老小都要背熟《大誥武臣》:“不聽不信呵,家裡有小孩兒每不記呵,犯法到官,從頭兒計較將來,將家下兒男都問過:你決得這文書里幾件?若還說不省得,那其間長幼都得治以罪”。
為了擴大四編《大誥》的影響,朱元璋把它們列為全國各級學術的必修課程,科舉考試從中出題。奉其旨意,行文國子監正官,嚴督諸生熟讀講解,以資錄用,有不遵者則以違制論處。當時天下講讀《大誥》的師生來京朝見者多達十九萬餘人,均賜鈔遣還。將如此眾多的師生由全國各地召來京師講讀《大誥》,舉行學習報告會,這在中國封建社會史上堪稱空前盛舉。此外,收藏《大誥》與否,成了判罪或減罪的依據;熟背《大誥》,不僅可以獲獎,而且還可以因此而被錄用為官,平步青雲。朱元璋為推廣自己的這幾篇作品,確實費盡心機。他的這些作為,可以當作中國封建文化專制主義的標本。
朱元璋以為依靠政權的強制力量,可以使《大誥》廣泛傳播,深入人心,明廷專制統治也能藉此而永久存在下去。但是,在他歿后沒多久,四編《大誥》就被他的臣民拋置腦後了。明代中葉,陸容說:國初懲元之弊,用重典以新天下,故令行禁止,若風草然。然有面從於一時而收違於身後者,如洪武錢、大明寶鈔,《大誥》、《洪武韻》是已。《大誥》惟法司擬罪雲有《大誥》減一等雲爾,民間實未之見,況復有講讀者乎!
嘉靖六年(1527),霍韜向皇帝上疏說:洪武中令天下生員兼讀誥、律、教民榜文,又言民間子弟早令講讀《大誥》三編,今生儒不知誥、律久矣,臨民蒞政,惟皆以吏為師。宜申明舊令,學校生員兼試以律,仍令禮部以御制《大誥》諸書刊行天下。
不到一百年時間,一度家藏人誦的御制聖書——四編《大誥》——在民間已灰飛煙滅,這是朱元璋始料未及的。到了清代修《明史》時,《大誥》為罕見的奇書,修史者亦未能得見,故而對之敘述多有謬誤。近代學者頗有注意此書者,廣為搜羅,“北方合公私所藏始得全帙,南中僅有范氏天一閣所藏《大誥初編》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