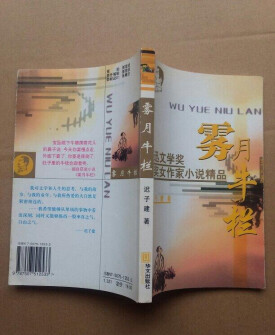霧月牛欄
霧月牛欄
《霧月牛欄》是遲子建的一部短篇小說。小說講述了一個普通鄉土人家的苦難經歷。繼父因一時衝動加之於繼子身體的傷害,使這個歲的孩子喪失了記憶,變得痴憨。男人衝動的一拳使其陷人深深的負疚之中,並開始了痛苦、漫長而絕望的贖罪之路。
1998年《霧月牛欄》獲首屆魯迅文學獎。
小說講述了寶墜的生父在打草時,因被毒蛇咬傷而喪了命。於是繼父走進了他和母親的生活。在一個霧月的夜晚,繼父與母親在大霧的包裹下盡情歡愉時,卻被半夜醒來的寶墜看見了。這一幕,特別是第二天面對寶墜對夜晚所見的坦率直言,繼父感到了巨大的羞辱,竟惱羞成怒,失手打了寶墜一拳。寶墜的頭磕在牛欄上,這個聰明活潑的繼子從此淪為一個智障兒童。繼父懊悔難當,開始了漫長而痛苦的贖罪之路。寶墜雖然什麼也記不得,卻本能地對那屋子和人心懷懼怕,從此再不回屋子裡睡覺,不再和人住在一起。在接下來的八年中,繼父深受良心的煎熬,在自責與懺悔中失去了自我。他無微不至地關心和愛護繼子寶墜,幾乎將所有的精力和愛都傾注於這個“不懂人事”的孩子身上。然而,這些努力卻始終沒能換回寶墜的回應,反而對妻子和女兒的心靈造成了傷害。最終繼父含憾而終,但他的死卻換來了寶墜和整個家庭的新生。
在20世紀末,出現了時尚寫作的熱潮,時尚寫作因為和方興未艾的網路寫作合流,對短篇小說寫作造成了一定的傷害,當然也改變了短篇小說的走向。一些名作家的創作也慢慢洗落鉛華回歸本色的寫作。其中遲子建的《霧月牛欄》在反映人性的深刻和多樣方面,敘述平實,起承轉合,自然精緻。
遲子建來自冰天雪地的中國最北端——黑龍江。她的筆從未離開家鄉廣袤的平原山川,她書寫黑土地上鮮活的人物,字裡行間刻畫出濃墨重彩的歷史和豐富多姿的現實。1987年,遲子建進入北京師範大學與魯迅文學院合辦的研究生班。3年寒窗苦讀,遲子建畢業后,依然選擇回到黑龍江。她調入省作協,成為一名專職作家。以故鄉為依託作者創作了《霧月牛欄》。
寶墜的繼父
寶墜的繼父並不是個天生的惡人,他從一開始就疼愛這個孩子。然而像所有的繼父必須面臨的一樣,寶墜的存在本身就使他感到尷尬。寶墜的靈性無疑又給他的性愛生活帶來了麻煩,所以,當寶墜毫無遮攔地說出母親與繼父做愛“像牛倒嚼的聲音一樣”時,惱羞成怒的他揮拳打昏了寶墜。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一拳使寶墜徹底地喪失了記憶並淪為一個弱智的孩子。為了補救自己的過失,他每天給寶墜送飯,跟他說話,希望能打開他記憶的閘門。三九天,他半夜起來給寶墜的炕填柴。寶墜喜歡金黃色的南瓜燈,他就每年新年送他一盞然而,這一切都減輕不了他心靈的壓力。他沒有對其他人說出寶墜痴傻的真正原因,但他又不能擺脫這一後果對自己良心的譴責。他對此事懷有罪惡感,但為了逃避懲罰不敢直白地道出;另一方面,他善良的本性又驅使他贖罪般地疼愛這個孩子。最後,他被自責的重壓摧毀了,以死亡為代價換取了永遠的安寧。
寶墜的母親
寶墜的母親是個家庭婦女。沒有受過教育,也就不懂得三從四德。為夫守節的觀念是沒有的,再嫁的目的也很簡單—養家、滿足自己的生理需要。這倒比許多經過偽飾的愛情要單純得多,也實際得多。如果沒有寶墜的突然呆傻,她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個知足的女人。然而,不幸的是兒子突然弱智后,丈夫也莫名其妙地失去了性能力。於是,她變了,變得醜陋、愛嘮叨、骯髒而又脾氣暴躁。這似乎是個自私而又醜陋的形象。當寶墜的繼父去世后,李二拐要把礙眼的寶墜送到金礦去看點時,寶墜的母親憤怒了:“他叔活著時對寶墜比親生的還好,誰要拿寶墜不當人看,這輩子就別想再踏我的門檻”。一個善良的母親形象鮮活地凸現出來。寶墜的母親在失去第二個丈夫后。終於懂得了自己該珍惜些什麼,並把全部的情感—遲到的母愛傾注到兩個孩子身上。寶墜繼父的死,使她得到了解脫。恨沒有了,愛便失去了負重感,自然而然地得到升華。
寶墜
寶墜在霧月里被繼父打傷后,變成了一個愚笨的孩子。他“不斷地說一些似是而非的話,而且貪吃貪睡,逢到有霧的日子就淚水漣漣。”家裡人不知內情,只認為他是痴獃了。寶墜也完完全全地忘記了繼父打昏自己的一幕,只是本能地開始逃避人,情願住在牛棚里與牛廝守。他的痴傻很大程度在於一種自我封閉。如果說繼父的善良在於念念不忘傷害了寶墜這一事實而儘力去補救的話,那麼寶墜的善良就在於他把那兇狠的一幕,趕到了“一片黑暗裡”。
蒙昧的傳統觀念對人性的禁錮
在小說中,遲子建向讀者展現了鄉土的閉塞和受蒙昧傳統觀念影響的生命個體。寶墜一家的悲劇從表面上看是一場偶然事件所導致的,但內里卻有著深刻的必然性。蒙昧的思想正是這一悲劇的根源。文中受蒙昧傳統思想禁錮的代表就是繼父。他既是這一思想的犧牲品,也是其代言人。繼父本是個善良的人,雖然頂著繼父的頭銜,卻一直視寶墜為己出“他第一次見到這孩子時就喜歡上了他。他生得虎頭虎腦,很愛笑。”這是繼父善良品性的自然流露,但繼父的思想卻深受傳統觀念的束縛。首先,這種蒙昧思想影響體現在父權制對人性的壓抑上。在父權制及其相應的宗法觀念中,女性被視為男性的附屬物,女性的價值在於其對男性和家庭的意義,而不在於她本身。雖然在小說中,作者沒有直接點明繼父對寶墜的母親也極好。但從他的思想困惑中,讀者卻能夠發現繼父對這一觀念的感知和因此受到的重壓。當他剛與寶墜母親結婚的時候,“由於新婚,他幾乎每夜都要和女人在一起如果月光好,他就能看清寶墜熟睡時的臉。寶墜每翻一下身或發出一聲夢吃,他都要為之一抖,覺得已故的男主人的陰魂還在角落裡監視他”。可見繼父的思想受傳統觀念的束縛很深。他的不安和羞愧,正在於他感到自己動了別人的“東西”。繼父並不是壓抑女性的父權制的代言人,但他卻深受這種觀念影響,受困於其中。因此,他仍然覺得自己對這個家來說是個外人,即使在順應天性時,也會有忐忑感。其次,蒙昧意識對人性的禁錮還體現在繼父對“性”的複雜情感上。繼父內心既有對性的渴望也有對性的羞恥感。這種複雜的情感和“繼父”這一特殊身份,使得人物總是處於自我分裂的矛盾當中“有一天晚上,他們被大霧包裹著盡情地歡娛”,然而,當寶墜“坐起來看著他們躍動的影子”“寶墜的笑聲徹底摧毀了他的激情,他膽怯地從女人身上哆哆嗦嗦地下來,覺得受到了莫大的羞辱”。從中可見鄉土蒙昧的道德觀念在人物身上的巨大影響力。繼父從性愛中得到快樂,但又對這一慾望抱持著否定的態度。因此,寶墜純真無邪的笑在繼父眼裡卻充滿了鄙夷和羞辱的味道。當寶墜將那聲音形容為跟牛倒嚼一樣時,繼父更是無法忍受將自己等同於畜生的“羞辱”。正是繼父難以自抑衝動才向不諳世事的寶墜揮出了那一記重拳,拉開了悲劇的序幕。
暴力下的人性扭曲
在小說中,寶墜毫無惡意的言語卻對繼父造成了巨大的傷害。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和擺脫羞恥感,失去理性的他採用了最直接和粗暴的方式暴力。這一行為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情感—宣洩的作用,但卻對寶墜造成了長久的傷害。繼父的暴力不但沒能為其挽回尊嚴,消除陰霾,反而使其陷入了更加深重的枷鎖當中。一方面,他沒有勇氣去坦誠自己的過失,而只能在內心懺悔,在行動上彌補。另一方面,繼父的“偏心”,甚至對其他家人的冷遇,也造成了親情的失衡,剝奪了女兒與妻子被愛的權利。可見,暴力帶來的傷害不僅是對個人,也是對整個家庭;不僅是一時之痛,也是長久的隱痛。首先,暴力的直接承受者是無辜的寶墜。暴力不但剝奪了男孩的社會屬性,也使其失去了感受親情之愛的能力。寶墜在受到暴力殘害前,是個性格開朗、聰明伶俐的孩子。然而經過這場變故的寶墜醒來時,他“目光獃滯,母親喊他寶墜時他也不知道答應”,他變得“貪吃貪睡”“逢到有霧的日子就淚水漣漣”。寶墜潛意識裡對人的懼怕,正是因為繼父那突如其來和無緣無故的暴力。對於寶墜來說,雖然在他人眼裡他仍是這個家庭中的一員,但對其本人來說,則已經完全割裂了這層聯繫,也剝離了自己作為社會人的全部屬性。作者對寶墜這一人物的設計是獨具匠心的。在繼父的暴力造成寶墜智障后,他成為一個低於常人的弱者。但在小說中,遭到傷害后的寶墜反而是一個“智者”的形象。一方面,他不僅記得如何熟練地把拴牛的繩子系成梅花扣,還懂得怎樣去照管那些牛,怎樣與牛溝通。對於一個正常孩童來說這些都是不簡單的任務,而寶墜處理起來卻能夠有條不紊。智障狀態下的寶墜對於這些農活都遊刃有餘。從這個角度上看,寶墜並沒有失去愛的能力和被愛的需要。而是他“認識到”人性的複雜和無常。另一方面,更加能夠體現出寶墜“智者”形象的是他對人事的透徹洞察。寶墜拒絕繼父臨終時讓他進屋睡的請求,因為會“再來個活的叔和她住一起”“他都要死了,謝他,他也記不住多一會兒了,還累腦子”。可見,寶墜這一人物形象又是超越了常人的。作者正是通過這一人物形象,揭示了世俗生活中的普通人,飽受的各種道德禮法羈絆的不自由狀態。其次,暴力對繼父也造成了巨大的創痛。繼父和母親新婚的時候意氣風發,生活過得有滋有味可是經過這次事件后,整個人都變了。他不敢把實情告訴母親,內疚盤踞在他心頭,壓得他喘不過氣,他為自己建造了一個牢籠,並終身未能走出。為了贖罪他拚命地付出,想要恢復內心的寧靜,繼續坦蕩地生鄉舌“他默默地把牛屋裝修起來,為寶墜盤了一鋪火炕”“每天給寶墜送飯,跟他說話”三九天為寶墜填柴,除夕給寶墜換新衣,親手給寶墜糊燈籠。繼父在贖罪的過程中,徹底地迷失了自我。甚至在女兒和妻子身上都無時無刻不看到自己的罪惡。這不但使整個家庭處於陰霆之中,繼父也在良知的折磨下,走到了生命的盡頭。暴力所導致的家庭悲劇看似偶然實則出於必然。暴力在這裡被作者賦予了象徵性意義,它所表明的正是蒙昧意識、迂腐的思想對個體的壯害和人性的扭曲。並且,作者用這一家庭悲劇闡明了它深廣的影響力和毀滅性。
血脈親情的溫暖與力量
在《霧月牛欄》中,作者雖然講述的是一場生命悲劇,但同時也以此展現了人性中所蘊涵的溫暖和力量。親情和愛能夠化解一切心靈的癥結,使人們開始嶄新的生活。繼父的死將蒙昧與狹隘也一同帶入了地下。但他對寶墜的愛,卻在女兒和妻子身上得到了繼承和延續。不是因恕罪而起的愛,變得純凈、真摯和發自於內心。只有這樣的愛才是真正溫暖和有力的。首先,對於寶墜的母親來說,她最初留給讀者的印象是一個純粹的自然主義者。她的生命簡單得只有吃喝、勞作和性。作為一個農村的普通女性她比當過獸醫的“文化人”繼父更少地受到世俗道德的羈絆。她在丈夫死後改嫁,對性更加坦蕩。繼父剛剛過世,她就招待繼夫李二拐父子在家吃飯。雖然她看似冷漠,但這並不表明她情感上的麻木。她雖然嘴上不斷呵斥著“窩囊廢”,但卻始終對卧病在床的男人悉心照料。她始終對寶墜強調繼父對他好,要懂得感恩和回報,可見其重情重義。但母親對寶墜的愛得到進一步升華,卻與繼父有著根本的聯繫“他叔活著時對寶墜比親生的還好,誰要拿我的寶墜不當人看,這輩子就別想再踏我的門檻。”可見,母親能將寶墜的利益擺在最前面,不僅是因為與後者的血緣關係,更在於繼父對寶墜的愛,對母愛的催化和激發作用。其次,血脈親情也最終將兄妹之間的情感由恨和隔膜轉變為愛與溝通。手足情是人類不可或缺的感情。寶墜的妹妹雪兒,因父親把所有的愛都傾注在寶墜身上而怨恨他。她從不叫寶墜哥哥,當父親糾正她時,她反問,“傻子也算哥?”在她心裡,寶墜和牲畜沒什麼兩樣,更像是家裡養的一頭牛。但在繼父去世后,她卻依了父親的叮囑,開始叫寶墜哥哥,陪他聊天“‘跟牛不能這麼論。’雪兒耐心地解釋,‘人才分兄弟姐妹。’”雪兒已經改變了從前將寶墜視為“牛”的立場,而將他當做自己的家人看待。雪兒看似突然的轉變,揭示了她內心深處對家庭親情的渴望和本性的善良。綜上,《霧月牛欄》雖然著眼於人性弱點所帶來的生命悲劇,卻又於其中透射出希望和暖意,體現出作家一貫的溫情立場。小說中可以讀出作者對耕耘於黑土地之上的勞苦大眾的理解、關注與同情,熱愛和依戀之情。
敘述空間
敘述空間是小說人物活動的場所以及故事展開的地域,如同現實小說中一切人物和情節是特定空間範圍內的人物和情節。作家往往是從他所熟悉的客觀空間中選取小說相對確定的敘述空間,因此作家創作呈現出鮮明的地域特色。小說描繪出那片未曾沾染都市污濁的原始風景,或是一望無際的田野,或是濃密無人煙的森林,冬季則是被皚皚的白雪覆蓋一切。但是作家又不單單停留在自然風景、民間風俗描寫刻畫的層面,而是讓讀者在自然的描摹中感受人與人情感的交流以及展現人性的複雜,從而深入探究作家創作的藝術世界的精神內核。遲子建呼籲人類重返“詩意的棲居”,即文學不僅要再現自然,還要實現自然的“復魅”。《霧月牛欄》中的霧就充當了“復魅”的自然力。“復魅”並不是倡導人類簡單地歸於原始世界的愚昧,而是幫助人類擺脫當今工業時代科學主義對人類的心靈禁錮,感受自然的美好和純真,內心恢復對自然的敬畏和信仰。
“兒童”視角和“傻子”視角結合
《霧月牛欄》中的寶墜是一個八歲的孩童,他用兒童的眼光觀察著自然世界的同時也體味著身邊的人和事。新婚不久的繼父和母親的激情場面被半夜醒來的寶墜看到,併發出嘻嘻的笑聲,使得迷信的繼父驚慌失措。當第二天繼父追問此事時,八歲的孩子無所顧忌地說:“看見叔和媽疊在一起……你們弄出的動靜怎麼跟牛倒嚼的聲音一樣。”繼父躥上牛槽,一拳將寶墜打倒,寶墜的腦袋重重地磕在牛欄上。這成了繼父和寶墜痛苦災難的開始:繼父走上了自我毀滅的救贖之路,而之後寶墜常常陷入失憶之痛,不斷說一些似是而非的話,而且貪吃貪睡,逢到有霧的日子就淚水漣漣,並且他每次解或結牛欄上的梅花扣時都怦然心動,彷彿這個瞬間曾發生過什麼重大事情,另外他還本能地感覺到牛反芻的聲音中包裹著什麼重要的事情,可他無論如何也想不起什麼,寶墜就這樣陷入失憶的深淵不能自拔,成了常人眼裡的“傻孩子”。
“傻”成為了另一種有意味的敘事策略。“傻”使得寶墜不再具有正常人的思維,也就意味著超越和自由,由此寶墜具有了一種脫離常規的局外人眼光,從人情倫理的規約中解脫出來。“傻”體現在寶墜身上主要表現為多客觀而少感情,繼父臨終時,寶墜被母親拉到屋裡,希望他能和繼父多待些時間,但寶墜問完繼父最想問的問題后,卻時刻惦記著給三頭牛再添些夜草,所以他就轉過身朝外屋走,母親哽咽著擋住寶墜的去路,說:“你不謝謝你叔這些年對你的養育之恩?他都要死了。”寶墜說:“謝他,他也記不住多一會兒,還累腦子。”人對於自己生長於其中的家庭都帶有深厚的感情,很少有人能抱定一種情感的中立,但“傻”可以令寶墜“不愛不恨”,因而可以看到最核心的真實;“傻”使得寶墜獲得了一種相對獨立的立場,具有了超越其生長於其中的情感倫理體系的規約。“傻子”作為一個不合社會規範的形象,其本身也構成了對現實的否定力量。“傻子”作為獨特的“這一個”,他的力量在於他不受社會等級秩序的限制,他既作為局內人又作為局外人談論事情;他們貌似失常卻十分清醒,看似荒誕卻有著離真理最近的言行。用“傻孩子”兼做故事的敘述者,關鍵時刻孩子做出的回答,常使讀者猛然醒悟,而且也隱含了這樣的判斷:人的社會化程度低,精神教化程度低,就更多地保留了人的自然本性,也更能體現作者隱在的價值觀。藉助“傻孩子”的敘事視角,感知寶墜對於成年人觀察和理解生活的窠臼的超越;通過寶墜對於生活的感知,別有洞天地發現生活本真的一面;透過孩子眼中的世界進入孩子心靈世界,以此進入作家的創作世界,領悟作家在創作中對於自然人性的追求。傾聽天籟在某種意味上就是傾聽“自然人”。
荒誕
小說《霧月牛欄》中的這個由女人改嫁組成的新家庭,除了奔入讀者眼底的個體之痛外,更多地傳達了關於世界與人生的荒誕之感。遲子建筆下的大自然與邊地文化充滿活力、神秘與想象,她帶有泛靈色彩的審美體察,為書寫人生的無常與宿命打開了精神通道,並造就了文本魂系彼岸的超驗色彩。這種神性思維既是遲子建賦予人生困厄的先驗底色,又與鄉土眾生的倫理觀念、世界感受水乳交融、相得益彰,這令其筆下的人物煥發出壯碩飽滿的生命原色。
《霧月牛欄》中的人事滄桑首先就來自某種異己力量的拋擲與團弄。繼父是一個背負鬼神觀念而難以自拔的鄉民。按照“殺父之仇,奪妻之恨,不共戴天”的古訓,自他婚娶寶墜母親伊始,內心就累積著對其前夫的莫大負罪感,這種樸素的鄉土倫理與幽冥想象的混合,使他在與新婚妻子的歡娛之際,始終將寶墜視為前夫的陰影,“寶墜每翻一下身或發出一聲夢囈,他都要為之一抖,覺得已故的男主人的陰魂還在角落裡監視他”。而他對寶墜的誤傷則更像上天對其命運、對這個家庭的一次發難與玩弄。“上帝躲在誰也看不到的地方,在每個人的人生關口處,悄悄地濫用它的‘支配權’,它在冥冥之中無目的、漫不經心,也可以說是隨意操縱每個人的命運。”其實,繼父的一記重拳,無非泄憤、遮羞而已,但在命運的巨大偶然性和不公面前,不期而遇的苦難從此降臨這個村野之家,並將之拋入更為可怖的生存深淵。甚至連雪兒的降生都沒有給身為父親的他帶來任何快樂,“因為他覺得雪兒的誕生與寶墜的病有著某種微妙的聯繫”。不僅如此,人類自身的有限性與溝通能力的匱乏又進一步加劇了這種人情、親情關係的疏遠與異化。小說,給人們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劇中人都陷入了無法溝通、彼此隔絕的生存境地,這是一種糅合了萬物有靈、人性弱點與神秘主義色彩的異己存在與“鏡像世界”,此種人生荒誕感的捕捉使遲子建小說傳達出與西方存在主義小說、荒誕派戲劇等現代主義文學流派仿若的存在悖論。繼父一家四口原本可以真誠、和諧地生活,不幸造化弄人竟至於斯——寶墜固然因弱智忘掉了恩怨與從前,卻也因之喪失了對繼父種種贖罪之舉的感受力,直到繼父臨終時他仍不肯離開牛屋見其最後一面;母親不知道丈夫內心的隱痛,更不了解其性能力喪失,乃至身心最終垮掉;妹妹雪兒同樣被現實鏡像所蒙蔽,始終因哥哥奪去了她的父愛而耿耿於懷……然而,從另一方面看,倘若家人間妥善溝通,共同分憂,繼父也可能免於壓抑成疾,但男人缺乏自擔重責的獨立人格,“不敢把真實的一幕說給老婆”,無形中將自己拋出了日常生活,切斷了家庭成員間的交流、體諒與和諧,這才是繼父人生悲劇的全部根由。在這種令人顫慄與疼痛的存在中,“現實世界”驚悚地虛無化了,它不再因知覺、感覺和觸覺的真實而“真實”,而演變為一座困鎖人類心靈的牢獄,奴役著每一個走不出現實幻象的個體。特別是當繼父故去,寶墜徹底失憶后,這種令人發狂的生命疑難則淪為永無破解可能的死結,一切生命之在都不可阻遏地墮向虛無,這種表象與事實之間的巨大反差使生存充滿悖論,使個體生命變得卑微而渺小。
《霧月牛欄》儼然是一首流動著空靈意境、質樸人性與生命尊嚴的溫暖詩篇,它為世界之夜的多變殘酷注入了美好與生機。
——牡丹江師範學院文學院講師黃大軍。
《霧月牛欄》中,遲子建以其細膩的筆觸揭示了社會底層小人物人性被縛的悲劇,但悲劇中又孕育著希望。繼父的死將人性的枷鎖砸碎,母親和雪兒繼承了繼父的愛,並糾正了其中的扭曲因素,使愛變得正常,給人溫暖的感覺,而這樣的愛也得到了寶墜的回應。霧月過去,牛犢的茁壯成長帶來無限生機,也帶給讀者無限的希望。
——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教師童俊。

霧月牛欄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