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找到2條詞條名為夏瑜的結果 展開
- 著名小說《葯》中的人物
- 康方生物執行董事、主席
夏瑜
著名小說《葯》中的人物
夏瑜是魯迅先生著名小說《葯》中的主人公。他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者。他家境貧寒,以致使貪婪的牢頭從他身上“榨不出一點油水”;他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有明確的認識,推翻清朝統治,建立“我們大家”的天下是他的鬥爭綱領;他意志堅定,在獄中堅持宣傳革命道理,甚至勸牢頭造反;在對敵鬥爭中“不要命”,不怕打,英勇無畏,毫不動搖。最後,在敵人的屠刀下慷慨就義,表現出革命者大義凜然的英雄氣概。
《葯》說的是兩個家庭———華家和夏家的故事———“華”“夏”代表中國整個民族了。華家出了一個病人,夏家則出了一個革命者。華家的病需要人血饅頭,而夏瑜的血則通過劊子手最終變成了人血饅頭。華家的人吃了,吃了也沒用,於是,華家和夏家的人一起走進了墳墓。
夏瑜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者。他家境貧寒,以致使貪婪的牢頭從他身上“榨不出一點油水”。他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有明確認識,推翻清朝統治,建立“大家”的天下是他的鬥爭目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意志堅定,在獄中仍堅持宣傳革命道理,甚至勸“牢頭造反”,對革命矢志不渝,毫不動搖;在對敵鬥爭中,“不要命”,“不怕”打,不畏懼,不退縮反而覺得打他的阿義“可憐”,終於在敵人的屠刀下英勇就義。表現出革命者英勇無畏、大義凜然的英雄氣概

電影《葯》封面
但是夏瑜的犧牲,也並非毫無影響。第二年清明時節墳頭出現的花環,正是對這“寂寞賓士的猛士”的慰藉,說明革命者仍在懷念著他,革命的火種還沒有——也不會被撲滅。它在黑暗中仍給人以希望。
夏瑜在作品中一直沒有出場,作者主要是通過劊子手和茶客們的談話,來描寫他的行為、思想的。

電影《葯》劇照
夏瑜的革命鬥爭,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代表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因此魯迅先生熱情讚揚了他為革命獻身的精神,但同時也描寫了他的鬥爭的悲劇性。他的革命主張不為廣大群眾所理解,他的革命行動沒有得到廣大群眾的支持,甚至連他的犧牲也沒有贏得群眾的同情。他講的革命道理,人們聽了“感到氣憤”;他挨牢頭打,人們幸災樂禍;他說阿義“可憐”,人們說他“瘋了”;他被封建王朝殺害,人們“潮加一般地去看熱鬧”只迎來一幫看客;甚至他母親對他為革命英勇犧牲也不理解,反而感到“羞愧”。更可悲的是他為革命所噴灑的熱血,竟成了華老栓給兒子治病的“葯”。總之,夏瑜的死並沒有在社會上引起什麼反響,只給自己的母親帶來了悲哀和羞愧,給愚昧的群眾帶來了一劑假藥,給健壯的看客鑒賞了一次“殺人的壯舉”,給無聊的茶客增添了茶餘飯後的談資,給貪婪的劊子手提供了一次詐騙的機會。所以,夏瑜的死是寂寞的、悲涼的。
但是夏瑜的犧牲,也並非毫無影響,第二年清明時節墳頭出現的花環,正是對這位“寂寞賓士的猛土”的慰藉,說明革命者仍在懷念他,革命火種還沒有——也不會被撲滅。它在黑暗中給人以希望。
夏瑜在小說中始終沒有出場,作者是用側面描寫,通過劊子手和茶客們的談話刻畫他的形象的。
一般認為是以志士秋瑾為原型的。
從文中對“士兵”的描寫,以及夏瑜說“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可知,夏瑜是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者,他的犧牲給社會造成的影響是什麼呢?
他的血給老栓一家帶來的是一劑“葯”,小栓吃了這“葯”,病情並未有任何好轉,最後還是死了。這是一劑假藥,那夏瑜的鬥爭能否療救黑暗的中國和愚弱的國民呢?是不是一劑救國救民的良藥呢?通過小栓的結局和命運,就可以看出資產階級革命的結局與命運。
因此,夏瑜的死只是給愚昧的群眾帶來了一劑假藥。
夏瑜就義時,人們“潮水一般”去熱鬧,頸項伸得很長,如一群鴨。因此,他的死給健壯的看客鑒賞了一次殺人的盛舉。夏瑜就義后,人們去打聽,不但不同情,反遭誤解,反被仇視,之後便又“現出活氣,談笑起來”。因此,他的死只不過給這些茶客增添了茶餘飯後的談資。
有錢有勢的夏三爺因告發自己的侄兒,“二十五兩白花花的銀子,獨自落腰包”;牢頭紅眼睛阿義要了“剝下來的衣服”;雖然康大叔說自己沒一點好處,但也拿夏瑜的血賣了因此,夏瑜給這些貪婪的劊子手提供了一次詐騙的機會。
那麼,夏瑜的死給自己的母親帶來的是什麼呢?除了悲傷之外,再有的就是“羞愧”。
這些,就是夏瑜犧牲的影響。當然,作品中寫了夏瑜墳的花環,象徵著革命後繼有人。那,夏瑜的死,除了使這些“后死諸君”哀痛懷念外,是否能帶給他們別的東西呢?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的魯迅日記寫道:“夜成小說一篇,約三千字。”這就是短篇小說《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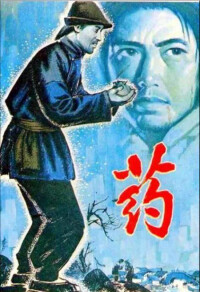 就在寫完這篇小說之後的一個多星期,五四運動爆發了。這也許不是一個巧合。歷史強大的的脈搏從遙遠的地層下傳來,被敏感的魯迅先生感覺到了、捕捉到了。《葯》是為了紀念那場已經逝去的革命,以及在革命中殞身不恤的先驅。而魯迅選擇這個特殊的時刻進行自己的紀念,顯然是"別有用心"的--誰能夠保證今天的"五四運動"不會蛻變成另一場鬧劇般的"咸與維新"呢?誰能夠肯定今天擁簇到刑場上去像鴨子一樣伸著脖子的看客會比前些年少呢?
就在寫完這篇小說之後的一個多星期,五四運動爆發了。這也許不是一個巧合。歷史強大的的脈搏從遙遠的地層下傳來,被敏感的魯迅先生感覺到了、捕捉到了。《葯》是為了紀念那場已經逝去的革命,以及在革命中殞身不恤的先驅。而魯迅選擇這個特殊的時刻進行自己的紀念,顯然是"別有用心"的--誰能夠保證今天的"五四運動"不會蛻變成另一場鬧劇般的"咸與維新"呢?誰能夠肯定今天擁簇到刑場上去像鴨子一樣伸著脖子的看客會比前些年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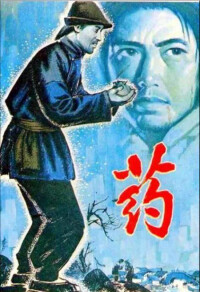
夏瑜
有人說,《葯》是魯迅為作為同鄉的“鑒湖女俠”秋瑾而寫的--從漢字本身複雜的影射功能來分析,"秋"對"夏"、"瑜"對"瑾",簡單而明了,無須再作進一步的索影和考證。然而,在我看來,它更是一篇魯迅寫給自己閱讀的小說,《葯》是魯迅給自己開出一張藥方--正因為如此,《葯》是魯迅寫得最凝重、最沉痛的小說之一。
在小說的結尾處,兩位蒼老的母親不期而遇了。她們的兒子,一個奉獻出了自己的鮮血,一個吃過對方的人血饅頭。可是如今孩子們都變成了小小的墳頭。兩個兒子各不相同,兩個母親卻驚人的相似:"她們的眼睛都已老花多年了,但望這紅白的花,卻還能明白看見。"古往今來,在這個龐大得沒有邊際的帝國里,母親們都是被凌辱者與被矇騙者。面對暴力和謊言,她們無遮無掩地赤裸著。歷史書上有太監的身影,卻沒有母親們的聲音。
統治者從來就不把母親放在眼裡。夏瑜的母親對著兒子的墳流著眼淚說:“瑜兒,他們都冤枉了你……”(其實,"他們"並沒有冤枉夏瑜,他們總是能夠極其準確地從人群中發現夏瑜的身影--從譚嗣同到秋瑾,從劉和珍到聞一多,從王實味到林昭……劊子手砍下頭顱,刺刀割斷喉嚨,子彈穿透胸膛,"他們"何嘗對"夏瑜"們心慈手軟過?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哪一頁不是蘸著鮮血寫成的?)而白髮更多的華大媽也在兒子的墳前慟哭了一場,她獃獃地坐著,不知道在等待什麼。除了眼淚之外,母親們找不到別的表示憤怒的方式。一夜之間,她們的背都被苦難壓駝了。真的,母親們的苦難比兒子們還要深重。(因此,我無比厭惡那諸如"祖國啊,我親愛的母親"的淫詞艷曲--"祖國"時刻都在辜負"母親","祖國"從來都是作為"母親"的對立物而存在。我愛"母親",我不愛統治者的"祖國")
沒有人會理解你(包括你的母親),你的結局是在民眾的唾沫中死亡,那些向你吐唾沫的人當中,有你的兄弟--對於這樣的命運,夏瑜早已知道得一清二楚。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熱情似火的大學生們喊出"理解萬歲"的口號時,我不得不感慨於歷史的弔詭與無情。我們的退卻已經超過了我們的底線,我們錯誤地把愚昧當作智慧來供奉。真理總是被徹底地忘卻,而謬誤總是能夠沉澱下來。其實,"理解"了又怎樣,"不理解"又怎樣?只有那些缺乏信念和信仰的人,才會不斷地乞求他人的"理解";而一個真的勇士,即使帶著沉重的枷鎖也會縱情地舞蹈和放歌。"理解"意味著要求某種回報,而夏瑜是不需要回報的。肩起閘門是夏瑜們自己選擇的事情,至於孩子們是否都會跑到光明裡去,那是孩子們的事情。
在茶館里,劊子手康大叔對著一班低聲下氣的街坊高談闊論道:"這小東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你曉得紅眼睛阿義是去盤盤底細的,他卻和他攀談了。他說: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你想:這是人話么?"幾千年來,在諾大的帝國網路內部,除了作為"天子"的皇帝之外,一般只存在兩種人,一種是奴隸,另一種是奴才。我們生下來就是奴隸,魯迅說,奴隸再向深淵墮落就成了奴才--而對於大多數的奴隸來說,奴才是他們夢寐以求的身份。在《葯》里,在我們每天都在面對的現實生活中,如果說康大叔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奴才,那麼那些津津有味地傾聽他講"故事"的大眾就是奴隸。奴才是罪惡的實施者(當然是在皇帝的命令之下),而奴隸則是每一次罪惡忠實的看客。因此,在東方那綿延不絕、金碧輝煌的宮闕下,作為"漏網之魚"的夏瑜,從來就沒有奢望過要獲得那些網中之魚的"理解"——他去撕咬那堅固的漁網,僅僅是他自己的選擇。他犧牲了自己的自由和生命,網依然沒有破。不過,他已經儘力了,他死而無憾。
康大叔講到,有一身好功夫的獄卒阿義因為沒有在夏瑜的身上撈到油水,便狠狠地給了他兩個嘴巴。當聽眾開始為這一情節喝彩時,康大叔卻緩緩說道:"他這賤骨頭打不怕,還要說可憐可憐哩。"
"打了這種東西,有什麼可憐呢?"聽眾之一的花白鬍子的人說。
康大叔冷笑著說:"你沒有聽清我的話;看他神氣,是說阿義可憐哩!"
聽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滯;話也停頓了。
人們恍然大悟地說:"瘋話,簡直是發了瘋了。"
魯迅先生寫到這裡,"狂人"的意象再次凸顯出來。在那些"奴在心者"看來,一切的自覺者都是瘋子和狂人,一切的吶喊者和愛人者都是破壞"規矩"和"穩定"的壞人。這是東方社會特有的"眼光"。韓國學者金彥河在他的博士論文《二十世紀前半期中國文學中的瘋狂主題》中指出:"魯迅透過狂人和瘋子發現了缺陷文明和苛酷命運的韌性反抗者,即使它們是歪曲的形態;進一步他又發現了民眾潛在的革命動力和現實上歪曲外表之間的矛盾。"在寫《葯》的同一年裡,魯迅在雜文《暴君的臣民》中寫道:"暴君的臣民,只願暴政暴在他人的頭上,他卻看著高興,拿'殘酷'做娛樂,拿'他人之苦'做賞玩,做慰安。"顯然,魯迅與"民族魂"這個莫名其妙的謚號無關,他是這個民族最惡毒的詛咒者和最決絕的背叛者。這個民族有自己的魂嗎?魯迅的答案是否定的。正如金彥河所論:"魯迅認為,中國人本質上是吃人的人、暴君的臣民和死靈魂,並且中國文明不過是掩蓋這些醜惡本質的好看的外套。"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魯迅本人也是狂人和瘋子序列中的一員,他對"尋根"和"招魂"都沒有什麼興趣,那是國粹派們喜歡的工作。
說到底,魯迅依然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在《葯》中,沒有出場的夏瑜的聲音貫徹始終。夏瑜始終像一塊閃光石一樣,在屋子的角落裡默默地發著光;夏瑜始終像一團燃燒的火花一樣,在寒冷的冰川之中獨自發散著溫暖。夏瑜是一個自覺者,也是一個獻祭者。與其說夏瑜們是"中國的脊樑",毋寧說他們在人間活出了一個又一個具體的脊樑的狀態來--他們讓自己擁有了不屈不撓的脊樑,與"中國"無關。當夏瑜在說阿義"可憐"的時候,他的態度是誠懇的,同時也是堅強的;正如耶穌憐憫那些毆打他的士兵和群眾,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夏瑜們從來就不相信烏托邦和黃金時代,而這正是他們樂觀主義的基點。當耶穌走上十字架的時候,並沒有指望信徒們會為解救他而發起暴動,也沒有指望自己的鮮血立即就能喚醒沉睡中的人們;同樣的道理,當夏瑜在獻祭出自己頭顱的時候,並沒有奢望從此以後人人都成為“天下”的主人,也沒有奢望從此以後這個邪惡帝國就能迎來片片燦爛耀眼的陽光。
夏瑜們面對的是一個比他們強大千百倍的"無物之陣",譚嗣同面對過,林昭也面對過。你揮出拳頭去,卻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你的鮮血在流淌,這片像荒漠一樣的土地卻立即將它吸干。你連殉難者的命名也無法獲得,人們甚至會嘲笑你:看哪,那個傻瓜!人們成為看客,成為罪惡的一部分,這是龐大的犯罪計劃中最邪惡的一個章節。緬甸的人權鬥士——那個無比柔弱又無比剛強的美麗女子——昂山素季曾經說過:"極權主義是一種建立在畏懼、恐怖和暴力基礎上的系統。一個長時間生活在這個系統中的人,不知不覺會成為這個系統的一部分。恐懼是陰險的,它很容易使一個人將恐懼當作生活的一部分,當作存在的一部分,而成為一種習慣。"她揭示了這種制度的重要一面,而在我看來,它還有同樣重要的另外一面--極權主義體制還是一種建立在愚蠢、蒙昧和欺騙基礎上的系統。當恐懼和愚昧同時對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發揮作用的時候,邪惡就滲透進人的心靈和每一個毛孔之中。轉瞬之間,人的價值、人的尊嚴、人的權利和人的自由統統都將灰飛煙滅、不復存在。夏瑜的死亡悄悄地被歷史的書寫者置換成一出喜劇,人們看得津津有味。在單調的生活中,人們的感覺系統麻木了,有時倒還需要一點類似的"調味品"。
然而,夏瑜們還從奴隸和奴才的行列中勇敢地、絕決地走了出來。鎖鏈拖在石板路上發出刺耳的聲音,六月的陽光撫摸著他們青春的臉龐。這是北中國青草生長最為繁盛的季節,然而黃土已經準備接納他們的軀幹。他們是孩子,他們要不顧一切地說出"皇帝什麼也沒有穿"的真相;他們又是智者,他們不允許皇帝的陰影長久地擋住太陽的光芒。
正是有了夏瑜們的存在,我們才不至於對這個世界完全絕望。
從某種意義上說,夏瑜們確實成了我們這個罪惡民族靈魂重生的一劑"藥引子"--不過不是以"吃人血饅頭"的方式。
光緒三十二年的秋天,江南的街市似乎並沒有因為前不久的“造反”而顯得格外死寂,依舊是往日那般熱鬧。街市上隨處都可以聽到小販們叫賣大不列顛花布、法蘭西香水以及東洋米的吆喝聲。與街市相比,茶樓酒肆更是顯得熱鬧,似乎是因為革命黨在各地作亂讓食客們多了一些在茶餘飯後閑侃的資本。與此同時,幾個步履維艱、神情恍惚的癮君子和一個腦滿腸肥的“洋先生”走進了鴻賓樓。
此時的夏家,由於夏四奶奶整日燒香禮佛,以致宛若“仙境”一般。周圍的鄰居見此,也紛紛議論起來……
“我說他李嫂,這夏四奶奶這般禮佛,夏家出什麼事了嗎?”
“喲,他張叔,您還不知道呢?前一陣子革命黨作亂,而四奶奶的兒子夏瑜和革命黨來往甚密……”
“可不是嘛!上次我遇到這小子,他竟然和我說什麼`天下人所共有,非他滿洲一家`這樣大逆不道的話,若為官差所聞,怎生得了?我做長輩的訓斥他兩句吧,他卻罵我食古不化,沒有血性!我這侄子一向明事理,可自從認識那些革命黨之後,就變得這般頑劣,現世寶!”李嫂話說到一半,便讓路過的夏三爺搶去了。
張叔道:“哎!造孽啊!三爺,這次革命黨作亂你侄子夏瑜聽說也參加了。就在不久前,我看見他和一些人在說什麼事,好像是說造反的事。聽說這次革命黨造反連萬歲和太后老佛爺都驚動了,老佛爺嚴令各省督撫徹查此事,搜捕革命黨,一旦逮捕,格殺勿論!你家夏瑜為奸人蠱惑,此去恐怕凶多吉少……阿彌陀佛……”
夏三爺憤恨的罵道:“孽障!死了也罷,免得禍及我夏家!”
正當夏三爺與各位鄰居閑侃之際,夏瑜回來了,不過他並未理會周圍的鄰居和三伯,而是徑直向家中走去。夏三夜見狀,便匆匆離去。沒多久,夏三爺帶著幾個差役進了夏家,將夏瑜押了出來,往衙門去了。
夏瑜被逮捕,似乎並沒有影響周圍人的生活。幾天後,鄰居們依然在檐下閑侃。
“張叔,我聽說夏家那小子下大獄了,是吧?”
“可不是嘛,李嫂。我聽說正是因為造反,所以審也沒審就被官老爺下了大獄。當時若不是夏三爺上衙門說的話,夏家是要被滿門抄斬的。後來青天大老爺念他上報有功,讓交一些銀子打通上下關係,這才了事,才沒有禍及他人。”
“喲,牢里的阿義來了,去問問他吧。”張叔興奮地說。“阿義,夏家那小子怎麼樣了?”
“夏家那小子啊,可太不老實了,在牢里還要勸說牢頭造反哩!昨天我去盤問他,本想從他身上撈點兒油水,哪曉得這小子竟然窮的叮噹響,我什麼好處都沒落到!沒撈到油水也就算了,他竟然蠱惑我!說什麼大清江山是大家的、人人平等這些大逆不道的話,還說什麼民主,我當時正在氣頭上,他這樣一說我更是氣不過,就收拾了那小子。哦,對了,那小子明天就要被問斬了,我到時候給你們留幾個好位置,大夥兒一定要來看啊,殺頭可好看了!”
“好的好的。”張叔高興地說。
光緒三十二年深秋的後半夜,刺骨的寒風呼呼的吹著。幾隻烏鴉在暗藍色的天空中發出了凄厲的叫聲。囚車周圍圍著黑壓壓的人,囚車上的夏瑜雖高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但所換來的卻是陣陣喧鬧及撲面而來的爛菜梆子……
在丁字路口,人們都最大限度的增加自己的身高,爭相一睹血濺三尺白綾的狀景。只聽“噗嗤”一聲,觀刑的人眾齊刷刷地後退了幾步。
夏瑜的生命,宛若刑場上的露水一般,隨風逝去……但我們相信,黑暗終將逝去,黎明終將來臨。看吧,旭日正在冉冉升起!聽吧,自由之神在縱情地歌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