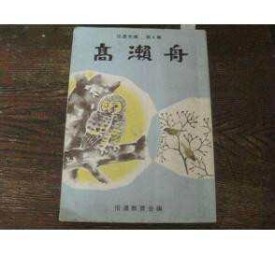高瀨舟
高瀨舟
《高瀨舟》是日本作家森鷗外創作的短篇小說,屬於作者所謂“脫離歷史”的歷史小說。於大正5年(1916年)1月發表在《中央公論》上。
小說描述了一個犯人在囚船上講述自己的經歷,取材於江戶時期的一部隨筆集《翁草》中的一篇小故事《流浪犯人的故事》,作者極大地發揮了想象力。
德川時代(1603-1867)京都的罪犯被府衙宣判為流放遠方小島時,需要由一個解差押解,先坐高瀨上的小船“高瀨舟”去大阪,此時作為慣例,允許罪犯的一個親屬同船陪同。寬政年間(1789-1801)某一日,京都智恩院的櫻花在暮鐘聲中繽紛飄零的靜悄悄黃昏,一個名曰喜助的30歲左右的犯人,坐上了一葉高瀨舟,如此氛圍描寫,飄蕩著悲情詩韻。通常情況下,“高瀨舟”上的流放犯,無不悲傷至極,與陪同的親屬徹夜長談,說的凈是些追悔莫及的絮叨話,凄凄慘慘。相比之下,無親無故的喜助卻迥然不同,他美滋滋的,好像在愉快地遊山玩水。“喜助的臉,無論橫看豎看,都像是很快活,甚至讓人以為,要不是顧忌解差,興許會吹起口哨,哼起小曲來呢”。押送喜助的解差羽田莊兵衛覺得此犯人神情匪夷所思,自己干解差多年,從未見過這等犯人。便問其緣由。作品以二人船上上交談為縱線,一步步展開情節。喜助對庄兵衛解釋道:京都是個好地方,但就自己的境遇來說,京都不是人間地獄。自己太貧困,居無定所,四處漂泊,拚命到處找活干,收入極少,飲食不繼,日子苦不堪言。今朝被流放,對自己來說是一件天大好事,終於有了落腳之地,再也不必四處流浪,有飯吃,還領到200文錢,這是自己迄今從未有過的幸福生活,所以由衷感到“超知足”。
聽了喜助此一番解釋,庄兵衛陷入沉思。他有四個子女,外加母親,一家七口。靠庄兵衛的祿米節儉度日。庄兵衛的老婆生於殷富商人家,花錢大手大腳,入不敷出,月底常回娘家要錢填補虧空。“窮時急,餓時吵”,家中常起風波。庄兵衛覺得即便如此,境遇也遠比與喜助好得多,然而自己卻常懷擔憂。按照常理,人有病時則分外憧憬無病的幸福;飢腸轆轆時則分外憧憬有飯吃的幸福;無錢時則分外憧憬有錢,而且錢越多越好,即所謂“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終朝只恨聚無多”。喜助卻相反,他是個出奇無欲的知足者。這種幸福的“知足感”,庄兵衛從未感受過。他因喜助“知足感”而深思,並開悟,肅然起敬,頓覺喜助形象高大。“庄兵衛覺得,仰望夜空的庄兵衛,頭頂上彷彿放出了亮光”。欽佩之餘,庄兵衛下意識地稱呼犯人喜助為“喜助先生”。
在高瀨舟上,解差庄兵衛又問喜助殺死胞弟的緣由,喜助細述原委。喜助父母雙亡,與胞弟相依為命,外出打工盡量做到兄弟形影不離。昨年秋天,哥倆進西陣的織錦作坊開織機,後來,胞弟患病喪失勞動能力,住在一間破敗窩棚里,哥倆全靠喜助一人微薄收入艱難度命。為減輕胞兄負擔,胞弟只求早死。趁兄上班之際,執剃刀割喉自殺,但割的深度不夠,未能如願。剃刀夾在喉嚨上,疼痛難忍。胞弟哀求胞兄幫忙將剃刀一拔,自己就可安樂死去。胞兄不忍,欲請郎中,被弟阻止,胞弟此刻痛苦不堪,一心只求早死為樂。胞兄無奈,歷經困惑,只好滿足了胞弟的哀求,這時“弟弟的眼睛豁然開朗,似乎很高興”。胞兄拔剃刀時碰到了沒割到的部位。胞弟如願,撒手人寰。
庄兵衛聽罷喜助的講述,心生同情。“同情是一種愛,此種愛使人對他人的幸福感到快樂,對他人的不幸感到痛苦”。庄兵衛心中懷疑:這能算殺人嗎?“如果就那樣不理不動,他弟弟遲早也得死。弟弟想快點死掉,因為受不了那個罪。喜助也不忍心瞧弟弟受罪,於是他就讓弟弟斷了氣,好使他從痛苦中解脫出來。這就是犯罪嗎?殺人,當然有罪,但是,一想到這是不讓人再受罪,不由得產生疑問,而且始終不得其解”。
森鷗外在德國留學四年,接觸過近代新思想的他回國后曾經致力於日本的近代啟蒙運動,並且進行了浪漫主義、反自然主義等文學的創作活動。1910年,日本政府製造了所謂的“大逆事件”,加強了對日本思想文化界的統治,森鷗外以此為契機轉向歷史小說創作,而且其作品思想也表現出了對封建傳統體制的一種妥協。
當時正值日本明治天皇駕崩歷史進入大正時代,它給與列強為伍而踏上苦難行程的近代日本帶來了一個轉機。作者身處時代的巨大變革,一方面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影響,培養了自由的精神和近代初步的自我覺醒;另一方面又受到以皇道為本的國家教育,森鷗外身為陸軍高官,因而會自覺不自覺地形成個人自由與國家秩序的矛盾與對立。
森鷗外出生在條件較為優越的醫生家庭,從小學習四書五經以及蘭學,綱常禮教的思想較為濃重。在《高獺舟》中表現出的是喜助、庄兵衛對封建等級制度的一種毫無質疑的信奉態度,也較為典型的反映了其創作者森鷗外的思想。
喜助
作品中喜助展現出來的是一個知足常樂的“殺人犯”形象。乘舟被押赴遠島的罪人們大都懊悔不己。而喜助卻沒有絲毫傷感之色,反而一副悠然自得的表情。庄兵衛問其原因,回答說:“去往遠島對於別人來說可能是件悲傷的事情,我也可以理解他們的心情。但那是因為他們在這個世上是享過福的人。京都是個好地方,但是我在這裡所受的苦,以後不管去哪兒都不會再有了吧。皇恩浩蕩,饒我一命。島上雖然艱難,但也不是什麼鬼棲之地。我從小居無定所,這次卻能夠在島上得到安居,確實得謝天謝地。雖然我身體不太健壯,但也沒有得過什麼大病。去了島上不管多累的工作,我都能應對。並且在出發前公家還發了二百文錢。”雖然當時“殺”弟弟確實是迫不得己,但從喜助的話語中卻絲毫找不到他對裁決的不滿,甚至對判決者展露出了感激之情。他的欲求是簡單而容易滿足的。更進一步說,喜助對自己的處境自始至終是認同的,沒有絲毫反抗的意識。自出生就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潛意識中已經接受了那種等級森嚴的社會階級制度。
喜助弟弟
喜助弟弟是在作品後半部分出場的。作者雖然沒有用大量文字介紹,卻刻畫了一個善良而又自尊的人物形象。因害病失去勞動能力的弟弟每天在家等著喜助買吃的帶回家。弟弟心地善良,加上經濟極度拮据,對於當時的狀況實在是過意不去。喜助弟弟深知自己的病無法治癒,便不想再拖累哥哥而選擇了以自殺結束自己的短暫人生。在用刀刎頸未成功之際,他請求哥哥幫自己結束生命來擺脫痛苦。求生本是人類的本能,喜助弟弟卻毫不猶豫地選擇並面對死亡。顯然,喜助弟弟是在充分考慮現實情況之後做出的決定,其選擇之理性、過程之堅決,時代的殘忍令人不勝唏噓。這充分揭示了作品的兩個創作主題,即:手足情深、安樂死。森鷗外有意識地刻畫這種長幼尊卑、手足情深,實際上是對傳統道德觀的一種肯定和妥協。
庄兵衛
從作品中對庄兵衛心理活動的描述,可以看出庄兵衛是富有同情心的人。他被眼前這個對現狀知足的“犯人”深深打動,從喜助的經歷中看到了自己,相比之下,自己的生存狀況態要比喜助好很多。聽完喜助傾訴境遇后他也曾質疑過權威。“殺人犯罪,這點毫無疑問。但若是為了解除痛苦而殺人,這能算是犯罪嗎?”儘管庄兵衛做了很長時間的思想鬥爭,但最終還是決定將判斷交給比自己地位高的人。對於喜助的遭遇,庄兵衛確實做到了“哀其不幸”,最終也沒有做到“怒其不爭”,甚至可以說庄兵衛本身也沒有絲毫“怒”的感情。
作品主題
《高瀨舟》描述了當時的社會環境與人的處境——日本封建幕府時期社會底層人民的生活慘狀。喜助和弟弟二人在京都做著非常低賤的苦役,而且收入連基本的正常生存狀態都難以維持,更嚴重的是疾病也相伴發生,窮困和疾病交加,主人公喜助即使拚命打工努力賺錢也是徒勞的,因為社會環境就是有錢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作為弱勢者的弟弟感悟到了這一切,他不願意看到愛他的哥哥如此徒勞地為他拚命打工,並且他也知道自己的病無法治好,於是割脖自殺。他自殺未遂,只得懇求喜助幫他從繼續苟活下去的苦難中解脫。可憐的喜助別無選擇,便拔出刀刃,划斷了弟弟的余脈,讓他滿意離去,幫助他實現了得以徹底解脫的“安樂死”。
在監牢里,喜助每天不用做事也可以吃上飯,這讓他“受寵若驚”,“光是這點,我就感到非常對不住衙門了”。主人公喜助即使拚命打工也無法治好弟弟;但被當成犯人,關在監牢里,喜助卻每天不用做事也可以吃上飯。現實竟然如此荒誕!甚至出獄后被押解流放海島,衙門又給他發了兩百文錢,相比以前的食不果腹,現在卻可以不勞而獲地吃到一日三餐,最後還領到二百文錢,這怎麼不能讓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滿足”?快樂的喜助並不以即將流放為憂。喜助竟然認為當囚徒或者被流放的生活比他原來的境遇還優越,所以處之泰然,這就更加深入地揭示了封建幕府時期社會的荒謬與黑暗。
喜助弟弟選擇死亡時,他是用死亡來確認他的實踐的自由,對於他來說死亡意味著合理的生存權利被剝奪和人的尊嚴受到侵害,從而使他應有的生存價值不能實現。作品體現出了人的自由意志與強大命運抗爭中所顯示出人的尊嚴和價值。喜助弟弟這個悲劇人物雖然在生前生活很艱辛,苦難重重,以致不得不選擇自殺,從結果上看是一個生活的失敗者,但他的精神境界卻高於他周圍的世界,這樣看來,與其說他被奪取了生命,不如說他從生命中得到了超脫。
面對生活的艱辛,喜助和弟弟的選擇卻截然相反,正是因為這種強烈的反差使我們深刻地感受到其悲劇性。喜助生性懦弱,他逆來順受地接受了苦難,對弟弟的描寫可以看出他面對死亡時表現出的堅毅,這才是真正的悲劇。《高瀨舟》展現出寬政年間白河樂翁侯掌權的幕府時代,幕府體制下貧困人民及下級官吏生活的極端悲苦,蘊含著作者對封建勢力,封建制度的嚴肅批判,體現出作者對既有社會道德的反叛,對生命價值的追求。
以一葉“高瀨舟”為舞台背景,森鷗外巧妙地將“知足”和“安樂死”兩個發人深省的主題穿插在了小說之中。但日本評論家長谷川泉認為“總覺得《高懶舟》只是因著個不同的興趣,把兩個主題拼湊到一起”“這是一部缺乏統一連貫主題的作品”,知足的問題和安樂死的問題是兩個分裂的主題。國內也有研究者指出,“實質上,兩者並無必然聯繫,如果對原作稍作改動的話《高懶舟》完全可以成為兩篇微型小說。”那麼兩個主題之間是否有聯繫呢?所謂“知足”是指不為慾望所苦,“安樂死”則是對生命知足,不去延續痛苦的生命。“安樂死”是“知足”的更深層的具體表現。兩者都是,將個體從痛苦的追求中解脫,都有著一種超然和淡泊。日本學者外尾登志美認為,兩者通過“自由”這一共同點聯繫在一起。前者是從物質追求中解放,獲得精神的自由,後者是擺脫時間的權威,獲得個人的自由,前者是對物質文明發展的近代,尤其是現代人而言的。後者是不受時間左右的永恆的自由。兩者一起構成了近代人所展望的完全意義上的自由。
藝術特色
作品的人物描寫與故事情節均具有很強的美學悲劇性,尤其是主人公喜助的弟弟面對災難敢於殊死抗爭,不惜以生命作為代價去超越苦難和死亡。他希冀突破生活現狀,實實在在打破周圍的平靜,使自我慾望得以實現,人格價值得以提升,不僅向我們展示出其所遭遇的不可抗拒的巨大災難與厄運,同時,也表現他不向命運屈服,敢於同厄運與災難抗爭的善美人性和昂揚頑強的生命力的悲劇性。
西北大學副教授曹汾:《高瀨舟》通過一個無辜獲罪的囚犯的自述和他被發落時的反常情緒,在客觀上反映了德川幕府時代下層人民的生活慘狀,並對長官老爺的滑稽判決提出質疑,給予嘲諷。但是,作家的主觀意圖是想宣揚安分守己、知足常樂思想,這當然是消極的。由於作家忠於生活,真實地再現了當時的社會現實,作品的客觀效果遠遠超出了作家的主觀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