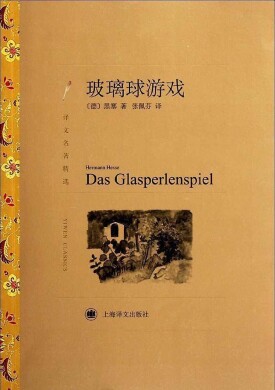玻璃球遊戲
玻璃球遊戲
《玻璃球遊戲》是黑塞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作品以長篇小說的形式出現,卻不是普通字面意義上的長篇小說,它用一系列象徵和譬喻編織起一種哲學上的烏托邦設想,虛構了一個發生在二十世紀后未來世界的寓言。

其他版本的《玻璃球遊戲》
作者從1931年開始構思此書,到1943年全書問世,整整用了12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初期,黑塞曾在一系列文章,尤其是在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里表達過自己最新的想法:要建立一種超越慣常好與壞概念之上的新道德意識,要對一切極端對立事物用統一眼光予以觀察。事實上,早在第一次大戰炮火正酣之時,黑塞目睹“愛國”概念競是沙文主義的土壤,自己還因反戰而被誣為叛國,就已撰文表白這一重要思想:“我很願意是愛國者,但首先是‘人’,倘若兩者不能兼得,那麼我永遠選擇‘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后,隨著希特勒倒行逆施的變本加厲,黑塞的想法也逐漸成熟,最終凝結成象徵性的《玻璃球遊戲》一書。
1932年,黑塞寫了書前格言草稿;1933年寫了引言草稿;1934年發表了後來成為附錄的《呼風喚雨大師》;1935年發表了後來成為小說主人公學生時代創作的大部分詩歌;1936年發表了後來成為第二篇附錄的《懺悔長老》;1937年發表了後來成為第三篇附錄的《印度式傳記》;1938年始寫玻璃球遊戲大師傳,該年寫完《感召》、《華爾采爾》;1939年完成《研究年代》、《兩個宗教團體》;1940年寫完《使命》、《玻璃球遊戲大師》;1943年,在瑞士出版了兩卷本《玻璃球遊戲》第一版。1945年,黑塞著作出版人彼得·蘇爾卡普僥倖從納粹集中營生還,獲得盟軍頒發的戰後德國第一張出版許可證后,立即著手《玻璃球遊戲》的出版事宜。1946年,《玻璃球遊戲》終於在德國問世。
小說主人公克乃希特從小聰明伶俐,刻苦好學,他被送到了卡斯塔里恩的精英學校。克乃希特在這裡接受了嚴格的教育與訓練,他汲取了東西方文化精髓,不僅熟諳西方先哲們的思想,也能靈活運用《易經》。他刻苦學習集世界文化之大成的玻璃球遊戲藝術,最終“玩”成遊戲大師,並擔任了精神王國的領導重任。他不斷探索,不斷超越自我,可內心的矛盾越來越大,以致開始懷疑這個精神王國存在的合理性,決心返回現實世界中去,從事有社會意義的教育工作。最後在與一學生游泳時溺水身亡。
故事發生時,時代已過去了幾個世紀,即2200年的未來世界。這個未來世界與今天的現實完全不同,它沒有戰爭,道德大廈也沒有坍塌,個人主義還沒有如此泛濫,總之,這不是一個精神受到污染、思想淺薄浮華的“副刊文字時代”。未來世界一個叫卡斯塔里恩的省,全國各地學校選拔出來的精英都來到這裡,他們之所以來到此,是因為他們看到了文化的衰落,可又無能為力,他們處於完全絕望的境地。這些飽學之士的目標是忠誠捍衛思想陣地,為價值的傳承服務,建設一個新的教育世界。他們致力於對所有學科和文化的綜合,而達到這一目標,掌握玻璃球遊戲技巧是必經之路。
從黑塞後期作品看,如《德米安》《荒原狼》《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等,現實社會的輪廓的確不夠清晰,而《玻璃球遊戲》的這個特點最為顯著,卡斯塔里世界是面目模糊的,然而,是否據此便能推論黑塞的小說脫離社會、脫離世界呢?這是值得商榷的。黑塞處理時代和現實的浪漫主義方式在其自身所處的文學傳統中固然 有跡可循,但他所面對、所質疑的時代精神畢竟已與德國浪漫派時期迥異,他的立場與德國浪漫派的立場相比也發生了改變,這突出表現在黑塞對世俗世界即“真實生活”的態度上。
文章開頭已經提到,在黑塞的作品中,精神王國與世俗世界、精神與自然之間始終存在一種張力。主人公對生命終極意義的探尋與獲得有時通過自然,比如歌爾德蒙式的;有時則通過精神,比如克乃西特式的。不過假如多做一些思考,我們就會發現,即使在《玻璃球遊戲》中,生命意義的實現也並非僅僅通過精神。卡斯塔里之外始終存在著一個廣大的世俗世界,克乃西特本人就是這個世界的孩子,他只是經後天培養成為一名卡斯塔里的“精神貴族”,並最終選擇了返回世俗世界。除了卡斯塔里借音樂大師的形象曾向克乃西特發出“感召”之外,自從克乃西特進入精英學校,世俗世界或“真實生活”也頻頻向他發出召喚。小說開頭幾章已經為克乃西特後文的轉變打下伏筆,其中包括克乃西特因為同學被開除離校引發的思緒,包括華爾采爾帶給他的初步印象;包括約可布斯神父向他展示的歷史觀;體現在代表世俗世界的普林尼奧·特西格諾利身上,更集中體現在克乃西特辭去大師職位、返回世俗世界的選擇上。主人公的這種選擇表明,《玻璃球遊戲》 雖然同黑塞後期大多數小說一樣,具有探索內 在精神的傾向,但它從未“脫離世界”。
實際上,“世俗世界”一詞在黑塞那裡有著豐富而複雜的內涵,它既催生出副刊文字時代,又孕育出卡斯塔里精神王國。卡斯塔里實際上依賴世俗世界供養,無法脫離後者獨立存在。那麼,在《玻璃球遊戲》中,作者是如何描寫一個與卡斯塔里相對照的“自然”的呢?傳記的結尾部分寫道,主人公走進代表自然的高山世界,那裡的風景既生動又猙獰。雖然描畫的手法仍然是象徵化的,但顯然同卡斯塔里的刻板、嚴謹構成鮮明的對照,比如下面這一處:“車子經過那些院牆高高、窗戶小小的農舍后,便馳入了一個更加崎嶇、更加粗獷的怪石嶙峋的高山世界,在這些堅硬冷峻的岩石間,竟有許多一片片天堂樂園般的綠地,使點綴其間的朵朵小花顯得格外可愛。”
卡斯塔里與世俗世界中 兩種面貌不同的風景描寫隱喻性地傳達出黑塞對待“兩個世界”的基本觀念:精神王國有序、和諧卻失之呆板,世俗世界生機盎然卻危機四伏。克乃西特最終死在自然世界的湖水中,從這個意義上說,《玻璃球遊戲》書寫了一個精神的人如何走向自然、走向真實的生活,即一個納爾齊斯如何從精神王國進入世俗世界,如何將精神融入自然。克乃西特從服務、奉獻的意願出發,試圖彌補兩個世界之間越來越大的裂痕,他的理想是“將卡斯塔里的基本精神注入世俗青年內心,化為他們的血肉”。這實際上嘗試性地回答了歌爾德蒙臨終前向納爾齊斯提出的問題:“可你將來想怎樣死呢,納爾齊斯,你沒有母親?人沒有母親就不能愛,沒有母親也不能死啊。”
少年特西格諾利曾這樣描述他與克乃西特的區別:“你站在培養精神這一方,我則站在符合自然生活這一邊。你的職務是指出:缺乏精神滋養的自然生活會陷入泥潭,會轉化成獸性,甚至必然越陷越深。因而我不得不一再提醒你們,純粹建立在精神上的生活是多麼冒險,多麼可怕,最終必然一無所獲。嗯,我們各以自己的信仰為優而辯論,你為精神思想,我為自然生活。”
精神與自然的分裂是西方思想史上重要的論題,也是德國浪漫主義嘗試解決而未能解決的問題。這個遺留的問題在現代文學作品中反覆出現,比如在托馬斯·曼的《魔山》那裡,精神與自然曾是塞塔姆布里尼和納夫塔之間論辯的兩個核心辭彙。那麼,何為精神、何為自然呢?美國學者拉爾夫·弗瑞德曼(Ralph Freedman)在分析黑塞的作品時對兩個概念的內涵進行了簡單總結:
精神既是心靈的也是智識的,它包括多重內涵,即從父權般的控制、調節直至對理性文化的破壞,不過通常情況下它更多意味著神聖理性精神的明晰性。其對立面自然則既是感官的也是靈魂的,與性、縱慾、感覺相關,並認同母親的形象或集體無意識。
這一概括體現了精神與自然之關係的複雜性:精神與自然相互對立、相互補充,同時由於精神也包括對理性文化的反思,於是精神與自然又有發生交集的可能。在《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中,納爾齊斯是精神之子,歌爾德蒙是自然之子,他們的天性決定了各自的道路。在《玻璃球遊戲》中,黑塞對“精神與自然”這一關係的探索似乎更深了一層,特西格諾利同克乃西特的關係不是歌爾德蒙與納爾齊斯關係的簡單翻版。特西格諾利與克乃西特雖然起初各有各的道路,但在文章的後半部分,當特西格諾利在世俗世界中飽受創傷時,他通過克乃西特的指點將卡斯塔里精神注入自己的生活,獲得了身心的平靜;而克乃西特也在個人的覺醒體驗和特西格諾利等人的影響下最終懷著服務與奉獻的 意願走向了世俗世界。可以說,特西格諾利與克乃西特在某種程度上發生了對雙方有益的中和。作者似乎是要藉此暗示,過於偏重精神或者過於偏重自然的生活都是有問題的,在兩者之間應該探尋一種 更平衡、更和諧的道路。
同時,小說的標題、副標題、題詞以及尾聲處處都提供了一種暗示:卡斯塔里的確是一個烏托邦,但它是一個已經進入肅殺秋天的烏托邦。像克乃西特個性之中的分裂以及玻璃球遊戲的二重性一樣,這個烏托邦也是一個二極分裂的宇宙之再現以及二極分裂的精神生活之象徵。1943年小說一問世,關於卡斯塔里究竟意味著什麼這個問題就馬上出現了兩種對立的看法:一是認為它是烏托邦國家的再現,二是認為它是衰敗頹廢的象徵。如果從包容萬有、涵蓋乾坤、主導靈魂的“二極分裂”觀之,這兩派意見各執一端,合則完美——卡斯塔里是一個正在衰頹的烏托邦。
隨著遊戲大師克乃西特的成長、求學、成功及最後加冕,卡斯塔里漸漸解神聖化了。在這個宗教組織里,個人無足輕重,隱姓埋名是他們的基本做法。想撰寫遊戲大師生平的作家都無法輕易地使用秘密檔案,只能從遊戲大師的學生那裡獲得一些隻言片語。即使是榮登遊戲大師寶座的克乃西特,其日常行為也必須接受嚴密的監護。在卡斯塔里,只有下屬以“您”或者“閣下”來稱呼上司,而上司總是習慣於居高臨下地對下屬頤指氣使。更可怕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交談總是使用反諷修辭術,言在此而意在彼,聽者詫異而言者迷惘,這表明在卡斯塔里缺乏真誠。卡斯塔里王國的最高統治者亞歷山大宗師那雙眼睛既可以放射出發號施令的眼光,也可以放射出虔敬服從的眼光,但對於這個宗教團體的一般成員而言,只有虔敬服從而永遠不可能發號施令。亞歷山大宗師、音樂大師、前任遊戲大師托馬斯、克乃西特的忠實奴僕德格拉里烏斯以及克乃西特本人都是一些孤獨的天才、孤獨的先驅者和無意識的虛無主義者,對他們而言,即使是“獨斷專行”,本質上也是奴隸一般地服從。克乃西特在想象中向亞歷山大宗師吼叫:“(我)追尋的不是自由,而是某種新的、不可知的隱秘約束;(我)不是逃兵,而是響應感召的人;不是任意專行,而是聽從命令;不是去做主人,而是要成為奉獻者!”
覺醒了的克乃西特感到卡斯塔里不是天堂,而是由神秘官僚制度、森嚴等級關係構成的地獄。他要穿越這個披著神聖光輝然而卻冷酷無比的空間返回到世俗世界,從靜觀冥想者變成身體力行的服務者。“在卡斯塔里人的眼裡,世俗世界的生活是一種近乎墮落和低劣的生活,那種生活無秩序可言,既粗魯又野蠻,既混亂又痛苦,可以說是一種全無美好與理想可言的拙劣的生活。”但是,“外來人”普林尼奧反問:
難道這不是一個虛偽、教條、沒有生育能力的世界么?這難道不只是一個苟且偷生的虛假世界么?這裡的人沒有負擔、沒有苦惱、免受飢餓,卻也沒有果汁和飲料。這也是一個沒有家庭、沒有母親、沒有兒童的世界,甚至幾乎也沒有婦女!人的原始本能被靜坐入定功夫所控制馴服了。
當克乃西特受本篤會約可布斯神甫啟發而懷疑卡斯塔里、懷疑這架複雜而又敏感的機器是否已經老邁而主張求助於世俗歷史時,卡斯塔里忠實而又孤獨的奴隸德格拉里烏斯卻告訴他:“所謂歷史,卻是又醜惡又可怖,同時也是無聊乏味的東西。”卡斯塔里日益精細純粹,這個神聖教育區同外在世界之間的深淵也日益擴大,以至於完全沒有可能彌平。當戰爭和瘟疫的時代降臨,當歷史風暴席捲整個世界,卡斯塔里及其遊戲的精緻形式已經無力維持生存。在卡斯塔里神聖秩序里苟且偷生的人們,都像黑塞在《一個提契諾人的故事》之中所描繪的馬里奧那樣,在兩個彼此分裂卻又生死相關的世界之間痛苦掙扎,但不可遏制地嚮往著自己的青春與故鄉。“故鄉就是母親、婆姨”。“故鄉就是二月在濕潤的草地上摘花,是夜晚的鐘聲,這故鄉真實而美好,受人愛戴,主宰著他的生命。”克乃西特最後在高山冰湖自沉,真正地返回到了自己的故鄉。男孩鐵托在初生的太陽下赤身裸體,跳起了獻祭之舞,與四周波濤起伏的光芒融合,與宇宙生命之流合二為一,遊戲大師也在這壯美的景象之中透悟了內心深處最高貴的本質。他跳下冰冷的高山湖,湖水似乎不是刺骨的寒冷,而是焚燒著他血肉之軀的熊熊烈火。他返回到了母親溫暖熱烈的子宮,無怨無悔。此刻,他沐浴著來自東方的光輝。
克乃西特壯美回歸后,卡斯塔里才真正成為一個屬靈的王國,那是諾瓦利斯所期待的“一個偉大的和解時代”,“一個預言的創造奇迹和治癒創傷的、給人帶來安慰和點燃永恆生命的時代”。在《印度式傳記》里,這就是王子達薩體驗到了世界的“瑪雅本質”之後的世界,“世界根本不存在熄滅,生命的輪迴永無盡頭”。在短暫的一瞬間,王子從監獄里走出來,失去了妻子、兒子和一個王國,卻融入了森林中無疆的大愛,超越圖像與偶像而進入了“聖靈世界”。世界超越了音樂大師仁慈、博愛、聖潔的音樂所放射的光輝,超越了戰爭和瘟疫籠罩的廢墟,超越了老邁龍鍾、機械冷漠、枯萎蕭瑟的狀態,進入了神話世界里的春天:美麗、快樂、神聖、光輝燦爛的黃金時代。
《玻璃球遊戲》所敘述的是卡斯塔里的衰敗階段,是烏托邦的秋天,但黑塞用隱微之筆傳達了神聖再度降臨的暗示。純粹精神形式的卡斯塔里、以古典音樂境界為至境的玻璃球遊戲,是一個充滿審美誘惑的烏托邦,本質上是一種奴役:“美感的誘惑與奴役總是削弱個體人格價值,並取代個體人格的生存核心,扭曲整體的人。”而瀰漫著父權強力意志、強調服役義務、建構嚴密制度的卡斯塔里,是20世紀道德意識的象徵,是極權主義政治的幽靈王國。“神話的暴力要求犧牲”,“以一己之偏好執行對神聖生命的滅絕”。最後,那個以遊戲大師的生命所贖回並且沐浴在東方的光輝之中的卡斯塔里,則是“第三王國”,即屬靈的王國,這就是以母性來象徵的故鄉和青春:“這個來自聖靈的第三種幸福也許就是奧利金所說的萬物的復歸。”正如保羅所說:“讓神在萬物之上,為萬物之主。”
另外,《玻璃球遊戲》融合了西方傳統和東方思想,在兩個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之間建起一座橋樑。黑塞把東方文化視為自己的精神故鄉,古老燦爛的中國文化給他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養料與素材。然而不能忽略的是,對於黑塞來說,探尋解決西方文明危機的出路,始終是第一位的。他說“我必須在精神上和感情上把握住真正的歐洲和真正的東方”。他借鑒與採納東方文化的精華,將其同西方文化傳統中依然有價值的東西加以整合,目的也在於找到一條西方和諧發展之路。
黑塞的《玻璃球遊戲》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這部作品對黑塞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起了很大的作用。

赫爾曼·黑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