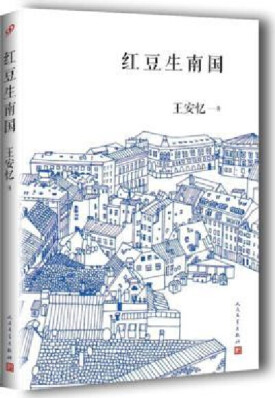共找到6條詞條名為紅豆生南國的結果 展開
- 王維創作詩句
- 2009年童麗發行專輯
- 王安憶創作中篇小說集
- 2018年拍攝電視劇
- 電影
- 凝隴著圖書
紅豆生南國
王安憶創作中篇小說集
《紅豆生南國》是作家王安憶創作的中篇小說集,首次出版於2017年6月。
該小說集共收錄《紅豆生南國》《向西,向西,向南》《鄉關處處》三部中篇小說,三部小說分別發生於中國香港、紐約和上海,講述了生活在這三個城市的“都市移民”的故事,從而表現了人物的青春,愛與孤寂。
2018年5月31日,《紅豆生南國》獲第二屆京東文學獎(中國作家作品)。
《鄉》:巷弄,鄉娥輾轉城市鄉村,論鍾,節鄉,踏歡騰。速融城市,歸鄉村。娥眾,投宿爺爺娥久違舒。爺爺叱吒雲,曾膠廠廠,陷三角債中,差點深陷囹圄,晚年雖不富裕,但也到了兒女反哺的時節,生活過得不至拮据,月娥的加入也為其安然無虞的生活平添了色彩。月娥在爺爺家養了一隻通體雪白、耳朵異色的貓,月娥喚她“爹一隻娘一隻”,月娥疼愛這隻貓,所以當爺爺得了濕症和哮喘時,爺爺女兒執意要把貓送給河南人時,月娥據理力爭,留下了這隻貓。在月娥節前返鄉前最後一次帶著同鄉們和爺爺聚會,她和這些同鄉們一樣,已非當年剛從鄉下來的、兩手空空、每一分錢都得捏出油地攢的“異鄉人”。小說結尾,月娥帶著“爹一隻娘一隻”回到農村。
《紅豆南》:幼貧,“百番薯絲”換養。養六偷渡南洋尋養,落腳香港島。艱苦,養濃烈粗暴,養供讀育,,娶妻,,跟二致。未片刻穩踏歸屬。雲激蕩五六棲遑紀末,香港童青春;歷運、戀、婚姻、喪、離異、尋系列浮沉,晃。忐忑、猶疑、恩養恩孰孰抉擇,思細密,,懷抱濃,予敢收,思。逐般旅,寶島台灣南端墾丁,看見了叢叢簇簇的紅豆,俗稱“相思豆”。心驚之餘,有如大夢初醒。
| 鄉關處處 | 紅豆生南國 | 向西,向西,向南 |
2016年年中,王安憶受邀去紐約訪學半年,沒有日常瑣事打擾的日子裡,她寫出了《紅豆生南國》和《鄉關處處》,同時構思了《向西,向西,向南》,回國後於2016年10月27日完稿於上海。《紅豆生南國》是王安憶自20世紀90年代初寫作並出版《香港的情與愛》后,又一次寫發生在香港的故事,她稱創作初衷是“為了寫一寫人世間的一種情”。
他:《紅豆生南國》中人物。他是養母用“三百斤番薯絲”買來的,這“三百斤番薯絲”的價值令他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耿耿於懷,直到他和養母要一起去菲律賓尋找養父時,大船擱淺,他差點丟掉性命。而這一次劫後餘生也冥冥之中將這對母子徹底帶去了異鄉——香港島。他在異鄉慢慢長大,讀愛國學校,偏愛戴望舒、徐志摩,還有林徽因,也愛香港氤氳集散的天空。在這裡,他認識了妻子,也組建了家庭,雖然這段婚姻在阿姆去世后最終瓦解,但夫妻二人並非形同陌路,也都在尋找著複合的可能,卻也更願意遵從內心選擇。也許是沒有了家庭牽絆,也許是中國人認祖歸宗的傳統不自覺地膨脹,他選擇回歸閩南故里找尋生母。
月娥:《鄉關處處》中人物。月娥是一個從紹興農村到上海的外來打工者,在班車上,她惦念著留守在家的丈夫五叔和兒子、媳婦,想到了極遠的終了,還是要回來面對現實,對即將開始的上海的異鄉生活仍存在著衣食住行的多方焦慮。在上海,月娥盡其所能地跟上此處的快節奏,與時間賽跑,輾轉多個主雇家,給“外國女婿”一家做保姆,在商場做保潔,幫同鄉頂工。許多東家的形貌都在輾轉中日漸模糊,只有投宿的爺爺一家讓月娥感到了久違的舒心。
徐美棠:《向西,向西,向南》中人物。在紐約經營中餐館,她的“准丈夫”福建人得了重病需要換肝。小說結尾,她和陳玉潔在在美國西部的南岸加州聖迭戈以南,共同經營了一個餐館,生意還算紅火。
陳玉潔:《向西,向西,向南》中人物。陳玉潔是一家外貿公司的公關經理,因工作的緣故在上海與漢堡兩地往來頻繁。二十年前,迫使陳玉潔和丈夫脫離體制自主創業的動因是住房局促,後來她和丈夫的事業在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夾縫中左右逢源,賺了錢,買了高檔社區的商品房,因為女兒高中畢業,要去美國讀大學。在女兒的慫恿下,陳玉潔準備在美國買房,在美國穩定下來,沒想到丈夫的背叛讓一切變成了白日夢。
《紅豆生南國》講述了男主人公自移入香港之後所展開的人生歷程。在這部小說里,王安憶在延續自身重於描寫個體經驗和日常生活創作觀念的同時,不再局限於對男女情愛的表現,而是從人與人的實際關係中抽出了一個超越於愛情、親情等情感形式之上的詞語,即恩情,以此表達出她對世態人情的理性思考和對倫常的再解讀。小說在主體層面上說的便是人與人之間所存的“施恩和報恩”的關係,“我”的大半個人生就陷入了應對種種恩情的境遇中:養母之恩,生母之恩,妻子之恩以及其他女性所給的愛情之恩,並時刻想著報恩,懷著感激的態度對待一切人事。“恩情”是王安憶對於人與人之間,甚至人與世界之間的關係的解讀。
“情與愛”作為香港的城市精神一直漂浮於王安憶對香港的寫作中,《紅豆生南國》中,王安憶不僅視“情與愛”為“香港”的精神內涵,還將之擴展為一種超越具體情感形式的“有情”屬性,與“我”的性格內容有了契合點。“我”的“有情”恰恰是“香港”這座城市於市井層面中有情有義的體現。另一種是二者都形成了“離鄉——歸鄉”的命運結構:被賣的“我”跟隨著阿姆離開內地進入香港,後來又從香港回到了內地尋找生家,“香港”也同樣走過了因被侵佔而離開故土后又“九七回歸”的歷程。如果說,文藝報刊上開闢的“故鄉情”一欄寄託著“我”自身所懷有的“離鄉和歸鄉”情感,那麼,這種“故鄉情”實質上不僅僅是“我”的情感,還是香港人的,是香港這個城市的。進而言之,“我”和“香港”也共同面臨著自我身份認同的問題。這源於精神內涵和歷史命運方面的同構性使得“我”的命運和心理不再具有純粹的獨立性,而是變成了對一座城市的鏡像式演繹,進而造成的結果是小說在寫“我”的人生歷程時常會發生“越界”,使得原本作為歷史背景存在的“香港”變得異常凸顯,從而“溢出”成為了文本的書寫對象與意義所指。
《向西,向西,向南》中,陳玉潔、徐美棠在域外萍水相逢,“向西,向西,向南”是她們一路遷徙的人生路線,她們在“異鄉”回望“原鄉”,“原鄉”的根捆綁著兩個在“異鄉”掙扎的靈魂,鄉愁被轉換為因積極尋求更好的生存空間而產生的情感支撐。兩個人在“異鄉”的自我救贖與自我實現,最終實現了對“異鄉”由對峙到認同的情感過渡。《鄉關處處》則將鏡頭探入王安憶熟悉的上海巷弄,以小人物月娥波瀾不驚的生活照見城市與鄉村的對峙融合。
王安憶在該小說集中,以極其細膩、平緩的基調呈現出“原鄉”與“異鄉”的具體圖景,藉助“原鄉”與“異鄉”的雙重視閾,關注徘徊於“原鄉”與“異鄉”之間的都市移民個體的生存現狀與精神世界。小說集中“原鄉”與“異鄉”的一種打破二元對立的、和解的、良性的交流,是一種從對峙走向融合的認同關係。最初的對峙來自於人們初到“異鄉”的物質局促與精神困頓,而作者並未將筆觸停留在這種困境之中,而是在“異鄉”感受到挫敗和艱難時依舊能夠堅強地走下去,最終能夠在積極地與“原鄉”融合時,坦然回望“原鄉”的嶄新姿態,在“異鄉”落地生根,以理性開放的文化身份找尋到了“原鄉”與“異鄉”交匯的最佳著力點。
《鄉關處處》描寫了保姆月娥,實際上,鐘點工、保姆和護工已經構成了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當代小說對他們的描寫數量不多,方式和結論也就幾種。王安憶的描寫,既是單個獨特的人的刻畫,又是為這個人所處的社會結構賦形,難得的是,這兩種動機在小說里互相成全和生髮,而不是互相貶損。小說涉及種種社會問題,如鄉村的“空心化”,然而月娥的活力、耐力和樸素識見本身是自鄉土中長出,也正是這種活力、耐力和樸素識見,填充進了城市,對城市的運轉至關重要,由此也使鄉土和城市建立起新的關係。在月娥們的現實中,上海符號化的存在變得不再重要,它就是一個通過千千萬萬的勞動者的遷徙而成就了的空間。令人感動的是,無名者的“生計”同時也創造出了他們自身的個性與面貌,一種真正的人物的個性自由因此而誕生。
“香港”這一元素在《紅豆生南國》里的重要性遠遠高於一般情況下的城市書寫,因為它在成為人物活動背景的同時也成為了小說的寫作對象,雙重角色使它獲得了一種可超越於人物而獨立生成意義的地位。此時,這裡的“香港”便類似於《香港的情與愛》《長恨歌》里的“香港”和“上海”。換言之,《紅豆生南國》對城市的想象既抓住了香港城市的精神實質,又將城市的歷史轉化為人物的命運,從而以人物的“有情”人生實現了對“香港是有情的”這一定義的詮釋,以人的命運遭際和心理變動推展開了“香港”回歸前後的歷史及其精神世界。
《人民日報》:初讀這幾部新作,書頁里凸現的依舊是人們熟悉的王安憶綿密從容的風格,其文筆精緻老到,幾入化境。她拋棄了冗長、重床疊架的歐式語句,多用平易樸實的短句,圓熟中透出樸拙,使全篇增添了幾分古典白話小說的神韻氣象。昔日杜甫評價庾信的詩句“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用在她身上也是合適的。
《華商報》:王安憶在《紅豆生南國》中,用她的文字,帶讀者重新發現人性中的善良和溫情。
| 出版時間 | 出版社 | ISBN | 版本備註 |
| 2017年6月 | 人民文學出版社 | 978-7-02-012626-2 | 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