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普
普洛普
弗拉基米爾·雅可夫列維奇·普洛普(Владимир Яковлевич Пропп,Vladimir Propp,1895—1970)當代著名的語言學家、民俗學家、民間文藝學家、藝術理論家,是蘇聯民間創作問題研究的傑出代表。他雖然不是俄國形式主義學派中的一員,但他於1928年出版的《故事形態學》一書在研究方法上與形式主義有相通之處,所以也被看作是20世紀形式主義思潮的一個推波助瀾者。在民間創作研究領域開闢了獨具特色的研究方向和方法,享有世界性的聲譽。
1895年生於聖彼得堡,1918年畢業於列寧格勒大學文史系斯拉夫語系俄羅斯語文專業。自1918年至1928年在列寧格勒的幾所中學講授俄語、德語和文學。他後來40年的學術生涯是在國立列寧格勒大學度過的,在那裡他教授民間文學課程,並出任過民間文學教研室主任。1966年他在該校退休。其間在國家地理學會、東西方語言研究所、藝術史研究所、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從事過學術工作。
普羅普是著作等身的著名學者,國際學術界往往重視它在結構主義藝術形式分析方面的巨大成績,其實他在非結構主義方面的研究著作也是相當豐富的。他的代表著作包括:《故事形態學》(1928)、《神奇故事的歷史根源》(1945 )、 《俄羅斯英雄敘事詩》(1955)等著作;此外他還發表了數量頗多的學術論文、評論文章,甚至還選編了數部民間作品集。

普洛普
在這部著作中,普洛普不滿於傳統的民間故事研究方法,提出了一種嶄新的民間文學研究思路。他認為,傳統的以敘事母題,如俄國民間故事中常見的“三兄弟”母題、“護身符”母題、“與毒龍搏鬥的英雄”母題等等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民間故事研究方法是一種不嚴謹的研究方法,因為一個母題下面可能包含若干子母題,我們很難找到一個最小的不可再往下細分的單位來作為分析的出發點。也就是說,母題是一個可變項,它不可以作為我們研究它出發點;真正科學嚴謹的研究應該從“不變項”或“常項”入手。為了達此目的,普洛普從人類學中引進了一個概念——“功能”,把它作為分析民間故事的最基本單位。功能單位是指人物的行為,行為之成為功能單位,依賴於其在整個故事發展中所具有的功用或意義。從這個原則出發,普洛普對俄國100個民間故事作了極為細緻的研究,從中歸納出了故事的31種功能,並得出以下幾個重要結論:1.功能在童話中是穩定的不變的因素,功能構成童話的基本要素;2.民間故事已知的功能數量是有限的;3.功能的次序總是一致的。
普洛普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他的功能概念:
普洛普認為,以上三個情節中人物身份雖有改變,但其基本作用或功能是一致的。也就是說,它們在整體故事中承擔的職能是一致的,因此,它們可以被歸為同一個功能單位。
在一篇故事中,除了功能單位,還包括其他因素,如功能單位之間的關聯與重複,人物行為的動機在故事中是否明確表明等等。與功能單位結合最密切的因素是“人物”,人物與功能單位通常有一定的對應關係,性質相關的功能單位常常組成一系列連續的行動,這個連續的行動往往屬於某個特定的人物。特定的功能單位與特定的人物相結合,構成所謂的“行動領域”。
在不同的故事中,同一功能單位可能會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同一角色也可以由具有不同屬性的人物扮演,比如上面所舉的例子:“沙皇以蒼鷹賞賜主角,主角駕蒼鷹飛向另一國度”,“老人以駿馬贈送主角,主角騎馬至另一國家”,“飛向另一國度”與“騎馬至另一國家”實際上是同一種功能單位的不同表現形式,而“沙皇”與“老人”是一對可以互換的人物,二者承擔的也是同一個角色。同樣一個角色,之所以在不同的故事中會由不同的人物來扮演,是因為地方習俗、宗教、儀式、文化背景等外界因素的影響。同一個角色的不同“變形”之間的變換常常有一定的規則可循,普洛普稱這些規則為“變換規則”。
功能是敘事作品的最小單位,功能之上的單位是“回合”。所謂“回合”,是由一系列功能單位組合而成的敘事單位。比如,故事的開始是災難或反角的作惡,這算是一個功能,然後又經過一系列其他的人物動作也即功能之後,災難消失,惡勢力被消滅,最後是大團圓的“婚禮”——這樣一整個過程,普洛普稱之為“回合”。一個故事可能由一個回合構成,也可能由數個回合組成;回合之間也有不同的組織關係,可能是兩個回合首尾銜接,也可能幾個回合互相重疊,也可能一個回合未完之際又插入一個新的回合,總之沒有一個定則。
通過對功能和回合的精細分析,普洛普總結出了一整套民間故事的敘事規則和敘事“公式”,他認為,用這些公式便可以代替所有的俄國民間故事,所有的民間故事都不過是這些公式的不同表現形式,正如所有的算術習題都只不過是少數數學公式的不同演算形式一樣。普洛普甚至還認為,我們完全可以依照這些敘事公式“創造”出新的民間故事。
具有戲劇意味的是,《民間故事形態學》這部被譽為結構主義奠基之作的名著,在其出版之初並未引起學術界的注意;直到30年後它的英譯本問世,這部著作以及它的作者普洛普才聲譽雀起;敘事學大師如列維·斯特勞斯、克洛德·布雷蒙、格雷馬斯等,都從這部作品中汲取過營養。甚至可以說,這部書哺育了整整一代結構主義者。但是撇開它的重要性不談,我們認為,作為一部文學研究論著,《民間故事形態學》的缺陷和不足也是很明顯的。文學藝術是無限豐富、無限多樣化的存在,任何一種概括或總結都無法窮盡它的全貌。《民間故事形態學》試圖用幾個有限的公式,將所有的民間敘事藝術一網打盡,這顯然是一個很難實現的設想。並且,藝術的真正難解之處是其感染力和表現力,而不是其形式,即便我們將藝術形式分析得頭頭是道、十分完備,我們還是沒有涉及最根本的問題所在:藝術作品的動人之處究竟來自何處?
普洛普的弊端也是整個俄國形式主義的弊端:片面地強調文學的形式因素,排斥社會、歷史、作者的個人經歷等對文藝作品的影響,把文藝研究封閉在一個形式的圈子裡,這種做法從根本上違背了他們試圖解答文學藝術的特殊問題的初衷。

普洛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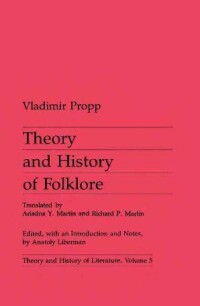
Theory and History of Folklore 封面
進入20世紀90年代,普洛普研究開始觸及細部問題,對已經凸顯出來的問題進一步深入探討。當然,這個深入的過程也是與結構主義在我國的深入研究相伴的,主要涉及基本概念和命題研究,我國敘事學理論的建構,普洛普學術身份認定和歸屬問題研究、學理運用等。但由於依據的材料依然是俄譯的二手材料(也為數不多)或英譯、法譯的三手材料(占絕大多數),而且仍是只觸及了普洛普理論的“功能論”方面,所以對普洛普的認識顯得似乎得了“真經”,但尤未識其“真面”。因而我們稱之為“亦真亦幻”的又十年艱難探索階段。
進入新世紀(材料截止到2004年),學者開始以第一手俄文材料為依據,這大大推進了普洛普研究,一些似是而非的認識得以澄清,一些“盲區”得以展現,對其理論的運用也更加靈活自如,且經過加工、改造,普洛普理論在我國已經進入對多種敘事體裁作品的分析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