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穩
范穩
范穩,四川人,中國作家協會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1985年畢業於西南師範大學中文系(現為西南大學),同年到雲南省地礦局工作。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文學創作,以小說創作為主,先後發表中長篇小說及文化散文四百多萬字。近年來主要在藏區大地遊歷,執迷於雪山峽谷和廣袤無垠的高原牧場,對藏民族文化與宗教情有獨鍾,有多部反映藏民族現實生活及歷史文化的書籍問世。

范穩
已發表各素文學作品二百萬字。已出長篇小說四部:《騷庄》、《冬日言情》、《山城教父》、《清官海瑞》中短篇小說集兩部:《回歸溫柔》、《男人辛苦》。報告文學一部:《生命與綠色同行》。文化大散文三部:《蒼茫古道:揮不去的歷史背影》、《人類的雙面書架》、《藏車探險手記》。曾獲得2003年度“中國作家大紅鷹文學獎”
《水乳大地》為范穩的力作之一,小說以西藏東部邊緣地區一個世紀以來的風雲變化為背景,塑造了一群非常有特點的人物形象:有藏傳佛教的活佛,納西東巴教的代表,基督教的傳教士;有紅漢人的幹部還有不懼天地鬼神的康巴漢子,以及西藏土著宗教苯教鼻祖的魂靈,小說就是在這種宗教和現實交錯、多種民族混居、多種文化相互衝撞與融合的氛圍里,打造出了一系列慘烈而有光彩的故事和性格突出、生動可見的人物形象。

范穩
然而,《水乳大地》絕不靠所掌握史笈的稀罕和神秘而炫奇鬥豔,也不靠宗教生活的怪異場景取悅讀者,它包含著嚴肅的思考。不管作者的探索是否接近了真理的高度,僅就把紛亂如麻的頭緒梳理清楚已屬不易,要是能尋繹出有價值的思想線索就更難得了。儘管故事鋪展得很開,伸出的枝叉甚多,小說的章節忽而世紀初,忽而世紀末,忽而20世紀30年代,忽而70年代,顛來倒去,如旋動的車輻讓人眼花繚亂,但全書還是有一條主動脈的,那就是從衝突、動蕩走向和諧、交融。展開在我的眼前的這幅圖畫是,爭鬥不斷,災害不斷,人禍不斷,但同時愛的潛流不絕,不同民族之間的互助精神不絕,人類友愛和尋求融合的力量不絕,最終形成了百川歸海、萬溪合流的多種文化水乳交融的壯闊場景。這不是虛構的烏托邦而是現實。想象力飛騰,不斷出現魔幻與神奇的細節,不斷在現實與超現實之間切換,營造出一種特殊的神秘氛圍,是《水乳大地》在藝術上突出的特色。不必諱言,一開始傳教士用火槍和望遠鏡買通野貢土司的情節,會立刻讓人想起《百年孤獨》。

范穩
在後工業化到來的時代,帶有原始想象的神秘文化具有了非凡的特質。一方面是全球化的同質化;另一方面人們渴望異域文化提供異質性的神秘介質。西藏就這樣成為後工業化時代的文化聖地,在這樣的朝聖行動中,文學責無旁貸充當了領路人的角色。較早的有馬原和扎西達娃的西藏書寫,在八十年代中國文學向內轉及先鋒派崛起的潮流中起到開拓作用;隨後有阿來的藏地史詩敘事,阿來的一系列作品,無疑是西藏書寫的高峰;緊隨其後的范穩,一直以他獨特的漢人氣質介入這片神秘領地,他的《水乳大地》一出手,就令文壇驚異不已,那是大氣磅礴的作品,如長風出谷,春回大地。隨後的《悲憫大地》略顯緊張和險峻,生僻有餘而從容不足;這次的《大地雅歌》則可以看到范穩更為沉穩輕鬆的敘述,號稱“雅歌”,當然優雅飄逸,揮灑自如。這部作品顯示出范穩對藏地文化,對生存於這片土地上的人的命運有著新的認識,尤其是他的漢語小說意識有著更為生動的體現。
范穩寫作這部小說,有一個相當明確的主題,那就是他要用愛來解釋人的生命追求,這些為愛而生的人們是如何為自己的信仰而不惜一切代價,這片大地上的愛情之歌,卻也唱得悲愴凄迷。當然,小說的故事主線,就是央金瑪(後來皈依基督教改名叫瑪麗亞)的愛情,一個是流浪歌手扎西嘉措(後來皈依基督教改名史蒂文)因為愛她與她私奔,逃到一個極其偏遠的教堂小鎮;另一個是強盜格桑多吉(後來皈依基督教改名奧古斯丁)也對央金瑪一見鍾情,不顧一切放棄做強盜,甚至後來放棄作為土司繼承人的權利而住到教堂小鎮。但他們的愛情卻遭遇到藏地歷史大變動的改變,革命突然降臨,再也沒有什麼比二十世紀的革命對這個地區的歷史、對這代人的改變更為激烈。奧古斯丁轉向了革命,而史蒂文成了革命的對立面,奧古斯丁在關鍵時刻給史蒂文一條生路,為此丟了公安局長的官職,但他在教堂小鎮住下,與瑪麗亞生活在一起。愛情又超越了革命。多少年後,史蒂文在台灣,已經步入老年,大陸開放,他從台灣來到教堂小鎮,但物是人非,瑪麗亞與奧古斯丁生活在一起,結果借著過那個滑索道,奧古斯丁可能是有意掉進湍急的河流,以死來成全史蒂文和瑪麗亞……所有這一切,表明愛是自我拯救,已經替代宗教成為生命存在的最高信仰。
這部小說的獨特之處在於寫出了三種力量的碰撞交合:藏地的佛教的神性力量、基督教進入藏地的影響力、肉身之愛引發的自我拯救力量。這樣三種力量貫穿於“愛”的主題中,具體化於扎西嘉措(史蒂文)、央金瑪(瑪麗亞)與格桑多吉(奧古斯丁)的愛的關係中。范穩這部小說力圖對藏地文化進行去神秘化,也對佛教去神聖化,他想寫出藏地文化及佛教可親近的悲憫情懷,以及更具有人情味的那種經驗。當然,這與小說著力刻畫的頓珠活佛的形象有關。頓珠活佛並未把基督教進入西藏看成是多麼嚴重的入侵,雖然他也有異教的觀念,但他以虛懷若谷的姿態與基督教對話。杜伯爾神父被貢布喇嘛射殺身亡,頓珠活佛把那本血跡斑斑的《聖經》收藏了,以此作為他對這個宗教對手的懷念(參見該書第246頁)。他甚至承認:“我們供奉神職的靈魂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的。”頓珠活佛被基督教神父帶來的電影迷住了,他在銀幕上看到自己的形象,對西方現代科技文明驚嘆不已,在他的藏傳佛教世界里,不能理解這樣的事物,這引起他的極大的困擾。他一病不起,不是因為靈魂被洋人攝去了,而是他有著對外面世界的重新思考。但正當這兩種宗教要溝通時,仇殺與革命先後到來,這一切都以鮮血告終。這樣的活佛形象在當代中國文學中還極為少見,在這裡不要追究范穩這樣的活佛形象是否可能。范穩很可能可以舉出頓珠活佛相當可靠的原型。范穩正是要寫出更具有真實感的、與人性完全可以溝通起來的藏傳活佛的心靈世界以及他的現代命運。看上去頓珠活佛並非小說的主角,但這一形象身上卻注入了范穩對二十世紀東西方宗教的衝突與融合的深刻思考。這給小說真正的主題——大愛,提示了深厚的背景。男女之愛,最後還是向著“大愛”超越,它穿越藏地文化,穿越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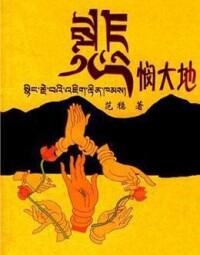
范穩
《悲憫大地》通過瀾滄江東西兩岸兩個家族的恩怨情仇為我們展現了藏族人的真正生存狀態。瀾滄江東岸住的是都吉家,世代以走馬幫為生,積累了不少銀子;西岸住的是朗薩家族,據說是吐蕃贊普們的後代,但他熱衷於不擇手段、強取豪奪,對東岸的富裕的都吉眼紅手熱。小說從上世紀初開始,以兩個家族為兩條主線,在老一輩的恩仇結束后,兩邊的少爺走向了不同的道路。洛桑丹增致力於成為藏教的上師,用一生追尋他的藏三寶——佛、法、僧,而達波多傑致力於成為藏族的英雄,用一生追尋他的藏三寶——槍、馬、刀!洛桑丹增在殺死仇人後用了7年的時間從家鄉一直磕等身長頭來到聖城拉薩學習佛法,在7年的時間裡他先後失去了他的兄弟、妻子、女兒。到達拉薩后,在修行的過程中,又失去了母親。最後他終於明白了佛法的悲憫。而達波多傑則用了10多年尋找西藏最好的寶刀、烈馬、快槍,來報殺父之仇。歷史的河流讓兩人在新中國即將成立時又一次碰頭。達波多傑帶領著一群貴族頭人們和共產黨對抗,戰爭即將開始,而洛桑丹增則用他的悲憫和自己的生命化解了這一場戰爭。這也讓達波多傑明白了英雄不是某種虛名,而是奉獻和犧牲,只有拯救人的心靈、救度苦難的眾生,才是真正的英雄!
作者以史詩的筆法表現了善與惡、人與自然、人性與神性等豐富的精神內涵,從而使悲憫的主題呈現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其中精彩的細節、奇異的物事,真實地再現了當地人神共處的生活場景,也為我們展現了一幅二十世紀前半葉藏區生活的風情畫。特別是穿插於書中的“田野調查筆記”和“讀書筆記”,更是以隨筆的語言,真實記錄了作者走訪西藏的歷程,給我們講述一個又一個神秘的傳說,讓我們結識一個又一個充滿神秘色彩的人物。對我們而言,所謂的“轉世”、“回陽”、“朝聖”,陌生而神秘,但是在作者的引導之下,我們對藏族的文化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
儘管書中的一些情節荒誕不經,比如狐狸變人、戰神在雲層間神出鬼沒、靈魂纏身等等,但是畢竟這是作者筆下的一個故事,一個傳說,或者說是一種想象,正是因為在特定的雪域佛土,這些故事的存在更有了合理性,也從另一個方面顯示出藏傳佛教的神秘悠久、博大精深。其實,作者想告訴讀者的還是藏族人精神世界里真正的“藏三寶”到底是什麼,他通過曲折生動的情節,鮮活感人的人物,深厚壯闊的歷史文化背景為我們詮釋出雪域佛土的人文畫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