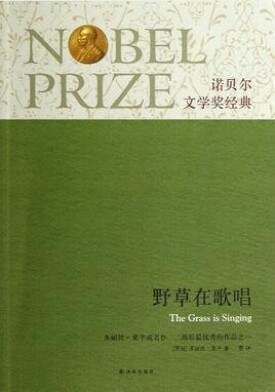野草在歌唱
1950年多麗絲·萊辛所著小說
《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是英國作家多麗絲·萊辛於1950年發表的作品。《野草在歌唱》以黑人男僕殺死家境拮据、心態失衡的白人女主人的案件為題材,側重心理刻畫,深刻表現了非洲殖民地的種族壓迫與種族矛盾。萊辛在小說中本能地渴望擺脫種族歧視,但又無法逾越那條鴻溝。因為無法逾越鴻溝,自南非白人政權自1956年起,萊辛就被禁止前往南非地區。一直到白人政權倒台以後的1995年,她才得以重訪南非,中間相隔的時間是40年。
《野草在歌唱》既表達了對於殖民者歧視、壓榨非洲黑人的憤恨和譴責;也表達了對殖民階級代表,受殖民者種族歧視思想毒害,自幼家境貧寒,命運多舛的白人婦女瑪麗,還從另一個角度表達了對受殖民者大肆掠奪,從而遭到嚴重破壞的非洲自然生態的憤恨。作者向讀者第一次真實地展現了白人移民在種族隔離制度下非洲大陸的生活狀況。1925年,萊辛跟隨父母搬到英國在非洲的殖民地南羅得西亞(現屬辛巴威)生活,並在那裡度過了大部分童年和青年時光。這部小說因深刻揭露了非洲殖民地的種族壓迫和種族矛盾而引起強烈反響,萊辛由此在文壇嶄露頭角。
瑪麗是南部非洲土生土長的白人,自幼家境貧困使她本能地渴望擺脫這種與土著黑人相似的生存狀況。瑪麗小時候,她的父親很厭倦自己的工作,並把這種不滿發泄到家裡。瑪麗的母親忍受著貧困和自己丈夫的雙重壓迫。瑪麗在缺少家庭溫暖的環境中長大,對性充滿了恐懼。她認為這是女人必須接受的懲罰。工作后,她的生活一度有所改善。但在迫於社會壓力結婚之後,她絕望地發現自己走回了母親的老路。她的丈夫迪克專心於農村的工作,對瑪麗十分冷漠。他們過著分居的生活。黑人僱工摩西的闖入打破了她麻木混沌的生活,使她有了新的生存力量。她被摩西所吸引並同他發生了關係。然而種族歧視的烙印深深地打在南部非洲每一個人的身上,註定了他們所面臨的必將是一個悲慘的結局。瑪麗和摩西的關係被人發現。瑪麗受社會壓力所迫,拋棄了摩西。摩西盛怒之下殺死了瑪麗,平靜報案等待被捕。全書共分為十一章。
《野草在歌唱》的創作以非洲殖民地的種族壓迫與種族矛盾為背景。 20世紀30年代處於英國殖民者統治之下的南非南部草原發生了一起悲劇:一位土生土長的白人婦女瑪麗被一名黑人男僕摩西殺害。作者圍繞悲劇事件展開了小說的創作。
瑪麗·特納
瑪麗的童年生活是在貧困中度過的,落後閉塞的鄉鎮和成天吵鬧的父母在她心中投下難以抹去的陰影,她從小就從大人那兒接受了仇視“黑種窮鬼”的教育,使她對男性和婚姻有一種本能的抗拒,她希望永遠過單身自由的日子。但是到了三十歲,人們的異樣目光和惡意議論使她感到惶恐不安,世俗偏見逼迫她終於意識到:必須找一個丈夫。遇到迪克后,她雖然不愛他,卻迫切地想立刻結婚,因為她心中隱隱約約地把期望寄托在迪克的農場上,認為那兒一定充滿了自然的氣息。
可是殘酷的現實在她渴求獨立遭受失敗后,又給了她沉重的一擊。迪克雖然本性善良卻固執無能,家中一貧如洗,慘淡經營的農場也年年虧損。瑪麗用盡了自己所有的積蓄來改善家中的布置,可是這既改變不了窮困的境況,也擺脫不了精神上的失落感;日復一日,瑪麗在破敗的房子里打發著沉悶空虛的日子。終於,在極度的痛苦中她決定逃離褊狹的農場回到城裡去,這是她向生活所做的唯一一次抗爭。可是她原先任職的公司拒絕了她,這個城市的其他地方也不接納已婚的女人,在人們眼中,她的社會身份已經從經濟獨立的白領女子轉變為寒傖可憐的鄉下女人。於是,她只能心灰意冷地跟隨尋她而來的迪克回到農場,回到與她母親的命運幾乎毫無差別的生活中。她在生活中第二次被挫敗了,這次打擊幾乎使她變得麻木,但是迪克卻在此時染上瘧疾,現狀迫使她必須面對面地和農場上的黑人僱工打交道。
她先前接受過中等教育,也受過民主平等思想的影響,甚至在初次聽到迪克稱黑人傭工為“老畜生”時,還憤憤不平地覺得他沒有教養;但是“黑人品性頑劣、不可信任”的種族歧視觀念早已牢牢地紮根於她的思想深處,這種觀念使她本能地對黑人充滿了敵意和戒心。當她手執皮鞭監視黑人幹活時,她心裡竟然感到十分踏實,當她揚起鞭子對準不馴服的摩西臉上抽下去時,雖然心中掠過一陣恐懼,但最終卻體驗到征服者的得意。在瑪麗身上發生的這種現象,在接受過英國文明教育的青年托尼身上也不難見到。先進的民主平等思想對於他們只是空泛的概念,根本不可能在現實中實踐,這是他們在殖民制度下的社會中的奴役地位所決定的,但這也鑄就了瑪麗的悲劇。因為一方面由於社會、歷史和現實生活的因素,她完全不能自主個人的命運,只是一個可憐的受命運擺布的弱者,但是在另一方面,她又是一個凌辱欺壓黑人的白人僱主。這種人格分裂的狀況,使她的內心體驗和道德判斷一直處於痛苦的矛盾中,每次對黑人濫施淫威后,她總是被更加歇斯底里的絕望所吞沒。與此同時,迪克的精神也日益頹唐,在瑪麗的眼中,他不過是一具沒有靈魂的軀體。窮困潦倒的生活似乎已經走到了盡頭;然而生存的本能使她乞求一種外來的變更,她想生一個孩子陪伴自己,可這一回是迪克冷酷地用貧困的理由否定了她做母親的權利。
生命的支撐點眼看就要傾倒,作為一個女人,儘管她身上帶有鮮明的種族歧視的烙印,可在她潛意識裡,還是渴望著安慰、愛撫和力量。因此,當她忍不住當著摩西的面痛哭失聲后,竟不由自主地接受了這個黑人對她表示的善意安慰。以後,她又被摩西強健的體格和沉靜果斷的舉止所吸引,而摩西似乎也細心地體察到她的苦悶心境,總是在生活上儘力照顧她。在他們倆關係微妙變化的過程中,瑪麗已經在內心對迪克和摩西進行了選擇,儘管她自己並未清醒地意識到這種選擇及其後果。她的思想成天跟隨著摩西的蹤影,可同時她又對自己的感情覺得恐懼,恐懼中還夾雜著對摩西作為黑人的憎恨。排斥與渴望的力量在她內心劇烈地衝突著,這種衝突實際上是還未完全泯滅的良知與被扭曲的人性之間的抗爭。瑪麗最終和摩西發生了曖昧的關係,這種關係在當時的南部非洲是諱莫如深的,萊辛不僅大膽地觸及了這個敏感的問題,而且尖銳地指出了這種關係在本質上無法逃脫階級屬性的事實。一方面,瑪麗在肉體上和某種感情寄託上需要摩西,但另一方面,她決沒有忘記他們之間的種族差別和雇傭關係,依舊時常以女主人的身份對摩西吆三喝四。這種不正常的關係是無法長久維持的,瑪麗和摩西的心中都隱約地感覺到有一個可怕的結果在等待著他們。果然,他們沒有逃過種族歧視社會的道德監視。英國來的青年托尼發現了他們的秘密,震驚之下,他覺得瑪麗簡直是跟野獸發生了關係,雖然他以前對白人統治階級的某些偽善行為很反感,並且一直為自己具有平等的先進思想而驕傲,但他此刻卻憤怒地感到白人的尊嚴受到了玷污,於是他立即以白人衛道士的面目嚴厲呵斥摩西滾開。托尼強烈的種族歧視態度似乎喚醒了瑪麗的白種人意識,她馬上站到了托尼的立場上,冷酷無情地叫摩西快滾。事後她又痛悔地哭泣,這種矛盾的兩面性註定了她的悲劇結局。在她終於認識到那個英國青年無法從精神上拯救自己的同時,她也看透了自己;在生命的最後一個黎明,她無限留戀地沉浸在大自然的美妙變幻中,她能感受到無數小動物的生命搏動,可她知道自己面臨的只有毀滅。社會制度無疑是造成瑪麗悲劇的主要根源,但是她本人的弱點也是不可否認的因素。瑪麗在精神上始終被動地接受環境和命運的擺布,她從未真正理解過自由的本質含義,狹隘的種族意識又妨礙了她對社會與自身的關係做深刻的思考,這一切加速了她走向悲劇的進程。
迪克·特納、查理·斯來特
特納夫婦被當地人稱為“窮苦白人”,當地人討厭特納夫婦是因為他們“落落寡合”。
理查曾經在倫敦一家雜貨鋪當過夥計。他在非洲生活了二十年。理查到非洲的唯一目的是賺錢,經營著農場。他是一個粗魯蠻橫、心腸鐵硬的人。
萊辛在小說中不僅描寫了白人與黑人之間的奴役與被奴役的關係,而且毫不留情地揭示了在南非殖民制度統治下,生活在兩種截然不同的經濟境況下的白人移民之間,同樣存在著掠奪與被掠奪的關係。迪克和查理就是這兩類人的代表。像無數貧窮的白人移民一樣,迪克滿懷美好的願望,期冀在南部非洲創立家業。他老實善良,一心一意地在農場上埋頭苦幹,可是由於缺乏精明的經營管理和盲目施行不切實際的計劃,結果土地只能被查理那種善於巧取豪奪的暴發戶所侵吞。貧富白人移民之間的爭奪兼并是當時南部非洲的一個殘酷現實,萊辛筆鋒犀利地揭掉了蒙在白種人關係上的虛偽面紗。查理在強行買下他稱之為“同種族兄弟”的土地時,竟然還非常動情地說這是“為了使白人兄弟不致敗落到過於悲慘的境地,否則黑鬼們就要自認為和白人沒有區別了”。當他看著迪克痛苦地抓起一把泥土不忍放棄農場時,他心中甚至懷疑自己對迪克是否太拖泥帶水,違背了自己一貫恪守的生意原則。善良懦弱的迪克被查理的“善行”推到了絕境,而查理及其白人掠奪者們在必要的場合下,依舊不忘表現出“維護白人團結”的面目。
摩西
摩西是一位土著人,之前住在辛巴威北部地區的馬紹納蘭,他的來歷很難說得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萊辛在小說中以充滿人道的理解和同情,把黑人視作和白人一樣具有愛憎感情的人來描寫。摩西的形象在小說中沒有被簡單地面具化,雖然萊辛沒有像描寫瑪麗那樣描寫他的心理活動,但是他的言語舉止從不同的側面比較完整地描繪了一個具有個性的黑人。摩西和瑪麗的第一次相遇發生在彼此身份完全對立的場合下,他是出賣勞力的僱工,瑪麗則是心腸冷酷的僱主。當摩西無端被瑪麗狠抽了一鞭子后,仇恨和輕蔑的目光幾乎使瑪麗嚇破膽。但是後來當他到迪克家幫傭,目睹瑪麗在貧困和絕望中度日時,他以寬厚的態度諒解了瑪麗平日對他的苛刻,答應她繼續留下來幫工。在他感覺到瑪麗對他的態度逐漸和緩后,他盡己所能地照料她的生活,甚至從山上采了野花笨拙地插在一起送給瑪麗,希望給她一些安慰。這個小小的細節使人看到一個普通黑人的內心也同樣具有美好細膩的感情。從他和瑪麗不斷發展的關係來看,應該說是他的質樸和寬厚首先觸動了瑪麗內心那點還殘留著的良知。摩西對自己所處的生存環境也沒有顯出渾渾噩噩俯首認命的奴性。他曾問瑪麗:“難道耶穌認為人類互相殘殺是正當的嗎?”這樣尖銳的問題使瑪麗聽了無言以對。除了純樸寬厚的一面,摩西的個性中還有血氣方剛的另一面,當他看見瑪麗殘忍地站在那個沒有心肝的白人一邊,態度堅定地叫他滾開時,屈辱和憤怒在他心中燃起了復仇的火焰,使他舉刀殺死了瑪麗。可是放下刀后,他卻站在雨中等待著人們來追捕他,這一舉止使人感受到他內心經歷著複雜的感情波動。由此看到了一個真實可信、具有個性特徵的黑人形象。
《野草在歌唱》表現的主題:婦女的生存環境及其社會地位、種族歧視制度和文化歷史背景對於個人生活的影響。書中通過對女主人公瑪麗具有典型意義的悲劇命運的描寫,深刻揭示了殖民統治制度下不同種族、不同階層人與人之間的本質關係,剖析了造成瑪麗悲慘結局的社會根源。
《野草在歌唱》觸及了萊辛創作中一再表現的主題:婦女的生存環境及其社會地位以及種族歧視制度和文化歷史背景對於個人生活的影響。瑪麗一生的悲劇不僅在於她無法擺脫種族歧視和殖民者的心態,更在於婦女深陷無法獨立、無法自主的困境:瑪麗原本憑藉自己的努力在城裡獲得經濟獨立和一定的自由,但迫於“世俗偏見”的壓力嫁給她並不愛的迪克后,婚姻痛苦,她一度從農場逃回城市,但當時的社會並不能為已婚女人在家庭之外提供立足之地,因此,她只能再次回到農場,麻木地繼續無希望的生活。譯者對瑪麗充滿同情,指出“作為一個女人,儘管她身上帶有鮮明的種族歧視的烙印,可在潛意識裡,她還是渴望著安慰、愛撫和力量,因此她發展了和摩西的曖昧關係。瑪麗被看作種族主義的受害者,認為她“受過民主平等思想的影響”,內心也曾有過對黑人的同情,但無奈種族歧視的種子在她心裡根深蒂固,這最終導致了她的死亡。譯者還將瑪麗與萊辛作品中一以貫之的“自由女性”主題聯繫起來,指出瑪麗“在精神上始終被動地接受環境和命運的擺布,她從未真正理解過自由的本質含義”,這也是造成瑪麗悲劇的“不可否認的因素”。總之,譯者雖並未從女性主義角度解讀小說,但指出了婦女的生存環境這一作品主題,深刻地認識了瑪麗在種族歧視思想和傳統婦女觀念中所面臨的困境。
象徵與暗示
1、野草象徵著摩西為主要代表的南非黑奴
作為殖民統治的犧牲品,以摩西為代表的南非黑奴像荒原中的野草一樣,“烈日噴炎曬不死,嚴寒冰雪鬱鬱蔥蔥。”在殖民者的任意宰割、壓榨和摧殘之下,不屈不撓,奮力反抗、吶喊。黑奴摩西第一次出現在讀者面前是在小說的第七章,瑪麗的丈夫迪克由於虐疾的突然襲擊等原因,迪克病倒了。為了生計瑪麗不得不代替丈夫下地監督黑奴們幹活。小說中有一段震撼人心的場面發生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南非土著人受白人虐待的真實寫照,這樣的血腥場面在南部非洲的殖民地土地上屢見不鮮,摩西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例子。五十年代的非洲處於西方殖民者的統治下,種族歧視在非洲這塊廣袤的土地上橫行肆虐著,土著黑人生活在社會的邊緣,他們的處境也非常悲慘。黑人被殖民統治者視為骯髒的、懶惰的、野蠻的、暴力的劣等民族。就像小說主人公瑪麗一樣,會因為黑人“臭”便罵他們“不要臉”;在這塊殖民地上,白人可以隨意像牲口一樣隨意買賣,沒有自己的話語權,也沒有做人的基本權利和尊嚴。禁止黑人在白人的飯館吃飯,不容許黑人和白人同乘一輛公交車。然而,“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當他被女主人瑪麗鞭打時,“摩西舉起粗壯的大手擦去臉頰流淌的鮮血,他的眼睛里有一種陰沉和憎恨的神情,而使她難堪的是那種帶有譏嘲的輕蔑的神色。”他用簡單而有力的反抗方式讓瑪麗丟掉了盛氣凌人的武器,不得不把他當作一個人來對待。也正如小說結尾所講的那樣,在女主人一而再再而三侮辱、壓迫和摧殘之下,摩西再也沒有忍下去,反而拿起鋼刀結束了瑪麗的生命,達到了復仇的目的。由此,看到題目與內容先悖后的疑惑得到了解釋:黑人摩西正是一株“歌唱的野草”。摩西殺害了瑪麗,按照常理他是一個殺人惡魔,然而在萊辛的字裡行間根本找不到任何對摩西的譴責,更多的是對他的讚揚和肯定。萊辛正是通過塑造摩西這一形象來填補標題留給讀者的空白。
2、野草象徵和暗示著荒蕪的非洲自然
小說中萊辛多處揭示了殖民者推行的工業化給非洲這塊美麗的土地所帶來的惡果。在這個“被金融巨子和開礦大王——首創建起來的南部非洲。”英國殖民者為了謀取更大的利益,肆意擴張和掠奪非洲南部的土地資源,根本不顧生態環境的保護,開墾土地,濫採礦石,分割土地,耕種作物。為了牟取暴利,竟然違背自然規律一味地在土地上種植“邪惡的農作物”——煙草。使得許許多多的良田變成了貧瘠的荒原。正如作者所描述的萊斯特農場一樣,“萊斯特先生的農場上簡直沒有什麼樹,這足以證明他耕作無方;農場上犁出了一條條大溝,許多畝烏黑肥沃的好地都因為濫用而變得貧瘠。然而他畢竟賺到了錢,這才是最重要的。”“他們一年一年地榨取這些土地,卻從來沒有考慮過施肥,......即便是像他那樣的肥沃農場,也不是取之不竭,用之不盡;”最後“他不再每年賺成百上千的錢了,土地荒蕪了。”
3、瑪麗的象徵與暗示
瑪麗這個名字在英文中意味著生活艱難辛苦,反應遲鈍,同時也暗示了她一生註定要受窮受苦,落寞孤獨之苦。她的名字與耶穌基督的母親聖母瑪利亞同名,暗示著她原本有著像聖母瑪麗亞一樣生養子女,撫育子女的偉大天性。比如在第八章中,當瑪麗意識到她和丈夫迪克的生活沒有生氣、希望渺茫時,要求她的丈夫與她生一個孩子,以此來慰籍空虛的精神世界。然而迪克以生活拮据無力撫養孩子為由拒絕了她的要求。從作品評析及其它而不但生不出拯救人類的救世主,就連一個普通女人最基本的做母親的權利都被剝奪了。萊辛用含而不露的象徵手法,儘可能地挖掘了作品的深度。在作者看來,小說的女主角瑪麗是一個既值得同情又值得憎恨的女性。同情的是,她生活在種族隔離制度下的南非,雖然是白人,從小卻家境貧寒、父母不和,早就了瑪麗厭惡男人和婚姻的畸形性格。她逃避家庭,在城裡過著獨立而閑散的單身生活,本想繼續這種自在的生活,卻迫於社會輿論和世俗偏見,選擇了婚姻。在她嫁給貧窮而懦弱的農場主迪克之後,發現他們的婚姻是失敗的。這場婚姻一步步把她帶入深淵,直至毀滅。從這個意義上講,她既是一個父權和夫權思想下的受害者,又是種族隔離社會下的犧牲品;憎恨的是,她愚昧而教條式地奉行種族主義,欺壓黑人,從這個意義來講,她的死是咎由自取的,不值得惋惜。
4、摩西的象徵與暗示
“摩西是《聖經》里一個神聖的形象,他是一位先知,是以色列人的拯救者。摩西這個人物形象就是以聖經中的摩西為原型來塑造的。”小說中的摩西是主人公瑪麗的僕人,這個名字象徵著瑪麗心靈拯救者和反抗種族歧視的黑人領袖。在小說中摩西被塑造成一個誠實、善良、勇敢的,有著獨特個性和人格魅力的黑人。讀者無法從小說中了解到他的身世,只知道他是千千萬萬個在殖民統治下“一個連狗不如的黑奴”之一,任人欺凌、任人宰割的生存境地。但是,摩西卻完全不同於其他被“愚化”的黑奴,“他倔強自立、勇敢善良、敢愛敢恨”,當女主人瑪麗舉起鞭子無緣無故地抽打他的臉時,他有力地舉起粗壯的手憤然擦去眼角的血跡,不但沒有害怕退縮,反而用一種陰沉、憎恨、譏諷和輕藐的神情注視著瑪麗,他用這樣一種無聲的方式進行了反抗,使得瑪麗感到難堪,心驚膽顫,使得瑪麗乖乖地低下了那顆高傲的頭。正如一些評論家所說的:“瑪麗是白人殖民主義種族歧視政策最大的犧牲品和受害者,他在殖民地成長的過程也是她的人性逐漸被扭曲而最終走向毀滅的。”瑪麗的丈夫迪克是一個懦弱、固執,背運的也不懂生活情調的人,她的生活單調,本身還有一種清高卻又自卑的性格,不願與鄰居和外人交流,和丈夫沒有性生活。他就是生活在這樣一個枯燥無味,精神處於快要崩潰的邊緣。而摩西的出現,無形中給瑪麗的生活帶來了一抹綠色和希望,也滿足了她心理的需求。摩西的忍耐、還有對女主人的無微不至的關懷使她第一次感受到了男人的關懷。雖然在她的內心中對這個黑人有了好感和愛的情愫,但是由於她像其它種族歧視者一樣對黑人有著根深蒂固的憎恨,不敢大膽地接受這個黑人。終於,在白人青年托尼發現了他們之間的不正當的關係后,瑪麗以一種高高在上的姿態呵斥責罵摩西。不堪忍受屈辱的摩西終於忍無可忍了,以一種極端的方式結束了瑪麗的生命。”瑪麗的被殺結束了她短暫的人生也同時使她從內心的痛苦中得到了解脫。”,“在她異常痛苦之時,黑奴摩西在某種程度上扮演著類似拯救者的角色。”
5、房子的象徵和暗示
瑪麗和迪克居住的那個蓋了鐵皮屋頂的房子像一個牢籠,不但囚禁住了她的肉體,而且禁錮住了她的靈魂,讓她的希望之火在這裡逐漸息滅。自瑪麗住進鐵皮房子的那天起,她就被封閉起來了,與外界失去了聯繫。“四方形的小屋孤零零地建在荒僻的大草原上,附近沒有人家,從外面看上去,房子是緊閉的、漆黑的、窒息的,到處透著一種陰冷的氣息......裡面又小又低,散發著霉臭味,家徒四壁。”好像到了另一個世界。那寒酸的房子就是對未來要過的窘迫生活的預兆。到了夏天,這個蓋了鐵皮屋頂的房子“熱得使人要發瘋”。在這個完全與世隔絕開來的陋室里,她度過了她的餘生,在這裡她始終感受的是窒息和腐敗,不在沉淪中吶喊,就在沉淪中死亡。
6、天花板的象徵和暗示
從瑪麗住進鐵皮房的那天起,她就發現房子沒有天花板,她曾多次要求丈夫迪克把天花板裝上,但都由於生活拮据,裝不起天花板等理由未能實現瑪麗的這個夢想。天花板就像他對迪克的期望,隨著一次次地提出希望,又一次次的失望,她對她眼前的這個男人也不抱任何的期望了。她處於一種心灰意懶、破罐子破摔的絕望狀態中。萊辛通過這樣一個意象,不僅深刻地反映了瑪麗一家的生活艱辛的處境,而且還暗示了瑪麗希望改善生活,改變命運的希望註定要破滅的。這樣的寫作技巧可謂是獨具匠心。
萊辛一向注重個人對生活的心理體驗,並以心理活動描寫見長,這一特點在《野草在歌唱》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現。瑪麗在生活變動和感情經歷中的每一絲心理變化都被細緻入微地記錄下來,讀者在跟隨女主角內心體驗的過程中,逐漸加深了對醜惡的殖民制度的認識。貫穿在她所有作品中最鮮明的特點是她對人類命運的深切關注和嚴肅思考。萊辛成為格勞麗亞·斯坦因(GloriaStienm)和傑曼·格理爾(GermaineGreer)等激進人物所擁護的女權主義的先鋒。
——李志成
《野草在歌唱》中的野草常常被解讀為種族主義壓迫下的黑人。然而,作為白人女性,瑪麗在種族主義和父權文化的物理空間下,不斷體會到物理空間與自身心理空間之間發生的矛盾,徘徊在兩者邊緣無法取捨,始終無法構建起自己的身份,從而導致了最終自己走向毀滅。
——張飛瓏

多麗絲·萊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