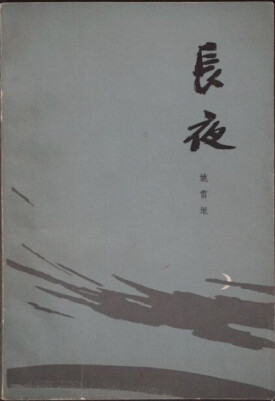共找到8條詞條名為長夜的結果 展開
長夜
姚雪垠著長篇小說
《長夜》以20年代軍閥混戰時豫西山區農村為背景,描寫了李水沫這支土匪隊伍的傳奇式的生活,塑造了一些有血有肉的“強人”形象,真實有力地揭示出許多農民在破產和飢餓的絕境中淪為盜賊的社會根源,同時也表現了他們身上蘊藏著反抗惡勢力的巨大潛在力量。像《長夜》這樣以寫實主義筆法真實描寫綠林人物和綠林生活的長篇小說,是“五四”以後的新文學中絕無僅有的,此書譯為法文後,姚雪垠被授予馬賽紀念勳章。
姚雪垠1924年小學畢業后,去信陽上中學。同年冬,由於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學校提前放假。回鄉途中,與二哥和其他兩名學生一起被李水沫的土匪隊伍作為“肉票”抓去,旋又被一個土匪小頭目認為義子。在土匪中生活約100天的這段特殊經歷,成為他後來創作自傳性小說《長夜》的基本素材。
《長夜》是姚雪垠寫於抗戰時期的一部別開生面的作品,一九四七年由上海懷正文化社出版。小說講述了作者在一九二四年冬天到次年春天大約一百天的時間在土匪中生活的經歷,是“一部帶有自傳性質的小說”。而且,“在寫作的時候,為忠實於現實主義,我決定不將主人公陶菊生的覺悟水平故意拔高,也不將貧僱農出身的‘綠林豪傑’們的覺悟水平和行為準則拔高。”“忠實的反映二十年代河南農村生活的重要側面和生活在那樣條件下的人物的精神面貌,是我要寫這部小說的中心目的。小說中當然反映了我的世界觀和我的思想感情,但是我決不背離歷史生活的真實,故意加進去某些思想宣傳。”豫西是有名的土匪世界,作者的親身經歷和追求寫實的創作態度,使《長夜》為現代讀者提供了一睹“真實”的土匪故事的機會。
《長夜》的真實感主要源於複雜的人物關係和人物形象的寫實性描寫。“在這部小說中,我寫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農民因沒有生活出路而叛亂。我寫出他們的痛苦、希望和仇恨;他們‘下水’(當土匪)后如何同地主階級存在著又拉攏又矛盾的關係,其中一部分人如何不得不被地主中的土豪利用;我寫出來杆子與地方小軍閥之間的複雜關係;我還寫出來杆子內部存在著等級差別:有人槍多,放出一部分槍支給別人背,坐地分贓;有人背別人的槍;有人當‘甩手子’,地位很低。小說中所反映的社會現象,人與人的關係,階級關係,正是我在少年時代曾經生活於其中的歷史現實。”“一支人數較多的土匪武裝,其階級成分是複雜的:有真正的失業農民,有農村中的二流子,有離開軍隊的兵油子,有破落地主家庭出身的人;還有曾經受過招安成了官軍,因打敗仗或不得意而重新下水的軍官。”正是這種“人與人的關係”、“階級關係”和土匪內部階級成分的複雜性,為讀者帶來了五、六十年代階級理論圖解式的作品所缺失的“真實感”。複雜的人物關係描寫是建立在複雜的人性、性格刻畫的基礎上的,土匪頭目李水沫、薛正禮和土匪趙獅子、劉老義都是令人難忘的“強人”形象。趙獅子在與地主武裝紅槍會、地方軍閥馬文德的交戰中彪悍勇猛;對待“肉票”和反抗的農民則透著兇殘,尤其是攻打胡劉庄時將其大舅、二舅槍殺的細節更是令讀者觸目難忘;而面對土匪頭目薛正禮的母親、妻子,他在親熱和調皮中流露出對家庭溫暖的渴求。強悍、兇殘、講義氣、重感情如此複雜矛盾的個性合於一體,顯示了作者對特殊家庭(趙五歲即淪為孤兒,他母親被其舅逼迫下自盡)、社會(兵荒馬亂,強人盛行)環境下形成的性格特點的精確把握。薛正禮則沉穩精明、強悍機警、善良義氣。他勸同村青年不要做土匪而自己又不得不為,他眼見土匪燒殺姦淫勸阻不成而又任其所為,他是一個集農民的善良、寬厚和土匪頭目的精明、強悍於一體的複雜人物。
值得注意的還有這部小說的敘事視角。作者自陳“因為這是一部帶有自傳性質的小說,所以我在進行寫作時,不追求驚險離奇的故事情節,不追求浪漫主義的誇張筆墨,而力求寫出我少年時代一段生活的本來面貌”第一人稱全知視角為自傳最常用的敘事方式,而且也更有利於還原“生活的本來面貌”。對讀者而言,由“我”來講述“我”的故事和“我”所目睹的土匪故事更具可信度和真實感。但作者寫作《長夜》時打算把它作為“三部曲”的第二部來構思,定名為《黃昏》《長夜》《黎明》的“三部曲”是旨在反映河南農村從清末至北伐近三十年歷史變遷的史詩,由“我”來講述顯然難負其重。“由於《長夜》帶有自傳性質,最容易寫,所以我先從《長夜》動筆。但是缺點也在自傳性質上,局限了我,不曾寫出來那個時代的較為廣闊的社會生活。”這種要反映“廣闊的社會生活”的寫“史詩”的雄心逼著姚雪垠選擇第三人稱視角,而對“真實感”的追求又要求他運用第三人稱時不能時時處處“全知全能”,二者相互妥協的結果是第三人稱眼知視角,這樣既可保留真實感又擴大了社會生活描寫的廣闊度。“一九二四年的冬天,從伏牛山到桐柏山的廣大地區,無數的田地已經荒蕪。”“半個月以前,吳佩孚正指揮直系軍對在山海關和九門口一帶同奉軍鏖戰,不提防馮玉祥從察哈爾回師進入北京,拘留了大總統曹錕,斷了吳佩孚後路。”——當需要將廣闊的自然風貌和歷史背景告訴讀者時,敘述人幾乎無所不知;而當進入具體的故事層面時,敘述人經常會不自覺轉入主人公陶菊生的個人視角——“小說的主人公就是我自己”。這種敘事角度事實上是由兩個“我”共同承擔:一個是現在(寫作《長夜》時)的“我”負責為讀者交代故事的發展和背景,一個是過去的“我”(陶菊生)講述不同境況下的見聞和感觸,兩個“我”不斷交替換位,共同完成兩個一直難於完全和諧的任務:自傳和史詩。而陶菊生是一個年僅十四歲的少年,讀過書,“思想進步”,但也不乏家鄉的“強人”思想,“把冒險當作遊戲和英雄事業”,而且又身兼土匪的“肉票”和土匪頭目義子的雙重身份。“肉票”和“進步”讀書人的身份使他感到土匪殺人放火的恐怖、殘忍,“強人”思想和義子身份讓他看到土匪的勇敢、講義氣甚至人性的美好。由這兩個“我”共同講述的土匪故事,帶給讀者的閱讀體驗是愛恨交織的複雜體驗。
姚雪垠(1910年10月10日~1999年4月29日)原名姚冠三,河南鄧縣人。1935年起,陸續在北平《晨報》、天津《大公報》發表短篇小說。1957年在逆境中開始創作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歷時30餘年,約230萬字,分為5卷。1981年12月,在古稀之年加入中國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