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商制度
行商制度
清政府的商業政策,不僅對國內商業加以干預,以達到壟斷和統制的目的,而且還操縱對外貿易。鴉片戰爭前,雖然上海、寧波、廈門等口岸,曾經有過時間短暫的對外貿易活動(康熙二十四年至乾隆二十二年,共七十四年),但整個清代前期的對外貿易活動卻主要集中在廣州,尤其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後,廣州成為“唯一”的對外貿易口岸,所有海上對外貿易全部集中在廣州進行。因此,在廣州的對外貿易活動集中地反映了清政府對外貿易政策和制度的主要內容。所以,在研究清政府干預對外貿易這一問題時,以廣州的行商制度(又稱“洋行制度” )作為主要的考察對象。清代行商制度是清政府利用特許的壟斷商人集團工具,來干預、控制和壟斷對外貿易的一項商業經濟制度。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行商制度具有特殊的壟斷性質。本文將對這一問題加以考察。

行商制度
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正式宣布開海貿易以來,開始了對海外貿易活動的干預。為了管理沿海貿易、對外貿易和徵收關稅的便利,清政府於康熙二十四年在江南、浙江、福建和廣東四省分別設立了江海關、浙海關、閩海關和粵海關。粵海關設立於具有悠久對外貿易歷史傳統的廣州。由於粵海關的設立,廣州的對外貿易就開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為了適應對外貿易的新形勢,清政府就著手創立新的制度。這種新的制度,就是廣州的行商制度。
關於廣東行商制度創建的年代,過去史學界頗多爭議,自從彭澤益先生《清代廣東洋行制度的起源》一文發表以後,才解決了這個懸而未決的歷史疑案。文章以信實的史料為確鑿的根據,考證出廣東洋行創設的時間為清代康熙二十五年(1686)四月。文章指出:“清代廣東洋貨行和洋行制度的產生是緊接著粵海關開關第二年的春夏之間,即從康熙二十五年四月間開始的。”同時,又進一步考證出“廣東洋貨行又叫十三行,其命名的由來不是因洋行數目而定”。由於行商制度產生的時間已有定論,在此毋庸贅述。
廣州行商制度在康熙二十五年四月創建時,洋行的主要職能只是評定進出口貨物的價格及承攬進出口貨物的關稅。史籍記載說:“自康熙二十四年開南洋之禁,番舶來粵者,歲以二十餘舵為率,至則勞以牛酒,牙行主之,所謂十三行也。”這說明當時的洋行所執行的職能與牙行大致相似,它們是對外貿易中的牙行。初始階段的行商制度也類似於傳統的牙行制度。以後,隨著對外貿易的發展,行商制度才在實踐過程中不斷完善起來,成為清政府壟斷、統制對外貿易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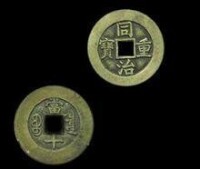
行商制度
四十年以後,“乾隆二十五年(1760),行商潘振成等九家呈請設立公行,專辦夷船,批司議准。嗣後外洋行不兼辦本港之事”。與此同時,再“別設本港行,專管暹羅貢使及貿易納餉之事,又改海南行為福潮行,輸報本省潮州及福建民人諸貨稅。是為外洋行與本港、福潮分辦之始”。外洋、本港、福潮諸行分辦業務,是沿海貿易和對外貿易發展的結果。據《廣東通志》的記載:“國朝設關之初,船隻無多,稅餉亦少,有行口數家,不分外洋、本港、福潮,聽其自行投牙。迨后船隻漸多,各行口有資本稍厚者,即辦外洋貨稅,其次者辦本港船隻貨稅,又次者辦福潮船隻貨稅,並無官立案據。”諸行分辦業務,也是行商之間競爭的產物。在競爭過程中,必然會出現資本集中的現象。這樣,擁有雄厚資本的行商就對獲取蠅頭小利的本港、福潮行的業務不屑一顧,而資本短缺的行商也無力經營外洋行的業務。於是就自然而然地引起了行商經營業務的分工。但是,這種分工的出現,就使外洋行的行商壟斷了對西歐各國貿易的經營業務。所以,在外洋、本港、福潮諸行分辦業務的基礎上而成立的“公行”,是當時經營對西歐各國外貿業務的行商的壟斷組織。

行商制度
就在成立“公行”的過程中,行商經營的業務活動範圍也在不斷擴張。他們除了評估進出口貨物的價格和承攬進出口貨稅之外,還代外商收購絲茶,以供出口;對外商的進口貨物“代為運往各省發賣”的同時,他們還要充當外國商人的“保商”。據美國商人亨特記載:“洋船或其代理商如違犯通商章程,均由行商負責。官方認為行商能夠並應當管理駐廣州商館的洋人與泊在黃埔的船隻。行商有‘保證’他們守法的責任。因此,和每隻洋船一樣,每一外僑自登岸之時起,必須有其‘保護人’,於是行商便成為‘保商’了。我們的保商是(伍)浩官,當然他還擔保了別人。由於這種關係,我們戲稱他為我們的‘教父’。”
同時,在行商中還出現了“總商”。 “總商”是行商的首領,由資本雄厚,居心 公正的行商擔任。嘉慶十八年(1813),正式批准“總商”的設置,“著照該監督所請,准於各洋商中身家殷實、居心誠篤者,選派一二人,令其總辦洋商事務,率領眾商,公平整頓。其所選總商,先行報部存案”。至此,行商制度已趨於完善,堪稱嚴密。在這一制度下行商成為清政府統制對外貿易的工具。他們操壟斷經營對外貿易的權力,經營進出口貨物的貿易,同時又代表清政府與外商交涉,對外商進行嚴格的管制,成為亦官亦商的特權商人。
在中國傳統社會裡,對外貿易一直由專制國家所壟斷。清代行商制
度同樣體現著專制國 家壟斷對外貿易的這一歷史傳統。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專制統治階級統治經驗的更加成熟,專制國家壟斷對外貿易的具體形式卻發生了變化。專制國家壟斷對外貿易的具體形式的變化集中反映在對外貿易壟斷所有權與壟斷經營權的分離過程中。行商制度的產生,是這種分離過程的產物。
清代行商制度產生於康熙二十五年(1686)四月。清政府為了建立行商制度,首先必須要招商(包括牙行)來承充行商。招商過程的具體內容,就是專制國家把對外貿易的壟斷經營權賦予其所招來的行商。因此,招商的過程也就是對外貿易的壟斷所有權與壟斷經營權分離的過程。康熙二十五年四月,廣州行商制度產生之時,為了保證當時對外貿易的順利展開和海關徵收關稅的便利,清政府第一次進行了招商。當時,廣東巡撫李士禎在《分別住行貨稅文告》中指出:“今設立海關,徵收出洋行稅,地勢相連。如行住二稅不分,恐有重複影射之弊。今公議設立金絲行、洋貨行兩項貨店,如來廣省本地興販,一切落地貨物,分為住稅報單,皆投金絲行,赴稅課司納稅;其外洋販來貨物,及出海貿易貨物,分為行稅報單,皆投洋貨行,候出海時,洋商自赴關部納稅……為此示仰省城佛山商民行人等知悉:嗣後如有身家殷實之人,願充洋貨行者,或呈明地方官承充,或改換招牌,各具呈認明給帖,即有一人願充二行者,亦必分別二店,各立招牌,不許混亂一處,影射朦混,商課俱有違礙。此系商行兩便之事,各速認行招商,毋處觀望遲延,有誤生理。”這個“文告”是研究行商制度起源的重要歷史資料,它反映了當時行商制度產生之時,清政府第一次招商的歷史情況。從“文告”中可以看出,是先有海關的設立,然後才有洋貨行的設立。當時清政府督促建立洋貨行,主要是為了海關“徵收出洋行稅”的方便。洋貨行是專制國家運用行政命令強制建立起來的。為了建立洋貨行必須招商承充。當時招商的條件並不苛刻,手續也較為簡便,只要是“身家殷實”,“願充洋貨行的”“商民行人”,“或呈明地方官承充”,“或改換招牌,各具呈認明給帖”就行了。“文告”發布的日期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四月,距離“夏末秋初”,“外洋各國夷船到廣貿易”(15)僅有二三個月的時間,所以招商之事十分倉促,這從“文告”“各速認行招商。毋得觀望遲延,有誤生理”的話中可以反映出來。“文告”沒有提及“商民行人”承充行商,向政府領取行帖,是否需要繳納款項的問題。但是,當時的行商,只不過是在對外貿易活動中充當牙行的角式而已。根據清政府的慣例,承充牙行是需要繳納牙帖費,才能領到牙帖的。“凡官牙定之以額,擇其人輸稅領帖以充牙行。”康熙年間承充行商,領取行帖而繳納的款項基本上與牙帖費相差無幾。因為當時的行商權力有限,僅僅是評估進出口貨物的價格。“文告”中說:“其各處商人來廣,務各照貨投行,不得重複納稅,自失生計。倘被奸牙重收,該商即赴本院(巡撫衙門)喊稟追究。或此後行情有遲速,行價有貴賤,俱聽各商從便,移行貿易。”可見,當時的行商主要擔任牙行的職能,幫助海關徵收關稅。商人有自由選擇行商的權利,這說明行商在對外貿易中的壟斷經營權力還尚未完全形成。所以當時願承充行商者人數並不很多。康熙二十六年(1687)四月間,廣東巡撫李士禎和兩廣總督吳興祚在會奏中說,“今貨物壅滯,商人稀少”就是一個例子。

行商制度
綜上所述,可見清政府招商的過程,是對外貿易壟斷經營權力與貨幣權力的一種 交換過程,這種交換還有其它附加條件(諸如“自家殷實”、“公平誠信”等等之類)。在這裡,作為壟斷所有者的清政府“出售”的是對外貿易的壟斷經營權。隨著這種壟斷經營權力的膨脹,它的“出售價格”(承商費用)亦趨於上漲。行商的壟斷經營權的膨脹與承商所需繳納銀兩的增加,呈現同一趨勢,就是這種交換關係的反映。而作為行商來說,他們支付的不僅有承商費用,而且還有在承商期間對於清政府的種種義務(諸如攬包進出口貨稅,負責處理涉外事務,管理外國商人等等)。通過這種交換,造成了對外貿易壟斷所有權與壟斷經營權的分離,從而使專制國家從繁瑣的對外貿易事務中擺脫出來,不承擔對外貿易的任何風險而穩操外貿關稅的收入。同時又利用其一手扶植起來的行商,作為專制國家控制、壟斷、干預對外貿易活動的工具。所以行商制度的產生與發展,標誌了對外貿易的壟斷所有權與壟斷經營權的分離,是清政府干預商業經濟,控制對外貿易的統治經驗高度成熟的表現。
行商是掌握著對外貿易壟斷經營權的特權商人。行商為了更有效地行使其所掌握的對外貿易壟斷經營權,清政府為了更牢固地控制行商的經營活動,由此,在行商制度下產生了行商的行會組織——公行。公行的產生,是行商制度成熟的表現。公行的作用,在於防止行商之間的競爭,由此使得行商的壟斷經營權得到進一步的加強。據亨特所說:“行商總稱公行,作為一個團體說來,是1720年成立的,從那時起,除了1725年前的一個短時期外,行商都是中國對外貿易的壟斷者。”“行商是中國政府承認的唯一機構,從中國散商販買的貨物只有經過行商才能運出中國,由行商抽一筆手續費,並以行商名義報關”,“他們享有統治廣州港對外貿易的獨佔權”。
公行加強行商的對外貿易壟斷經營權,主要表現為採取統一制定進出口商品價格的方法。外國商人“帶來貨物,令各行商公同照時定價銷售,所置回國貨物,亦令各行商公同照時定價代買”。這種由公行統一制定價格的辦法,為行商帶來了高額壟斷利潤。據夏燮《中西紀事》所載,“粵中初設洋商通事洋行,據為壟斷之利”。亨特說:行商因“享有統治廣州港對外貿易的獨佔權,每年獲利達數百萬元”。因而,由公行統一制定價格一直遭到東印度公司等外國商人的反對。他們千方百計地企圖瓦解公行,主要就是這個原因。其理由是“如有公行交易,貨低價高,任公行主意,不到我夷人講話”。
另外,行商的對外貿易壟斷經營權還表現為獨佔對外貿易,不許私商染指。“設立洋商,例 以家業殷實者為之,而輸其餉。洋貨入口,總歸洋商販買,不得它越。”清政府曾頒有法令,承認行商的對外貿易壟斷經營權,禁止行外商人同外國商人貿易,“凡夷商一切交易事宜,俱系責成行商經手,以杜內地民人勾結滋事”。行商在獨佔對外貿易的過程中,攫取了巨額的壟斷利潤。光緒十年(1884),奉旨辦理廣東海防的彭玉麟說:“咸豐以前,各口均未通商,外洋商販,悉聚於廣州一口。當時操奇計贏,坐擁厚貲者,比屋相望。如十三家洋行,獨操利權,豐享豫大,尤天下所艷稱。”
綜上所述表明:行商制度的產生是對外貿易壟斷所有權與壟斷經營權分離過程的產物。公行組織的出現標誌著行商所擁有的對外貿易壟斷經營權的加強。負責招商和建立行商制度的粵海關監督及廣東巡撫、兩廣總督是清政府掌握對外貿易壟斷所有權的代表。在他們管制、監督之下的行商是具體經營對外貿易業務的特權商人。
清代行商制度是官商結合的產物,行商制度下的行商具有官商的特徵。 《廣東新語》中所載詩曰:“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即是明證。
實行行商制度的關鍵在於選擇合適的商人來承充行商。《粵海關志》說:“蓋商得其人,則市易平而夷情洽;商不得人,則逋負積而餉課虧。”嘉慶年間粵海關監督德慶說:“

行商制度
同時,從行商的職責來看,也是有官商的性質。在行商制度下,行商要為清政府承擔種種義務。行商承擔的第一項義務是負責為清政府徵收進出口貨物的關稅。“凡外洋夷船到粵海關,進口貨物應納稅銀,督令受貨洋行商人,於夷船回帆時輸納,至外洋夷船出口貨物,應納稅銀,洋行保商為夷商代置貨物時,隨貨扣清,先行完納。”為了保證關稅的及時徵收,清政府規定:行商如有“欠餉之案,俱移會督撫,將乏商家產,查封變抵,其不敷銀兩,著落新辦行業之新商,代為補足。如行閉無人接開,眾商攤貼完結”。徵收海關關稅,歷來是官吏的職責。但是,在行商制度下,由行商來負責徵收關稅,這就說明行商已具有官吏的職責。
行商承擔的第二項義務是負責管理來華的外國商人。乾隆二十四年頒布的“防夷五事”中曾明確規定:“夷人到粵,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也。查歷來夷商到廣貿易,向系寓歇行商館內,原屬事有專負。”這裡所說的“行商館” ,史稱“夷館”或“商館”,是行商的產業,出租給外商。住入“行商館”的外國商人,由行商負責加以管制,“至夷商居住行館,稽查出入,乃該行商專責,豈可聽鋪戶民人私相交易!”(34)管理來華外國商人,屬於涉外治安事務,理應由官吏負責。但是,在行商制度下,行商被賦予此種職責,這也說明行商具有官吏的性質。
行商承擔的第三項義務是受清政府之命,辦理同外國商人各種涉外事務。清政府曾有規定:“該夷人遇有公事,呈遞夷稟,均由該國大班,轉交洋商,轉呈總督。”據亨特的記載:行商的“責任則是作為中間人,處理當地政府對於外人在廣州居住的一切有關事件,以及外人人身和財產的安全”。在道光十年所發生的盼師夫人(Mrs.WillianBaynes)事件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行商所承擔的官吏的職責。當時,兩廣總督李鴻賓命令廣州知府轉飭總商伍受昌等令其(盼師夫人)退回澳門,不得在省城停留,嚴禁乘坐肩輿。在這裡,行商與其說是經營對外貿易的商人,毋寧說是清政府的外交官。總之,從上述行商所承擔的義務來看,他們已經具有了官吏所具有的種種職責。

行商制度
清政府利用行商來管理與控制對外貿易,一方面是為了在政治上駕馭那些被他們稱為“姦宄莫測”的“夷人”,防範內地人民與“夷人”的交結,目的是為了鞏固其政治統治。
另一方面,清政府在對外貿易中推行行商制度,是為了保證關稅徵收的穩定,增加其財政收入。粵海關歷年稅收儘管數目不等,卻是一筆頗為可觀的稅款進項。對清代皇室來說,其經濟意義就更為重要。對於這個問題,只要查閱一下當時海關稅收報告,就可一目了然。據歷史檔案記載:道光十九年(1839),粵海關共征銀1,448,558兩。移交廣東布政司藩庫所謂正額銀40,000兩,銅斤水腳銀3,564兩,兩項合計43,564兩,僅佔總數的百分之三;其次,留作海關之用的被稱為“通關經費、養廉、工食及熔銷折耗等銀”共47,285兩,僅佔總數的百分之三。其餘百分之九十四的銀數中,有1,002,909兩解戶部,355,000兩解內務府,專供皇室使用。據計算,解內務府的銀兩占粵海關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四。內務府從對外貿易關稅收入中獲得355,000兩白銀,這在內務府總收入中佔有較大的比重。所以,清政府實行行商制度,除了政治目的之外,亦有搜刮財富,充實帑銀的意圖。這個經濟上的目的,是不容忽視的。
同時,行商制度還能保證清皇室滿足對海外奢侈品的貪婪要求。清代行商制度規定:行商必須每年向皇室“貢銀”與“貢物” 。行商每年要代廣東巡撫、粵海關監督採辦鐘錶洋貨,作為“貢品”,呈獻皇室,所需費用全部由行商“賠墊”。“從前廣東巡撫及粵海關監督,每年呈進貢品,俱令洋商採辦對象,賠墊價值,積習相沿,商人遂形苦累。”(43)乾隆五十五年諭令:“嚴飭該督撫等,嗣後不準呈進鐘錶洋貨等物,並嚴禁地方官向商人墊買物件,以杜弊端……嗣後該監督亦不準備物呈進。”三十年後,嘉慶二十五年(1820)又恢復呈進“貢品”,“畢獻方物,若一概停止,究於體制未協,且無以申芹獻之忱;所有方物,仍照舊例呈進。粵海關監督遵奉行知,准進朝珠、鐘錶、鑲嵌掛屏、盆景、花瓶、琺琅器皿、雕牙器皿、伽楠香手串、玻璃鏡、日晷、千里鏡、洋鏡”。此外,行商還有向皇上“貢銀”的義務,“查向來備貢銀五萬五千兩,繫於乾隆五十一年間該商等感戴,情殷投效,具呈吁捐,每年解繳備用”。同此,使清朝統治者獲得了經濟上的實惠和滿足了其對海外奢侈品的貪慾。
清代行商制度的上述壟斷特徵,是中國傳統社會後期對外貿易中特有的現象。善於將對外貿易中的壟斷權力加以分離,培植亦官亦商的行商資本集團,這充分反映了當時中央集權的專制國家對商業經濟實行干預的巨大能力。清政府對對外貿易的干預,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是富有成效的,它為專制國家帶來了財政收入,有效地抵制了西歐資本主義侵略勢力夢寐以求的打開中國市場大門的願望。同時,也有效地維持了當時對外貿易的秩序。
清代行商制度是在當時的政治、經濟矛盾運動過程中運行的,所以必然要受到這些矛盾 運動過程的左右。而支配著清代政治、經濟矛盾運動過程的主要軸心是各種社會政治、經濟集團的利益關係。行商制度在實際的運行過程中,涉及清政府、粵海關等衙門的官吏、行商、外國商人,中國行商以外的私商集團之間的利益關係。這些社會政治、經濟集團的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所構成的矛盾運動,形成一股合力,制約著行商制度的實際運行過程,決定著行商制度發展的命運。行商制度的衰落,是上述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本節主要從利益關係來考察行商制度衰落的原因。
行商與清政府及其官吏之間的利益關係
在上述利益關係中,行商始終處於矛盾的中心。首先來考察一下行商與清政府及其粵海關等衙門官吏之間的矛盾關係。在這三者關係中,粵海關等衙門官吏處於中介地位,他們是勾通清政府與行商之間的橋樑。他們一方面代表著專制國家的利益,運用政治行政手段和對對外貿易的壟斷所有權,來管理行商的業務活動,監督行商履行其各種義務。另一方面,他們又有著自己的私人利益。為了滿足私慾,他們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勒索行商,謀取私利。他們的這種以權謀私的行為,在所謂“規禮”問題上,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屈大均指出:“吾廣謬以富饒特聞,仕宦者以為貨府,無論官之大小,一捧粵符,靡不歡欣過望,長安戚友,舉手相慶,以為十郡膻境,可以屬饜脂膏……其人至官,未及視事,即以攫金為事,稍良者或恣睢掠拾,其巧黠者則廣布爪牙,四張囊橐,與胥吏表裡為奸,官得其三而胥吏得七。”陞官發財是官吏的人生哲學,他們視“粵符”為肥差,一旦走馬上任,就趁機撈一把。考之有關記載粵海關官吏的史籍資料,可以看出粵海關衙門的官吏幾乎是無官不貪,無吏不污。
“規禮”,亦稱陋規,其名目繁多,不勝枚舉。在廣州,上自將軍督撫監督,下至書吏丁役家人,視行商為肥羊,無不貪黷勒索,得贓分肥。雍正五年,廣東巡撫兼管海關楊文乾在奏摺中說:“查粵海關陋弊甚多,臣先將書役藉稱繳官公費,需索商民陋規銀一萬餘兩情由查出革除,奏明在案。此外尚有分頭、擔頭、梁頭等項,系管關衙門陋規,相沿已久,臣思若一併革除,徒於洋商有益,與小民無涉。況洋商獲利甚厚,亦不必令其再加便宜。但臣受恩深重,絲毫不敢自私。總計各項陋規,共得銀三萬八千一百有零。”在這裡楊文乾裝出一副清官的架勢,似乎大有整頓陋弊的決心。但是,他乾的只是革除“書役”的“陋規銀”,而對“管關衙門”的陋規則聽之任之。其實,“管關衙門”的陋規不革除,則上行下效,“書役”等胥吏怎麼會洗手不幹勒索的勾當呢?可見,“革除”云云,儘是官樣文章。更奇者,奏摺中竟然為“管關衙門”的陋規辯護,說什麼“陋規”“一併革除,徒於洋商有益”,“況洋商獲利甚厚,亦不必令其再加便宜”。這真是典型的“紅眼病”患者的“理論”!這種“理”是中國傳統社會財產關係沒有明確法律界限的歷史狀況的反映,是官吏可以隨心所欲地勒索“富商”的經驗之談。上述“理論”的炮製者,自稱為“絲毫不敢自私”的廣東巡撫楊文乾,其實是個大貪污犯。雍正四年,他漏報稅銀六萬兩,同時在“彝人帶來銀兩內,每兩抽銀三分九厘,謂之分頭,計得銀二萬餘兩,此系粵海關舊例。再紅黃顏色綢緞,例禁出洋,楊文乾令其置買,每緞一匹,得銀七錢;絲綢五錢,綢匹及線,每斤得銀四錢,約計得銀萬兩。又洋船所載,多半皆屬番銀,於起船時勿論其是否置貨,先以每兩加一抽分,得銀四萬兩。此系楊文乾例外之求。復以進上物件,洋船開艙時檢選奇巧,統歸署內,並不發價,專行代償,約值銀二萬餘兩”。總計上述各項,楊文乾在雍正四年共貪污勒索銀十五萬兩。竟然超過當年粵海關的關稅收入(正額銀四萬三千七百五十兩,羨餘銀四萬八千零,共九萬一千七百五十兩)。由此可見,粵海關等衙門官吏對行商的勒索是何等厲害!
清政府作為對外貿易的壟斷權力所有者,對其招來的行商施行種種權力,藉此獲得經濟利益。首先,清政府總是力圖獲取更多的關稅收入。除了粵海關的“正額”與“羨餘”之外,清政府往往借口整 頓吏治,把官吏的“規禮”變成歸公銀兩。雍正四年,清政府“管關巡撫楊文乾等節次報出(規禮銀)歸公,每年自數萬兩至十五萬餘兩不等”。這裡需要指出的是“規禮銀”歸公以後,表面上看來是把官吏的勒索,變成國家的收入。其實不然,舊的“規禮”歸公以後,又產生新的“規禮”。據乾隆二十四年李侍堯等奏:“臣等查直省各關,從無規禮名色載入則例,獨粵海關存有此名者,因從前此等陋規,皆系官吏私收入己,自雍正四年起,管關巡撫及監督奏報歸公,遂同正稅,刊入例冊,循行已久,自當仍舊徵收。但存此規禮名色,在口人役,難免無藉端需索情弊。”以後,清政府即“將此項規禮等名目,一概刪除,合併核算,改刊每船進口歸公銀若干,出口歸公銀若干,俾歸一定”,企圖消除“額外私征及賄縱浮收等弊”。但是,事實上粵海關等衙門的官吏,在清代實行行商制度的時期,一直在徵收非法的“規禮”,“不合法的苛征”“常常超過正課四倍以上,而在最重要的貨物之一棉貨上,則竟達十倍”。又如徵收一兩稅銀,“法定的加耗共計為一錢一分六厘,但實際上則徵收三錢。這種情況唯一可能的解釋是,這項差額系非法訛索,由粵海關及其屬吏分肥了”。由此可見,“規禮”歸公的實際負擔是落在行商與外國商人的肩上。粵海關等衙門官吏的利益並未因“規禮”歸公而遭受損害。
其次,除了關稅收入之外,清政府對行商還有種種額外的需索。凡遇到清政府要興修水利(“河工”)、鎮壓農民起義及某些軍事費用的開支,乃至皇帝的壽辰,行商都需以捐獻的名義,向清政府交納巨額銀兩,據表一的不完全統計,自乾隆中葉到道光二十二年行商制度廢除時止的七十年中,行商向清政府捐款共有二十二次,捐款數額總計達937萬兩之多,平均每年捐款約十三萬兩白銀。這筆銀兩超過行商制度規定的行商每年向清政府交“貢銀五萬五千兩”之數的二倍。由此可見,清政府和其官吏一樣,都以行商為勒索的對象。
清政府對行商的額外勒索,在粵海關官吏的奏摺中被說成是行商“情殷報效”、 “出於至誠”,“情願捐輸”,其實這不過是欺人之談。據亨特記載:“政府常常向他們(指行商)勒索巨款,迫使捐獻,例如為了公共建築、救災、江河決口等等。有時見到浩官,我們談起天來了。‘浩官,今天有消息嗎?’‘壞消息太多了!黃河又鬧大水了。’他說。這當然不是好兆。‘官大人來看你了嗎?’‘沒有,但他派人送了一封札子來。他明天來。讓我拿出二十萬塊洋錢。’這顯然仍是老一套怨言,又是‘勒索’,而且這次數目大得驚人。”由此可見,行商們都把這種“捐獻”視為“不是好兆”,是“勒索”,因而私下裡怨聲載道。據清代歷史檔案記載,這些捐獻,行商們往往拖欠不交,粵海關吏不斷地下令勒限年月追清欠款。甚至鬧得“屢催罔應,實屬任情延玩,未便再事姑容”的地步。粵海關監督為此“奏請將天寶行商人梁承禧之訓導銜,仁和行商人潘文海之州同銜,暫行斥革”。爾後又將“天寶行商人梁承禧發交南海縣監追,予限一年,勒令掃數清款;如屆期不完,即行奏明定地發遣,未定銀兩著落各商攤繳”。可見,所謂的“捐獻”,實際上是專制國家利用政治權力進行強制的敲詐勒索。
粵海關等衙門官吏和專制國家對行商的勒索,是導致行商破產的主要原因之一。當時史料記載說:“又且正餉外,洋商多被勒索銀兩,且有下吏暗中要賄賂、陋規,如此內商與遠商均被壓害。”行商的破產倒閉,在嘉慶年間已見端倪,當時的上諭說:“洋商向有十三行,現祇存八行,其積年消乏可知。且該商等捐輸報效,已非一次,自當培養商行,令其家道殷實,方不致稍形疲累。”道光年間,行商雖然仍不斷向清政府捐納銀兩,但實際上大多數行商資本已十分拮据。到道光十九年,行商積欠備貢、參價、商捐、攤繳等項銀兩總數已超過百萬之數。在鴉片戰爭前的道光年間,行商總共捐輸給清政府的銀兩為八十七萬兩(參見表一),而積欠商捐銀卻達一百三十萬餘兩,可見,當時行商資本的拮据狀況。由此,在道光年間,行商紛紛倒閉。“道光四年以後,各洋行內有麗泉、西成、同泰、福隆等行節次倒閉,共欠稅餉銀六十八萬兩,夷帳銀一百四十五萬餘兩”。到道光十一年間,“洋行殷實者不過一二家,自上年八月至今六個月之內,追完舊欠銀五十餘萬兩,實屬筋疲力盡”。據外人記載:“每逢本省或國家有了特殊的事故,他們(指行商)必須‘捐獻’,由此獲得個頭銜、頂戴。某家行商如果破了產,或被發現有操行不正之罪,便被流放到伊犁,同時其它行商須代其償債……經常的壓制與勒索已使得大多數行商瀕於危境,難以支持。因此貿易已受到阻礙,稅鈔任意勒征,外國商人遂常常和一些沒有正式建行而在交易中困難較少的散商進行大量的貿易。”綜上所述表明:清政府和粵海關等衙門的官吏對行商的肆意敲詐勒索,導致了行商的破產。而行商的破產造成了行商制度的危機。“數年以來,夷船日多,稅課日旺,而行戶反日少,買賣事繁,料課難於周到,勢不能不用行伙。於是走私漏稅,勾串分肥,其弊百出。”行商制度的危機帶來了清政府在對外貿易活動中的失控。所以,在上述利益關係的矛盾運動支配之下,行商制度必將滑到瀕臨崩潰的邊緣。
行商與行外商人的利益關係
在行商制度的實行過程中,行商與行外商人之間也存在著利益關係。所謂行外商人是指 廣州十三行附近中國街的“小商鋪”和經營販運貿易的中國私營商人。他們沒有清政府特許的對外貿易壟斷權力,他們同外國商人之間的交易,實際上是走私性質的貿易活動。根據行商制度的規定,“小商鋪”被允許售與外國商人一些零星的個人消費品,諸如蔬菜食物之類的商品。但不準經銷由行商壟斷經營的絲、茶、土布、瓷器等大宗貨物。當然,經營販運貿易的中國民間商人亦不準向外國商人出售上述大宗貨物。可是實際情況並非完全依照行商制度的規定而進行。在行商制度實行的年代里,行外商人與外國商人之間的大宗貨物貿易屢有發生,並且有越演越烈的發展趨勢。如乾隆年間,“買賣貨物,亦多有不經行商、通事之手,無稽店戶私行到館,誘騙交易,走漏稅餉,無弊不作”。“近來狡黠夷商,多有將所余資本,盈千累萬雇倩內地熟諳經營之人,立約承領,出省販貨,冀獲重利”。當時有行外商人汪聖儀“領取英商洪仁輝本銀營運,與之交結”。嘉慶年間,英商里德·比爾行在他們的信件里說:該行的細洋布等印度布匹及紅木是售與“不願意在生意中露面的行外人”。又說:“從行外商人購買貨物已經成了此間的一個長久的和普遍的習慣,尤其是購買普通所謂的‘藥材’,他們做這一類貨物的生意比行商多得多;從行商那裡我們不能這樣便宜取得這一類東西。”嘉慶九年,有一個“具有很大財產和身價”的行外商人向英商訂定原棉貿易的契約。到了道光年間,行外商人與外國商人的走私貿易進一步發展,鴉片的走私貿易成了行外商人與外國商人交易的主要商品。“夷船等往往寄泊外洋,進口延緩,亦有竟不進口,旋即駛去,不特躉賣鴉片,並恐私銷洋貨……唯粵省與福建、江、浙、天津等洋麵毗連,各省奸徒坐駕海船,在外洋與夷人私相買賣,貨物即從海道運回。此等奸販,既不由粵省海口出入,無從堵拿。而洋貨分銷,入口漸少,於稅餉甚有關係。”為了躲避清政府的干預,這時的走私貿易已不在廣州進行,而轉向沿海近洋。如伶仃島在當時就是鴉片走私的基地。
中國行外商人與外國商人的走私貿易直接侵犯了清政府與行商的對外貿易壟斷權力,它使清政府的海關收入減少,行商的利益受到損失,因而清政府屢次下令禁止。在嘉慶十二年(1807)甚至封閉了廣州的二百多家“行外”商號,並將他們的貨物充公。但是,走私貿易非但沒有被禁絕,反而進一步地發展起來了。這是什麼緣故呢?
第一,中國行外商人與外國商人的貿易是走私貿易,他們之間成交的商品價格要比通過行商轉手便宜得多。英國散商和美國商人都認為同“小商鋪”做大宗貨物如絲、土布甚至茶葉等生意是有利可圖的。當然,中國行外商人亦有同樣的感覺。唯利是圖,是商業資本的本質特性,在這一點上中外商人相互結合起來,不惜置身家性命於度外,進行違法的走私貿易。而這種冒險的動機與違法的行為,往往與利潤的大小形成正比。清政府的海關關稅負擔越是沉重,行商的進銷差價越是巨大,官吏的勒索越是貪婪,那麼走私貿易的利潤也就越是豐厚。這豐厚的利潤乃是走私貿易發展的動力。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行商制度與走私貿易是一對孿生兄弟。
第二,行商的庇護,為走私貿易打開了方便之門。行商與行外商人之間的利益關係,是十分微妙的,他們之間既有利益上的衝突,又有利益上的一致。作為壟斷商人,他們具有官僚的部分特點,走私貿易侵犯了他們的壟斷權力,有損於他們的利益。而另一方面,他們又具有商業資本所固有的追求最大利潤的特點,他們與一般商人一樣,都要遭受官吏的欺侮與勒索。而有時他們所遭受的欺侮與勒索,與一般商人相比,往往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只要庇護行外商人的走私貿易能為他們帶來利益上的好處,他們也就會同行外商人結合起來,進行違法的活動。當時從事走私貿易的英商里德·比爾行的內部信函中說:“這個口岸(廣州)的法律的確並不完全許可這種交易——行外商人必須用行商的執照或名義裝運貨物——可是,習慣卻承認它,甚至可以用真正賣主的名義申請通事和行商起運貨物,因為他們從這種生意取得規費,對於這種生意也就默許了。”“規費”——錢,對於行商來說,只要有了錢,什麼禁令,法規均可拋到九霄雲外。這就是商人的本性。
第三,行商資本的缺乏和官吏腐敗,是無法禁止走私貿易發展的一個原因。正如我們在考察行商與清政府及其官吏的利益關係時所說明的那樣,行商深受專制國家和官吏的各種壓榨,行商資本常常處於短缺狀態,而廣州的對外貿易卻在不斷的發展。因此,行商越來越顯得捉襟見肘,他們“並沒有經營廣州全部對外貿易的足夠的資本”(76)。而行商制度又不允許商人隨便充當行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私營商人只能以行外商人的身份,通過走私貿易的方式,使自己的商業資本在對外貿易中增殖,發揮它的作用。另外,官吏除了在向行商敲詐勒索之時,發揮他們的特殊天才之外,在管理對外貿易方面,在對付走私貿易方面,他們只是十足的蠹才。如面對日益猖獗的鴉片走私,他們除了高談空論之外,便是束手無策。在外國資本主義侵華勢力的威脅之下,他們唯有屈服與讓步的“才能”。道光八年(1828)駐廣州的總督和粵海關監督會銜發布了“小商鋪經營貿易告示”,縮減行商壟斷經營貨物的品種範圍,擴大了“小商鋪”經營的商品品種。這個告示,削弱了專制國家和行商的壟斷權力,是清代行商制度衰落的徵兆,是清政府在外國資本主義侵華勢力的進襲下,步步退卻的記錄。
上述表明,行外商人與外國商人之間的走私貿易,是衝擊行商制度的力量。行商與行外商人的結合,是由於他們利益上有一致的地方。這種結合,助長了走私貿易的發展。走私貿易是行商制度的必然的伴生物。清政府在建立行商制度的過程中,同時鍛造了摧毀它的武器。這個武器,就是走私貿易。
行商與外國商人之間的利益關係
行商在內遭受清政府與粵海關等衙門官吏的敲詐勒索,使他們積聚的財富遭受嚴重損失。作為商人資本的行商所具有的獲取利潤的內在動力,並沒有因為他們充當了專制國家控制對外貿易的工具而減弱。他們企圖在與外商的交往中實現其攫取利潤的目的。他們一方面藉助於清政府的力量,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壟斷經營對外貿易的權力,在與外商的交易過程中,獲得利潤,另一方面他們又利用手中掌握的管理外國商人的政治特權這一有利條件,投身於外商的懷抱,進行非法貿易活動,藉此獲得非法收入。他們不擇手段地獲取利潤,充分反映了商人資本的特徵。
行商制度
行商利用其所掌握的對外貿易壟斷經營權在與外商的交易過程中,獲取利潤,首先表現在“行用”問題上。所謂“行用” ,外文史料稱之ConsooFund(公所經費)。“行用”是行商所擁有的對外貿易壟斷經營權的產物。由於外商來華貿易,必須與行商交易,行商便利用其對外貿易的壟斷經營權力,強制性地規定按貿易額向外商抽取一筆款項,用作“公行”的經費。“查行用原系各行中所抽羨餘,以為辦公養商之用”。當初“行用者,每價銀一兩,奏抽三分”,即按進出口貿易額的3%比率抽取“行用”。乾隆四十五年(1780),因當時行商顏時瑛、張天球拖欠夷帳,無力償還,粵海關下令“各商攤還”。於是,“各商定議,將本輕易售之貨,公抽用銀,分年還給,經前任總督巴延三、監督圖明阿奏明,列款出示曉諭。檢查此次原案,亦止加抽進口貨物,共二十二樣,並無呢羽匹頭在內。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前監督李質穎因議速清夷欠,飭令洋商增加行用。據舊商十家聯名稟請加抽進口出口貨物共四十七樣,其匹頭亦未入撫分之列。遞年清還夷欠,捐款軍需,從無短少貽誤”。由此可見,“行用”最初的用途是“以為辦公養商之用”,“以給洋行商人之辛工也”。爾後用途漸廣,“清還夷欠,捐款軍需”概出其中。隨著“行用”用途的廣泛。“行用”的抽取比率不斷提高,嘉慶十五年東印度公司大班刺佛等訴於廣東巡撫韓崶,略曰:“始時洋商行用減少,與夷人無大損益,今行用日伙,致壞遠人貿遷。如棉花一項,每石價銀八兩,行用二錢四分,連稅銀四兩耳。茲棉花進口三倍於前,行用亦多至三倍,每石約銀二兩,即二十倍矣。他貨稱是。”由此可見,對進口棉花抽取“行用”已上升到貨價的25%,比原來增加了七倍多。再加上進口棉花增加了三倍,公行在進口棉花中抽取的“行用”比原來增加了二十倍。“行用”的用途,不管是“清還夷欠”,“還是捐款軍費”,行商徵收“行用”的目的,都是為了把自己的負擔轉借給外商的肩上。所以,徵收“行用”一直遭到外國商人的反對。上引東印度公司大班的訴詞,即是明證。嘉慶六年,英商末氏哈(RichardHall)亦有訴詞曰:“公司呢羽等貨一體加抽行用,與夷人生意大有損礙,懇請照舊不入抽分。”“行用”的徵收,雖然不直接增加行商的利潤,但從“行用”的用途來看,它減少了行商的種種開支,因此是一種間接增加行商利益的方法。
另外,行商利用其所掌握的對外貿易壟斷經營權,制定壟斷價格,藉此獲取壟斷利潤。當時,行商操縱著對外貿易的支配權,“洋人奉令惟謹,其見行商,皆旁立弗敢坐”。進出口貨物的價格全由行商決定,如“行商伍怡和各商第至海岸稍一瞭望,即遙指此船我出貨價若干,彼船我出貨價若干,便可交易,亦不細覽貨單”。由於行商在對外貿易中“壟斷居奇,賤買貴賣”,因而“每年獲利達數百萬元”。對於行商所制定的壟斷價格,外商一直持反對的態度。乾隆二十六年(1761),東印度公司廣州大班企圖利用行商之間的矛盾,要求和個別行商進行議價,拒絕公行的統一規定。甚至以拒不進貨,威脅公行。僵持了兩個月,最後仍然屈從於公行,不得不低價出賣自己的毛織品,並為購買茶葉而付出高價。事後,公司大班說:“只要公行繼續存在,我們和所有的歐洲人就必須忍受,我們必然要為我們的進貨付出比以往更高的價格。”乾隆四十二年(1777)東印度公司大班白立把(MatthewRaper)抱怨“行商茶又雜又不好,價錢又高”。
清政府對行商肆意敲詐勒索,而對外國商人卻顯得外強中乾,軟弱無力,總是懷有懼怕的心理。在外商的反對之下,清政府則對行商壟斷進出口貨物價格加以干預,嘉慶二十年九月二十八日兩廣總督蔣攸銛在奏摺中說,“經前任督臣朱珪、前任監督舒璽援照乾隆四十五年酌議行規,洋船每年到廣,將出口入口各貨,摘其大宗銷售最多者,照時值定價,公平交易。其餘各貨,亦隨時酌議價值,不致懸殊。既不病夷,又不虧商。自應仍循舊章妥為辦理,俾各行承買各貨,照時值定價,隨買隨賣;固不得高抬居奇,亦不得減價賤售,各期公平交易,貨物流通等因。咨部核覆,亦在案,至今仍遵照辦理。並由監督不時稽查,如有將價值任意低昂,即行查究”。清政府之所以不準行商“高抬居奇”,是因為它害怕外國商人以此為借口,騷擾沿海疆域。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治統治,清政府不惜損害中國行商的利益,這充分暴露了清政府對商人資本的態度。它對行商的態度是利用,而不是加以保護。只要危及它的統治,它就不惜損害行商的利益而維護其自身的利益。
當然,行商對清政府的政策、法令也並非始終付諸實施,在利潤的誘惑之下,他們往往置清政府的政策、法令於九霄雲外,甚至違法犯禁。這表現在“行欠”、販賣鴉片等問題上。
所謂“行欠” ,就是行商所負外國商人的債務。據馬士書記載:最遲在十七世紀末期,就有行商負欠東印度公司大班債務的事情發生。行商之所以欠外國商人的債務,大概有如下幾個原因:
第一,行商代銷外商進口貨物,造成“行欠”。“洋商拖欠夷人銀兩,總由夷人於回國時,將售賣未盡物件,作價留與洋商代售,售出銀兩,言明年月,幾分起息。洋商貪圖貨物不用現銀,輒為應允。而夷人回國時,往往有言定一年,託故不來,遲至二三年後始來者,其本銀既按年起利,利銀又復作本起利,以致本利輾轉積算。愈積愈多,商人因循負累,欠而無償”。代銷貨物,對行商是有利可圖的,等於做了無本的買賣。所以,行商“輒為應允”。
第二,行商為了擴大經營範圍,借貸外商資本而造成“行欠”。“近來狡黠夷商,多有將所余資本,盈千累萬雇倩內地熟諳經營之人,立約承領,出省販貨,冀獲重利。即本地開張行店之人,亦有同夷商借領本銀,納息生理者。若輩既向夷商借本貿販,藉沾余潤,勢必獻媚逢迎,無所不至,以圖邀結其歡心”。早在乾隆初年,東印度公司廣州大班對中國行商墊款收購絲茶,已成定例。行商為了增加利潤收入,必須擴大投資,因此造成“行欠”。
第三,行商因經營不善,造成虧本,遂向外商借貸,以便維持門面,從而造成“行欠”。如行商“沐士方揭買港腳夷商呵啰等棉花、沙藤、魚翅、點銅之貨,該價番銀三十五萬一千零三十八圓,折實九八市銀二十四萬七千六百九十二兩四錢一分三厘。嗣因市價平減,價銀虧折,沐士方又經理不善,將貨價用缺,以致無力償還”。
第四,由於粵海關等衙門的官吏向行商肆意勒索,行商無力完納其所承保的稅餉,挪用外商款項,從而造成“行欠”。“據呈稱:自設保商,受累多端,入口貨餉,統歸保商輸納,保商任意挪移,將伊(夷)貨銀轉填關餉。又關憲取用物件短價,千發無百,百發無十,保商賠辦不前,即延擱該船,連誤風信。”行商挪移外商款項,企圖暫時轉借負擔,結果導致“行欠”。
綜上所述表明行商借貸外國商人的款項,進則為圖更大的利潤,退則為避免破產的厄運,總之是為了行商自身的利益。所以“行欠”問題長期不能給予解決。
清政府的態度卻截然相反,堅決反對行商借貸外國商人的資本。自乾隆朝,經嘉慶朝,到道光年間,三令五申地要加以禁止。乾隆二十四年(1759)頒布的“防夷五事”中明文規定:“嗣後內地民人,概不許與夷商領本經營,往來借貸。倘敢故違,將借領之人,照交結外國誆騙財物例問擬,所借之銀,查追入官,使外夷並知炯戒。”乾隆四十二年(1776)清政府又一次重申禁令:“近日竟有賒欠夷人貨價盈千累萬者,如此大宗貨物,皆系該行商司事夥伙,藉與夷商熟悉,遂以自開洋行貨鋪為名,任意賒取……但貨物既在行館發賣,必經行商之手,豈能諉為不知?嗣後如有鋪戶賒欠不還,惟該行是問。”嘉慶十四年,“行欠”益趨嚴重,為此清政府再次下令禁止:“是在該管監督嚴催洋行,早清夷欠;……若限期已屆,而商欠尚未清結,則罪在洋商。”道光年間,中英關係日益緊張,“行欠”又是行商與外國商人相互勾結的契機。於是,道光十一年(1831)清政府的禁令,措辭顯得更為激烈,“防範措施變得更加嚴密”。“查原定章程,違禁借貸夷商銀兩,串引勾致結者,照交結外國,借貸誆騙例問擬,所借之銀,查追入官等因。是行商借貸夷商銀兩,定章久為嚴密。惟行商與夷商交易,有無拖欠尾項,向於夷商出口時虛報了事,不足以昭核實而杜朦隱。應請嗣後除商民借貸夷商銀兩,串引勾致者,仍照例究治外,其行商與夷商交易,每年買賣事畢,令夷商將行商有無尾欠,報粵海關存案。各行商亦將有無尾欠,據實具結報明粵海關查考。如有行商虧本歇業,拖欠夷商銀兩,查明曾經具報者,照例分賠;未經報明者,即不賠繳,控告亦不申理。所有應償尾欠銀兩,應飭令行商具限三個月內歸還,不準延宕。如已歸結,即取具夷商收字,報明存案。若逾期不償,許該夷商控追;稍逾期該夷商不願控追,應聽其便。其當時不控,過後始行控追者,不為申理,以杜新舊影射之弊。”道光十一年的禁令,表明清政府對“行欠”問題要實行國家的干預,對不奏報粵海關的借貸行為,不予法律保護。而且不允許這種借貸關係保持三個月以上。
清政府的上述一系列禁令,實際上是治標不治本。因為“行欠”的最主要原因還是在於行商資本的不充實。行商資本既具有壟斷商業資本的特徵,它的壟斷經營的排他性,阻礙了其他商業資本的流入。因此,隨著對外貿易的發展,必然會出現資本短缺的現象。而在這種情況之下,清政府與粵海關等衙門的官吏又對行商肆意敲詐勒索,由此使資本缺乏的現象更趨嚴重。所以,行商要繼續經營其貿易活動,就不得不向外國商人借貸資本。其次,清政府在處理“行欠”問題上,缺乏常識,不能按照國際慣例來行使主權。如乾隆四十一年(1777)行商倪宏文賒欠商銀一萬一千二百一十六兩。案發後,乾隆帝上諭云:“據李質穎(廣東巡撫)奏,革監倪宏文賒欠英吉利國夷商貨銀一萬一千餘兩,監追無著,經伊胞兄倪宏業、外甥蔡文觀代還銀六千兩,余銀五千餘兩,遵旨於該管督撫司道及承審之府州縣,照數賠完貯庫,俟夷商等到粵給還,並請將倪宏文即照部議酌發等語。倪宏文赤手無賴,肆行欺詐,賒欠夷商貨銀,多至累萬,情殊可惡……倪宏文著發往伊犁,永遠安插,以示儆懲。”乾隆四十五年後,清政府規定:行商破產以後,將無力償還的“行欠”“著令通行(全體行商),分限代還”。無論是由清政府出面來歸還“行欠”,還是“著令通行分限代還”,行商的破產,都不損害債權人的利益。這種做法,顯得十分愚昧無知。因按當時國際對外貿易的慣例,經營對外貿易商破產後從無同行歸還欠款之例。如“行商對於外國人的‘倒歇’並沒有同樣的保證;不僅是聲名狼藉的亞美尼亞人貝本(C.M.Babarm)之類的騙子,就是公司的監理委員會的投機大班像詹姆士·厄姆斯東爵士(SirJamesUrmston)之流也是一樣,他私人名下拖欠了幾個行商的款子好多年。當行商以浩官為首向董事會提出申訴,要它也按照公行在一切情況下都清償‘破產’行商債款的同樣辦法,來付清它的廣州大班的債務的時候,董事會拒絕了”。清政府如此處理“行欠”的歸還問題,使得外國債權人的利益有了鐵一般的保障,這樣勢必導致外國商人不管行商殷實與否,隨意出貸資本。由此,反而助長了“行欠”的發展。
清政府在處理“行欠”問題上的愚昧無知和三令五申禁止行商借貸外國商人的資本,是有其目的的。乾隆帝的上諭披露了隱藏在其政策法令背後的心病。上諭說:“且朕此番處置,非止為此事,蓋有深慮。漢唐宋明之末季,受昧於柔遠之經,當其弱而不振,則藐忽而虐侮之,及其強而有事,則又畏戄而調停之,姑息因循,卒至釀成大釁,而不可救……英吉利夷商一事,該督撫皆以為錢債細故,輕心掉之,而不知所關甚大,所謂涓涓不息,將成江河者也。”乾隆帝的心病就是俱怕“錢債”之類的“細故”小事,會“釀成大釁”,危及其統治。這種心病的根源在於缺乏與外國來往的自信心。無論其表現得狂妄自大,還是恐怖異常,都反映了他的虛弱本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