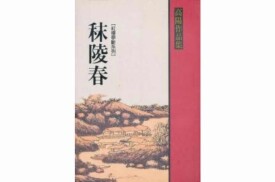秣陵春
秣陵春
秣陵春,高陽作品系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秣陵春是一部寫盡曹、李兩家由朱門繡戶,錦衣玉食到家道中落乃至籍沒歸京的榮辱興衰過程的歷史小說。
“紅樓夢斷”,用高陽的話說,寫的是“曹雪芹的故事”,是一部寫盡曹、李兩家由朱門繡戶,錦衣玉食到家道中落乃至籍沒歸京的榮辱興衰過程的歷史小說。 《秣陵春》是第一部,高陽揣摩曹雪芹原意,以鼎大奶奶的自盡來曲釋“秦可卿淫喪天香樓”,從而開始了蘇州織造李煦家族的中落和衰敗。...
是清初所謂的“興亡悲劇”之一。
(興亡悲劇,顧名思義是歷史興亡感的流露,但這種興亡感往往與情緣糅合在一起,小家的悲歡離合與國家的盛衰興亡交相輝映,纏綿悱惻。雖由家國悲劇衍化而來,但它們不單是家國覆滅的悲痛,更在於通過朝代的變更,傳達對整個人生的空幻之感。納入我們視野的清初興亡悲劇包括:主要是傳奇,有吳偉業的《秣陵春》、徐石麟的《浮西施》、洪升的《長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等。此外,吳偉業的雜劇《臨春閣》、《通天台》雖然其中沒有佔主體的愛情素材,但仍不失是一部部抒發興亡之感的劇作。它們將興亡與情緣轉化為審美的藝術形式,強調悲劇境遇,在審美效果上以感傷、哀艷為特色,這恰恰是中國悲劇精神的集中體現,筆者力圖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闡釋。)
吳偉業的《秣陵春》是清代最早一個體現此情懷的傳奇。劇中徐適與展娘同為前朝南唐名門要將的後代並忝作近鄰,隨著改朝換代,曾經的門庭若市,人丁興旺,如今只落得凄凄慘慘戚戚,朱門洞敞,全不似舊時情況。徐適書劍飄零,浪跡金陵,不熱衷於仕途,成日把玩古董打發日子,展娘家父黃濟將軍府也是門庭冷落,擔心自己年衰,女兒展娘無所依傍,因夢中重溫前朝皇人保儀(展娘之姑,南唐後主之妃)替其擇婿一事,更添幾分惆悵。正巧,虛幻化為實,保儀仍借在天之靈,幾經周折,完成這一諾言,徐適與展娘喜結良緣。雖然小家得以團聚,然而看《秣陵春》收場詩才恍然若初醒,“門前不改舊山河,惆悵興亡系綺羅,百歲婚姻天上合,宮槐搖落夕陽多”,歲晚暮遲,徒留惆悵,百年好合的婚姻只能繫於上天的安排,實則無奈,山河依在,人的面目改!
《秣陵春》將興亡感寄寓在劇中人物的主觀情感之上,與愛情的悲歡離合沒有必然聯繫。南唐將軍黃濟出場時“歌鐘零落,花沒舊昭陽。老去悲看故劍,記當年、笳吹橫江。傷心處,夕陽乳燕,相對說興亡”的自我介紹;徐適拜謁後主廟時“蘚壁畫南朝,淚盡湘川遺廟。江山余恨,長空黯淡芳草,臨風悲悼,識興亡斷碣先臣表”的悲歌;就連深閨秀女展娘也發出“朱門洞敞,全不似舊時情況”的感嘆,借人物的身世之悲及主觀情緒流露出亡國之痛。劇中第一出《塵引》中說到:“悶把殘編誰是,剩有相思字。玉笙吹徹風流子,吾輩鍾情如此。一卷澄心堂紙,改抹鶯花史”,將故國之思改寫到愛情的筆調之中。其實劇中並無過多兩人之間情意繾綣的場面描寫,鍾情的並非專指展娘與徐適的愛情,實為戀舊情結,相思是對故國的思念。劇中的重要道具 —— 古董如玉闐杯、宜官寶鏡等,都是南唐舊物。收藏古董既是劇中人的主觀嗜好,也表現出作者對歷史的追懷。愛情只是輔助線條,放在兩個朝代中,兩個“大家”都對他們給以成全。從結構上說,興亡感也主要體現在前半部分對前朝皇人的虛幻性描寫中,而後半部分體現出作者在現實人生道路上的徘徊。這種徘徊將在第二部分進行論述。
吳偉業的《秣陵春》被冒襄稱之為:“字字皆鮫之珠,先生寄託遙深”,他的劇作“借古人之歌呼笑罵,以陶寫我之抑鬱牢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