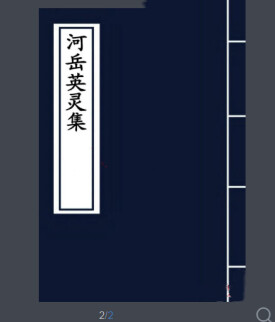河嶽英靈集
唐代殷璠主編的史書
《河嶽英靈集》是唐代殷璠編選的專收盛唐詩的唐詩選本。書中自序說:“粵若王維、王昌齡、儲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嶽英靈也,此集便以《河嶽英靈》為號。”
此書宋刻本分上下兩卷,明刻本分上、中、下三卷。選錄了從開元二年至天寶十二年24位詩人共234首(今存228首)詩,書的序、論簡述了詩歌發展歷程,正文中對所選詩人均作了評論。
此書論詩標舉”風骨“、”興象“,提出了“夫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既閑新聲、復曉古體,文質半取,風騷兩挾”等重要文學理論觀點。該書選篇精到,評論中肯,是現存的唐人選唐詩中最重要的一種。
此書宋刻本分上下兩卷,明刻本分上、中、下三卷。《敘》稱“起甲寅(開元二年,714),終癸巳(天寶十二載,753)”,一本誤作“終乙酉(天寶四載)”。它選錄了這個時期自常建至閻防24家詩234首,今本實為228首。由於選者具有較高的理論水平和藝術鑒賞能力,選錄標準又非常嚴格,因而在唐人編選的唐詩選本中歷來最受重視,影響深遠。
在《序》中,殷璠回顧了自梁至唐的詩歌發展道路,他把自梁以來二百多年的詩歌的發展分為四個時期。以為自蕭梁至武德,中間包括陳隋兩代,都是“尤增藻飾”,只重視詞採的華麗;唐開國以後,也仍然沿著齊梁的老路走,一直到貞觀末,才開始有了轉機。高宗、武后共有六十多年,殷璠稱之為“標格漸高”,大約因為這個時期有了四傑和陳子昂,已經不完全是亦步亦趨的按照前朝的式樣作詩了。接下去,是睿宗景雲時期,殷璠認為是“頗通遠調”,當時,沈、宋和李嶠、杜審言已經建立了律詩的格式,張說、張九齡、賀知章已顯露新貌,及至孟浩然、王翰等揚名之後,盛唐之音已在形成之中,故有“遠調”之說。這是殷璠對《文選》以後、玄宗之前一段時期詩歌發展的簡單的概括,也是符合詩歌發展實際的。開元、天寶之際,是唐詩繁榮興盛的時期,也是中國古典詩歌的音律和體裁發展到成熟的階段。殷璠真正要編選以使之流傳後代的正是開元十五年以後的詩歌。《序》中說:
“開元十五年以後,聲律風骨始備矣。實由主上惡華好朴,去偽從真,使海內詞人,翕然尊古,有周風雅,再闡今日。”
在這段話里,接觸到了幾個問題,一是盛唐詩歌的聲律風骨是從開元十五年(公元727年)起成熟的。這時盛唐時代的主要詩人李白、王維都已二十七歲,高適、岑參、李頎、王昌齡、崔顥等也屆壯年,在詩壇嶄露頭角。他們的出現,以新氣派、新詩風,使唐詩展現了新的氣象。
其次,殷璠把盛唐之音的形成原因歸之於玄宗的愛好與影響。這自然有些把問題簡單化了。一代詩風的形成,絕不會僅僅決定於帝王的好惡,而是經過長期醞釀、探討以及創作實踐的結果,它的原因是複雜的。但帝王的藝術傾向及其由此產生的號召與提倡,對藝術的發展所產生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玄宗即位之初,確如殷璠所說,“惡華好朴,去偽從真”,並從政令上對華麗的文風施加了批評和限制。在所下詔令中曾說:“我國家效古質,斷浮艷,禮樂詩書,是宏文德。綺麗珠翠,深革弊風。必使情見於詞,不用言浮於行。”(《玄宗禁策判不切事宜詔》)。又因為“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敕令改變考試內容(《玄宗條制考試明經進士》)。這些詔令既然事關士大夫的科舉前程,自然對革除浮艷詩風產生了相當的作用。
此外,在這段序文里,殷璠還把“風骨”視作盛唐之音的基本特徵。不言而喻,這也是《河嶽英靈集》選詩的重要標準。但是只簡單舉出“風骨”二字;畢竟太籠統了,他深恐未來讀者對此發生誤會,因而在《集論》中又作了一番具體的闡述:
“璠今所集,頗異諸家:既閑新聲,復曉古體,文質半取,風騷兩挾,言氣骨則建安為傳,論宮商則太康不逮,將來秀士,無致深惑。”(《集論》)
選者在“敘”和“集論”里論述了詩歌形式和內容之間的關係,認為“伶倫造律”,“為文章之本”;“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氣因律而生,節假律而明,才得律而清”,所以詩人“不可不知音律”;但又不可“專事拘忌”,流為“矯飾”。他批判了齊、梁以來詩歌“理則不足,言常有餘;都無興象,但貴輕艷”的不良傾向,指出唐代詩歌正是在糾正上述詩風中“去偽從真”,逐步向前發展,到了開元中期“聲律風骨始備”。殷璠評詩注重“風骨”和“興象”。他選錄的標準是“既閑新聲,復曉古體,文質半取,《風》、《騷》兩挾”;“如名不副實,才不合道,縱權壓梁、竇,終無取焉”。由於有比較正確的觀點作為指導,通過選詩以標舉其論詩宗旨,書中所選,雖因當時的條件限制,不可能搜羅得很全面,但這個時期的一些主要詩人如李白、王維、孟浩然、王昌齡、高適、岑參、李頎、崔顥、崔國輔、祖詠、儲光羲、常建等人的優秀詩篇都能入選,基本上反映了盛唐詩歌的面貌。書中沒有選及杜詩,可能由於杜甫蜚聲詩壇,較遲於上列諸家,當時還沒有篇什廣為流傳的緣故。
書中略仿南朝鍾嶸《詩品》,對入選各家詩歌的藝術風格都作簡括的評論,其中有不少精闢之見為後人所稱述。這種把評和選結合起來,在體例上實屬創舉,為後來許多評選本詩文集的灠觴,但由於此書自序說“分為上下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馬端臨《文獻通考》也都著錄為2卷,而明代毛晉、清代何焯都曾有手校抄本為2卷本,因此也有學者認為今本3卷是後人“推測其意似以三卷分上中下三品”,並非編者原意(孫毓修《河嶽英靈集校文》引黃丕烈說。
敘曰:梁昭明太子撰《文選》,后相效著述者十餘家,成自稱盡善。高聽之士,或未全許。且大同至於天寶,把筆者近千人,除勢要及賄賂者,中間灼然可尚者,五分無二,豈得逢詩輯纂,往往盈帙?蓋身後立節,當無詭隨,其應詮揀不精,玉石相混,致令眾品銷鑠,為知音所痛。
夫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有雅體、野體、鄙體、俗體。編紀者能審鑒諸體,委詳所來,方可定其優劣,論其取捨。至如曹、劉詩多直語,少切對,或五字並側,或十字俱平,而逸駕終存。然挈瓶庸受之流,責古人不辨宮商徵羽,詞句質素,恥相師範。於是攻異端,妄穿鑿,理則不足,言常有餘,都無興象,但貴輕艷。雖滿篋笥,將何用之?
自蕭氏以還,尤增矯飾。武德初,微波尚在。貞觀末,標格漸高。景雲中,頗通遠調。開元十五年後,聲律風骨始備矣。實由主上惡華好朴,去偽從真,使海內詞人,翕然尊古,南風周雅,稱闡今日。
璠不揆,竊嘗好事,願刪略群才,贊聖朝之美。爰因退跡,得遂宿心。粵若王維、王昌齡、儲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嶽英靈也,此集便以《河嶽英靈》為號。詩二百三十四首,分為上下卷。起甲寅,終癸巳。倫次於序,品藻各冠篇額。如名不副實,才不合道,縱權壓梁、竇,終無取焉。
《河嶽英靈集》有《四部叢刊》影明翻宋本、汲古閣本,通行的為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收入《唐人選唐詩(十種)》中。
在《序》中,殷璠回顧了自梁至唐的詩歌發展道路,他把自梁以來二百多年的詩歌的發展分為四個時期。以為自蕭梁至武德,中間包括陳隋兩代,都是“尤增藻飾”,只重視詞採的華麗;唐開國以後,也仍然沿著齊梁的老路走,一直到貞觀末,才開始有了轉機。高宗、武后共有六十多年,殷璠稱之為“標格漸高”,大約因為這個時期有了四傑和陳子昂,已經不完全是亦步亦趨的按照前朝的式樣作詩了。接下去,是睿宗景雲時期,殷璠認為是“頗通遠調”,當時,沈、宋和李嶠、杜審言已經建立了律詩的格式,張說、張九齡、賀知章已顯露新貌,及至孟浩然、王翰等揚名之後,盛唐之音已在形成之中,故有“遠調”之說。這是殷璠對《文選》以後、玄宗之前一段時期詩歌發展的簡單的概括,也是符合詩歌發展實際的。開元、天寶之際,是唐詩繁榮興盛的時期,也是中國古典詩歌的音律和體裁發展到成熟的階段。殷璠真正要編選以使之流傳後代的正是開元十五年以後的詩歌。《序》中說:
“開元十五年以後,聲律風骨始備矣。實由主上惡華好朴,去偽從真,使海內詞人,翕然尊古,有周風雅,再闡今日。”
在這段話里,接觸到了幾個問題,一是盛唐詩歌的聲律風骨是從開元十五年(公元727年)起成熟的。這時盛唐時代的主要詩人李白、王維都已二十七歲,高適、岑參、李頎、王昌齡、崔顥等也屆壯年,在詩壇嶄露頭角。他們的出現,以新氣派、新詩風,使唐詩展現了新的氣象。
其次,殷璠把盛唐之音的形成原因歸之於玄宗的愛好與影響。這自然有些把問題簡單化了。一代詩風的形成,絕不會僅僅決定於帝王的好惡,而是經過長期醞釀、探討以及創作實踐的結果,它的原因是複雜的。但帝王的藝術傾向及其由此產生的號召與提倡,對藝術的發展所產生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玄宗即位之初,確如殷璠所說,“惡華好朴,去偽從真”,並從政令上對華麗的文風施加了批評和限制。在所下詔令中曾說:“我國家效古質,斷浮艷,禮樂詩書,是宏文德。綺麗珠翠,深革弊風。必使情見於詞,不用言浮於行。”(《玄宗禁策判不切事宜詔》)。又因為“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敕令改變考試內容(《玄宗條制考試明經進士》)。這些詔令既然事關士大夫的科舉前程,自然對革除浮艷詩風產生了相當的作用。
此外,在這段序文里,殷璠還把“風骨”視作盛唐之音的基本特徵。不言而喻,這也是《河嶽英靈集》選詩的重要標準。但是只簡單舉出“風骨”二字;畢竟太籠統了,他深恐未來讀者對此發生誤會,因而在《集論》中又作了一番具體的闡述:
“璠今所集,頗異諸家:既閑新聲,復曉古體,文質半取,風騷兩挾,言氣骨則建安為傳,論宮商則太康不逮,將來秀士,無致深惑。”(《集論》)
選者在“敘”和“集論”里論述了詩歌形式和內容之間的關係,認為“伶倫造律”,“為文章之本”;“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氣因律而生,節假律而明,才得律而清”,所以詩人“不可不知音律”;但又不可“專事拘忌”,流為“矯飾”。他批判了齊、梁以來詩歌“理則不足,言常有餘;都無興象,但貴輕艷”的不良傾向,指出唐代詩歌正是在糾正上述詩風中“去偽從真”,逐步向前發展,到了開元中期“聲律風骨始備”。殷璠評詩注重“風骨”和“興象”。他選錄的標準是“既閑新聲,復曉古體,文質半取,《風》、《騷》兩挾”;“如名不副實,才不合道,縱權壓梁、竇,終無取焉”。由於有比較正確的觀點作為指導,通過選詩以標舉其論詩宗旨,書中所選,雖因當時的條件限制,不可能搜羅得很全面,但這個時期的一些主要詩人如李白、王維、孟浩然、王昌齡、高適、岑參、李頎、崔顥、崔國輔、祖詠、儲光羲、常建等人的優秀詩篇都能入選,基本上反映了盛唐詩歌的面貌。書中沒有選及杜詩,可能由於杜甫蜚聲詩壇,較遲於上列諸家,當時還沒有篇什廣為流傳的緣故。
書中略仿南朝鐘嶸《詩品》,對入選各家詩歌的藝術風格都作簡括的評論,其中有不少精闢之見為後人所稱述。這種把評和選結合起來,在體例上實屬創舉,為後來許多評選本詩文集的灠觴,但由於此書自序說“分為上下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馬端臨《文獻通考》也都著錄為2卷,而明代毛晉、清代何焯都曾有手校抄本為2卷本,因此也有學者認為今本3卷是後人“推測其意似以三卷分上中下三品”,並非編者原意(孫毓修《河嶽英靈集校文》引黃丕烈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