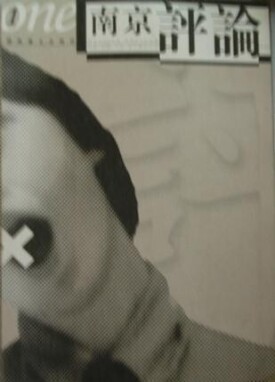南京評論
南京評論
《南京評論》作者:吳情水/ 張桃洲,2003年由國際華文出版社出版,創刊號出版時曾引起文學界廣泛關注。后出版兩期,《南京評論年度詩選》、《南京評論詩年選》仍在繼續出版中,價格:12元。
總編:吳情水
主編:張桃洲
責編:育邦 夏夜清 瘦叟 程世農
藝術主持:茅小浪
裝幀設計:王俊
一直到今天,對於很多人來說,南京仍然是一座想象中的城市:它的一半掩映在六朝宮牆的斑駁陰影里,另一半,則從混合著褪色照片、嘈雜市聲和懷舊意緒的民國鐘樓下浮現出來。所有從想象者腦海掠過的建築、街景、服飾、吃食乃至表情,無一不被塗上一層既絢爛、艷麗,又灰暗、頹敗的色調。那些浮遊於其間的文字,似乎也不例外。
長期以來,這種源於歷史(時間)的想象性誤讀,以及自身發展遭受遮蔽的現實,致使南京被寄予更多的文化上的期待,而不是以一座現代意義都市的面目出現在人們面前。相形之下,人們更願意將南京視為一種生活情景或氛圍的“代名詞”:這裡雨燕低飛,風光旖旎,一切顯得寧靜而安詳……。無疑,這樣的理解過分渲染了南京的空間特性,即僅把南京當作一個帶有南方氣息的地域概念,因而未免偏狹。
不過,有一點則是確實的:這座城市的體內從來就不缺乏對書寫的隱秘熱情。在它並不寬闊的林蔭底下,總棲歇著一些敏於詞語的人,一茬接著一茬,代代展現著江南一地的風俗與傳奇。南方的溫潤培育了寫作者的耐心,同時也掩藏了他們探索的鋒芒——由於種種偏見,他們中的多數耽於纖細的機巧,最終難逃閑情雅趣的宿命。
或許出於對上述誤讀和偏見予以匡正的渴望,但更是為表達對這座城市固有氛圍的珍惜與敬意,我們創辦了這份冠以南京之名的文學刊物。當然,寫作本身與這些毫無關係。寫作在這個時代,自有其特殊的伸展方向和命運,對此我們無須多說什麼。與其說一份刊物試圖倡導某種寫作風尚,不如說它將會提供這樣一處場所:在其中,一批寫作者自由集結,各自尋索通往寫作秘地的路徑。
二○○三年四月,南京
低矮的南京嗓音——寫在《南京評論》創刊號出版之際
五月的中國,一場卓有成效的低燒已經接近了尾聲,一本醞釀許久的文學刊物——《南京評論》2003年春季創刊號——悄然面世。從嚴肅的角度說,一本書和一個城市之間的必然聯繫是微乎其微的,這套叢刊雖然冠以《南京評論》的名號,但其中並不隱含文學地理學的特別意義。它和南京部分面容之間的明投暗合也屬於不可考證的範疇,它顯然更願意服從另外一種更加隱密也更加細微的文學願望,就如內頁上的那行黑底白字:重現文學的儆戒……。
《南京評論》並不是“南京評論”網站的紙本成果。雖然叢刊編委中的很多人員都和這個網站有關,但創刊號上的所有文字都是第一次結集出版,代表著這些作者目前最近的寫作水準和思考方向。叢刊總編為詩人吳情水,主編為青年詩評家、詩人張桃洲,編委名單包括代薇、朱朱、的克、西渡、臧棣、岩鷹、趙剛、馬鈴薯兄弟、沉河等,藝術主持為茅小浪。從這個名單來看,它基本上屬於一本同仁刊物。
出於人所共知的原因,《南京評論》採取的是以書代刊的方式,一年四期,沒有辦公地點和編輯部,它的成型完全基於時間性的樸素勞動。稿件來源相對集中。但文體上力求廣泛和前衛,分為詩歌、評論、小說、當代藝術閱讀四個版塊,這種安排將持之以恆。如同這本刊物的繼續發展。
本期《南京評論》在四個版塊中突出了詩歌的位置,並著重推介了南京女詩人代薇,刊載了她的十首作品,同時附有詩人、小說家黃梵所寫的詩評《代薇:本能頒布的詩歌榮譽》,詩人朱朱的《門鈴》和麥道的《連接代薇的虛線》,這是兩段融印象記和個人思忖於一身的篇幅。另有一篇《落地的聲音——代薇訪談錄》是代薇除了詩歌和散文之外的特殊創作,這些和代薇相關的文字把一個成熟、優秀的當代漢語詩人奉獻了出來。代薇作品中高華、節制、晴朗的語言外觀和珍貴的情感傾吐在九十年代以來的詩歌行進曲中是一個不可忽略的音符。
詩歌部分的其他作者大多成名已久,如朱朱、臧棣、馬鈴薯兄弟、陳東東等,他們的作品大量面世,已經有了太多說法和議論,這裡不加贅述。值得一提的是和這些名字並列的沈娟蕾、郭向華、吳情水等人的寫作,雖然向度不同,但他們幾乎一致地表現的是對生活的的過敏性記錄,充滿平緩但隱秘的抒情渴望,彷彿江南的丘陵地貌和梅雨氣候以陰影的方式落入了他們年輕的寫作過程。
九十年代的南京,一直是小說這種植物生長的優良濕地,這裡碰撞著各種新奇的小說觀念,同時收養著一大批寄身小說的自由職業者。在這裡列舉他們的名字是不恰當的,因為不用懷疑,文學史秩序、市場意志和個人功利企圖這些傷害文學本體的因素,也同樣程度地作用於他們,除了生活在共時軸上的南京這一點,要在南京為數眾多的小說家中找出可供書寫的相同之處,實在勉為其難。本期的《南京評論》在小說的數量上略顯單薄,但育邦和何晴的兩篇小說無疑讓人感到醒目,因為相對於腐朽卻泛濫成災的現實主義創作主流和南京文壇在慾望化書寫方面的可恥墮落而言,他們的小說提供了一種必要的心靈的高度,或許可以把他們的小說和80年代興起的先鋒寫作看成一種對應和對接:比如對故事性的淡漠和疏離,比如對形式策略的偏愛,比如對語言和世界關係的重新認識,比如對哲學精神的文學化理解等等,即使就在這兩篇形式差異極大的小說中,那種直指虛無和碎片的寫作路徑也頗有投合之處。當然,這樣的類比是粗淺的,小說一旦署名,便成為作者獨一無二的工藝。而《飛鳶》和《黑子活動極大年》中表現出來的奇異素質也有待作者進一步的深化和完整。
在評論部分,敬文東和張桃洲的兩篇文章讓人充滿期待,有趣的是,這兩人的生活經歷和學術背景也很相似,年齡非常靠近,都是國內著名高校的博士,都對當代詩歌的發展表現出極大的批評熱情,敬文東的《六十年代的“懷鄉博》視野宏大,例證豐富,通過考察60年代詩人不約而同在“家鄉”這一深沉意象上的流連,在行政現實和詩意的精神原鄉兩個方面梳理了“鄉村”的書寫意義之後,敬文東總結出60年代詩人返鄉路上的兩種姿態:西川式的和李亞偉式的,前者對在現實變異中越來越模糊的故鄉依然充滿信任,後者面對故鄉時則充滿狂放不羈的遊戲精神,最後,作為另一個60年代人,評論家用辯正的語氣說到:種種跡象表明,粗知故鄉,我們很容易傾向於消滅故鄉,而精研故鄉,我們也會在有限制、有條件的情況下,象海德格爾說過的那樣,回到故鄉的懷抱中去,無論式西川式的,還是李亞偉式的。
張桃洲的《寫一種神經質的魔術》相對集中,通過對詩人朱朱於2000年出版的隨筆集——《暈眩》的細讀分析,作者企圖建立一種新型的散文和詩歌的對應關係,這種關係不再像以往教科書中所表述的那樣緊張,那樣壁壘分明,因為包括布羅茨基、曼德爾施塔姆在內的大量的詩人隨筆表明,散文文體依然存在著可能的詩性空間,它的具體表現即是朱朱所說的散文元素式的功能——描述,而詩歌作為“語言的最高形式”也經常受益於來自散文方面的智慧。比如《暈眩》表現出來的柔軟的、苔蘚式的敘述樣式,給朱朱以後的詩歌寫作帶來極大的改觀。這兩種思維範式在真正的詩人那裡交叉感染,相互推動並最終失去了刻板的文體界限。張桃洲在此既批判了已有的散文觀念對詩性意識的排斥,同時也堅決表明了一種“詩人散文”的存在意義。它既不同於我們這個時代大行其道的言之鑿鑿的實用主義散文,也和空洞無物的囈語式的“詩化散文”毅然告別。
限於篇幅,無法在這篇小文中完成對《南京評論》的全面評價和詳細讀解。畢竟這只是創刊號,對它更為成熟的意見需要時間,但對於文學刊物在質量和數量兩個方面江河日下的當代中國來說,《南京評論》的出現具有不言自明的意義:一方面它代表著持續的困難和邊緣化態度,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方面,這些低矮的南京嗓音在文學的喉嚨里流淌,它確信在一定的儆戒中,繆斯必然領受著孤獨者和先鋒的命運,也必然迎來更廣闊意義上的光榮和希望。
200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