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驗論
先驗論
先驗論出現在19世紀30年代和19世紀40年代。先驗論是一場出現在美國的年輕知識分子中的運動,這場運動強調了人的善良品質、創造力、以及自我發展的潛力。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被認為是先驗論的領導者。先驗論是唯心主義認識論的一種表現形式。同唯物主義反映論根本對立。其認為人的知識是先於感覺經驗、先於社會實踐的東西,它是先天就有的,亦稱先驗主義、唯心主義先驗論。

相關書籍
先驗論割斷人們的認識(理性認識)同感覺經驗與社會實踐的聯繫,必然否認認識同客觀世界的反映與被反映的聯繫,從而把認識變成與生俱來的、主觀自生的,物質不可脫離於物質,無客觀坐標證偽,客觀事物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先驗論是天才論和英雄史觀的理論基礎。

相關書籍
不過,RZ這個重構並非沒有問題。事實上,對先驗論證的邏輯分析是在下面的“元分析”背景中獲得重要性的:作為話語活動的哲學與論證活動的關係是什麼?對於某一種特定的哲學,它所提供的話語所要完成的任務是什麼,這種哲學中的論證又是如何保證任務的完成,或者,保證其話語的有效性的?——哲學是如何通過論證而成為“話語”的?但是,RZ所提供的重構卻不能充分地回答這些問題,甚至會導致錯誤的答案。目的就是嘗試給出一個能夠更好地說明這些問題的重構,並初步確定哲學論證的邏輯重構的一般方法,最後,通過給出先驗哲學的“演進圖”——
檢驗條件(1)+(2)RZ是以一種“論證模式+檢驗條件”的二分結構出現的。其中的檢驗條件是“先驗論證的核心技術”。我們就從這一核心部分開始。

相關書籍
這兩個檢驗條件共有的第一個問題是:表述太弱。也就是說,適用範圍太小。事實上,這兩個條件都可以看作是對“q的解釋”的限定,即,滿足條件(1)則p成為“必要的解釋”,而滿足條件(2)則p會成為“唯一的解釋”,如果同時滿足,則成為“唯一合法的解釋”。但是,這樣的檢驗條件無法應用於,比如,笛卡兒的我思論證。因為在笛卡兒的論證中的那個p,即我思,並不是任何東西的解釋。
同時,在其適用範圍內,它們提供的標準又都太強。比如,考慮康德對知性範疇的先驗演繹[1],它首先就不能滿足條件(1)中的“非p是p的直證”,同時它也不滿足(2)中的“唯一性”要求。
事實上,康德對範疇的先驗演繹目的是要證明範疇是“有用的”。這並不是說,所有的直觀雜多都必須結合到範疇上,而是說,如果某個直觀雜多是通過與範疇結合而成為知識的,那麼它就必然結合到範疇上。而整個證明則是通過統覺的必要性來證明範疇的必要性。它具有這樣的形式[2]:
(1)已知,表象要想成為知識就必須有我思/統覺相伴隨。
(2)因為,我具有同一性。
(3)所以,所有的表象都與同一個我思/統覺相伴隨。
(4)因為,範疇的功能就是統覺。
(5)所以,與範疇的結合對於(已經如此結合了的)表象是必要的
而如果嚴格寫出,它應該具有這樣的形式,
DC[4]:
令是表象領域,知識領域,是統覺,F是範疇集,
(6)已知,[5]
(7)所以,([2])
先驗論
(8)既然,,如果,滿足,那麼,([4])
(9)那麼,,如果,滿足,則有,

笛卡兒
不過,條件(2)並不是排除了康德所有的先驗演繹。事實上,如果把先驗演繹一般地理解為對“必然結合”的證明,那麼統覺/我思也是有先驗演繹的(7)。這也就是上述DC中的(6)和(7)。即非形式表達中的(1)-(3):
(1)已知,知識需要與一個我思的表象伴隨才能成為知識[8]
(2)而且,我具有同一性(唯一性條件)
(3)所以,所有的表象都與同一個我思/統覺相伴隨
這裡,(3)中的兩個定語(“所有的”、“同一個”)是分別從(1)和(2)中獲得的。另外,可以看出,整個證明是內置在DC中的,也就是說,對於知性範疇的先驗論證需要這裡所證明的結論。
論證模式M
RZ中“論證模式”的具體形式如下,
模式M(9):
(10)如果p是q的必要先決條件,

相關書籍
(12)事實上q確實是如此這般的,
(13)並且,不是如此這般的q是不可能想象得出來的,
(14)那麼,p就無疑是q的先決條件,
(15)p就當然是真的。

相關書籍
[10’]已知,p→f(q)(p使得q如此這般)
[11’]又有,q→f(q)(“q不是如此這般是不可想象的”意味著“如果有q則q如此這般”)
[12’]所以,q→p(p是q的先決條件)
這顯然是一個不成立的推論。而就這一推論本身來看,我們會很自然地想到,如果[10’]中是f(q)→p就好了。但是,如果是這樣,那麼整個先驗論證就變成是一個單純的“後件推理”:f(q)→p,q→f(q)├q→p,從邏輯的角度看就沒有任何新穎之處了。另外,如果p是範疇,q是知識,f(q)是“知識具有統一性”,那麼我們在上一節也已經看到,f(q)→p即“如果知識具有統一性那麼它是通過範疇得到的”其實是一個過強的條件。
嚴格說來,上面提到的所有重構工作,還只是在重寫的意義上進行的。也就是用 邏輯語言重新敘述了論證過程。其中還沒有進行任何分析。事實上,對於一個論證的邏輯分析,它的對象應該是從已知命題到求證命題之間的約束條件,即,它要這樣提問:在前提已經給定的條件下,需要滿足什麼樣的條件才能從前提推到結論?
邏輯分析的幾個例子:全域性條件

相關書籍
前面也已經說過,我思/統覺的先驗演繹,是從同一性到表象與統覺結合的必然性的推論。
而保證這一推論成立的條件,正是康德在第16節說的第一句話,“我思必須能夠伴隨所有的表象”。也就是DC中的[1]。我們把這樣的一個條件,稱為“全域性”條件,把[1]稱為“全域性條件[1]”,記作UC1[11]。
事實上,應該注意到,在上一小節當我們對康德的先驗演繹進行重構的時候,對於我思/統覺的先驗論證,我們使用的實際上是量化了的一階謂詞演算,在重構對於範疇的先驗論證時,則在這一基礎上又添加了等詞。與RZ中的M相比(M是普通的一階謂詞演算),這裡的關鍵顯然是“量化”。而全域性條件,恰恰只有在量化的邏輯系統中才能被表達出來。
不過,這個分析仍然只是初步的。因為康德對我思的先驗演繹,仍然不能看作是他的先驗論證的全部內容。為了充分說明這一點,我們先來分析一下笛卡兒的我思論證,作一點準備工作。
初看上去,笛卡兒的我思論證要比康德的先驗演繹簡單的多。也就是,
DA:
如果我思是可懷疑的,那麼我可以就去懷疑我思,而我去懷疑我思也就是在我思,所以我思是不可懷疑的
笛卡兒 但是,這個論證並不是笛卡兒關於我思的完整證明:僅僅證明我思存在,還不能說明它就是笛卡兒需要的那個“阿基米德點”。事實上,這后一部分的工作,是通過《第一哲學沉思錄》的整個前兩個沉思完成的,也就是通過(嘗試性的[12])懷疑排除其它一切存在者。事實上,只有完成了這種排除,笛卡兒才能在第二沉思的後面說“我只是一個在思維的東西”[13]。
在這個意義上,笛卡兒同樣需要對我思進行某種“演繹”,即“權利的證明”。而無論是康德還是笛卡兒,這種權利的證明其實都是對於我思在其先驗體系內部的作用的證明。事實上,DA最多只能說是證明了我思作為“阿基米德點”的候選資格。真正的證明是通過排除“顯示”出來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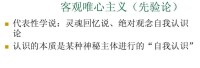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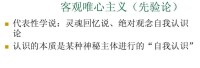
先驗論
通過對笛卡兒的初步分析,自然要對康德提出一個“平行”的問題。如果說先驗演繹的目的只是在於證明某個基點的權利(對於康德來說,這個權利意味著“結合的必然性”),那麼這個基點的候選資格在康德那裡是怎麼出現的?
這就讓又回到了第節。事實上,從的DC中已經看到,我思的先驗演繹([1]-[2])是“嵌”在整個對範疇的先驗演繹中的。換句話說,範疇的先驗演繹是“通過”我思的先驗演繹進行的。但是,這只是在重寫式的重構中出現的順序。如果我們焦點集中在我思/統覺上,那麼,順序正好是反過來的:我思的候選資格是通過範疇提示出來的[14]——正是因為範疇本身不能說明自己的權利,所以才引入了我思/統覺這一“一般聯結的可能性”。不過,真正給出其候選資格的其實還是我思/統覺的同一性。因為康德正是從這一點來說明知性的:“知性無非就是···把給予表象的雜多置於統覺的同一性之下的能力”。它也是一切知性的“至上原理”。
事實上,康德的先驗演繹可以看成是兩個歸入過程。第一個是在我思/統覺的演繹中藉助UC1把表象歸入統覺,第二個,在範疇演繹中把範疇歸入統覺。這裡仍然運用了一個全域性條件即DC中的[3],記為UC2。只不過,這裡的領域不是表象領域Q,而是範疇集F。而這個先驗的領域(即形式領域),實際上正是在這兩次歸入中其意義才真正確定下來的。
這樣,對於康德整個的先驗論證,可以給出這樣一個約束條件式的重構,
LRK:
對於某個給定的領域E,e是E中的任一元素,以及先驗領域F,f是F中的任一元素,如果f對於e滿足全域性的約束條件UC1和UC2,那麼下列推論成立:
如果f和e有關係R,那麼f和e就必然有關係R
對於康德的先驗演繹,上述LRK中的關係R和領域E可以有兩種解釋。一種是把R看成是所謂的“結合”關係,而領域E則是由直觀雜多構成的領域,或者,也可以把R看成是“部分”關係,而把領域E看成是“知識領域”,這時“f和e有關係R”即“f是e的一個部分”[15]。但是,應該注意的是,無論採取哪一種解釋,這裡的關係R都不是任意的,而是由UC1和UC2確定下來的(因為UC1和UC2實際上是關於這個關係的)。在這個意義上,整個推論不僅在成立與否這個方面受它的約束,而且是由它們賦予意義的。
前面的已經說明了,笛卡兒的歸入不是在DA中而是在排除活動中完成的。而這個排除,實際上也是全域性的排除。換句話說,這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全域性條件,只不過是表述形式是否定的而已。這個條件的具體形式可以通過修改RZ中的條件(2)寫成,
UC3:E是整個存在者領域,a是E中唯一具有屬性r的元素。
注意,RZ中的(2)還調用了(1)。而我們的這個表述是“純粹”的全域性條件。另外,與康德的先驗論證結構不同的是,這裡的UC3本身就是一個演繹,而不是保證另外某個(演繹性)推論的約束條件。但是,跟UC1,UC2一樣,在它的表述中也顯示出了歸入點(a)與領域(E)的關係類型。事實上,根據UC3的表述,a是E的元素,換句話說,a和E中的其它元素是並列關係——而不是象UC1,UC2所規定的那樣,f是E中元素的部分或者與E中的元素有“結合”關係。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康德的先驗領域是形式領域,而笛卡兒的不是。換句話說,對於一種先驗哲學來說,它的先驗論證中的全域性條件給出了它的先驗領域的類型。而且,顯然,這個類型是著眼於先驗領域與領域E之間的關係而進行劃分的。
先驗論證的一般模式與先驗論證的先驗性
而事實上,整個先驗哲學所試圖確定的,正是先驗領域T[16]與領域E之間的關係。不妨把後者稱為“基礎領域”。那麼,整個先驗哲學可以用圖表示:
先驗論
這個圖中,所謂的“結論”,就是比如,“所有的表象都有我思/統覺伴隨”,“範疇與直觀雜多的結合是必然的”,“我在的含義是我思”。而這些結論,如上面所述,都是通過先驗論證的那種“歸入法”得到的。而不同的歸入法,卻直接影響到不同先驗哲學如何獲得意義的方式。
先驗論證/先驗論證的一般模式可以寫成下面的形式:
如果a滿足某種全域性條件UC,那麼在UC所規定的意義下,a就與E有滿足某種關係。a稱為歸入點。
不同的先驗哲學,差別則不僅在於歸入點不同,而且在於歸入方式的不同,即UC不同。這正是下一個小節要分析的問題。
事實上,先驗哲學,如果我們從“親緣性”出發,可以畫出這個一個“譜系圖”(從左到右是歷史上的先後關係):
先驗論
而且,事實上,這個“直接程度”的標準,也不同於通常對先驗哲學的分析中所關係的超越問題的標準,也就是所謂“無外化”的標準。如果按照這個標準,關係會是這樣:
先驗論
最簡單來說,圖4是單調的,而圖3明顯不是(“譜系圖”無所謂單調不單調)。換句話說,先驗哲學的“無外化”程度是隨時間單調增加的,但是它的直接性卻遠非如此:所有人都比笛卡兒弱,胡塞爾又另外弱於黑格爾。事實上,所謂直接性,關心的是作為話語更準確的說是作為話語活動的先驗哲學——在這個意義上實際上只是它通過先驗論證所獲得的結論。而超越問題則關心的是作為“物”的先驗領域。最顯著的例子,就是笛卡兒恰恰是以最弱的“無外”程度獲得了最大的直接性。事實上,對於笛卡兒來說,我是與其它存在者並列的存在者。但是,他所獲得的“方法”結論,卻直接應用於所有的人類活動。胡塞爾和康德的問題是他們採取了一個“對象化”的路線,結果先驗領域變成一個純形式的領域。由此獲得的“方法”結論只能應用於形式——範疇只是客觀性(因此對象)的形式,由範疇提供意義說明的“我思/統覺”因此也只局限於形式領域。黑格爾、海德格爾和德里達雖然沒有這個問題。但是他們的先驗領域本身是靠所謂“重演”獲得的。而黑格爾和海德格爾的重演又是一種包含著歷史性的重演。
先驗哲學的活動方式
哲學活動的核心部分,可以說就是論證。它總是通過論證獲得結論,然後通過這些結論去產生“影響”。而對於哲學活動本身的邏輯分析,其要點也正是在於去分析論證活動所得到的結果是如何作為哲學話語而發生作用的。正是在這一點上,對於哲學活動本身的邏輯分析成為哲學史分析的一個趁手的工具。
事實上,正是通過這一方法,趙汀陽才在他的論文中把希臘哲學與(康德的)先驗哲學之間的差別,說成是“確定知識基礎”的方法上的不同。這個一般結論當然是成立的。但是,如果從那種對於哲學活動本身進行邏輯分析的觀點來說,這個結論又不太充分。事實上,這種在確定知識基礎上的方法差異,根源是在於對於“基礎”的不同理解。希臘哲學始終以為關於“什麼是基礎”的答案本身就是有意義的。但是在先驗哲學的活動方式中,確定一個基礎卻是為了得到關於基礎某個論斷,而有意義的,不是“什麼是基礎”,卻恰恰是這個論斷(而這個論斷之所以有意義,則是因為這個“基礎”是作為“歸入點”活動的)。在這個意義上,先驗哲學關於“基礎”的“反思”,已經是一種直接的話語活動(儘管直接性程度有差異),而並非某種為現有的話語活動(比如知識生產活動)提供“權威性”的後勤論證。也正是因為這樣,才能理解自相關性為什麼不是先驗論證的根本特徵。事實上,只有當基礎要成為權威性的根源的時候,它才需要成為“終極”的、不假手別的東西就能自行確立的東西。而對於先驗哲學來說,只要它能證明它的那個“停步”點可以將先驗領域中的其它東西“歸入自身”之中,它就可以完成自己的作用。正是因為如此,先驗論證的重心其實始終是放在“歸入點”與先驗領域中的其它東西之間的關係上的。而先驗哲學,作為一種活動,其實是通過對先驗領域的重新安排而未來一種預演,而這種預演總是超出先驗領域本身而“嵌入”在人的實際活動當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