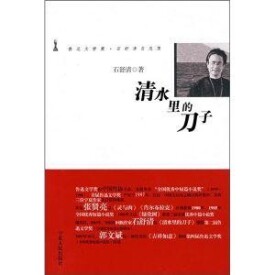共找到3條詞條名為清水裡的刀子的結果 展開
- 石舒清創作的短篇小說
- 2016年王學博執導電影
- 石舒清著小說
清水裡的刀子
石舒清著小說
魯迅文學獎由中國作協主辦,其前身是“全國優秀中短篇小說獎’(197-1996)。首屆魯迅文學獎產生於1997年。在這一中國文壇為之矚目的評獎中,其有三位寧夏作家先後獲得殊榮。《清水裡的刀子》主要內容:石舒清的《清潔的日子》《黃昏》獲第七屆、第八屆《十月》文學獎;小說集《苦土》入選首卷“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並獲第五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駿馬獎;2008年獲莊重文文學獎。馬子善老人是最後一個走出墳院的,在走出墳院門的那一剎那,老人突然覺得自己的鼻腔陡然地一酸,似乎聽到一個蒼老而又穩妥的聲音附在自己的耳畔輕輕說,好啊,老東西,你命大,讓你又逃脫了,那麼就再轉悠上幾天,再轉悠上幾天就回來,這裡才是你的家。
出版社: 寧夏人民出版社; 第1版 (2008年5月1日)
叢書名:魯迅文學獎·寧夏作家自選集·石舒清
平裝: 248頁
正文語種: 簡體中文
開本: 32
ISBN: 9787227037729
條形碼: 9787227037729
商品尺寸: 20.6 x 14.4 x 2 cm
商品重量: 299 g
ASIN: B001BM4LYW
作家張賢亮以《靈與肉》《肖爾布拉克》分別獲得1980年、1985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1985年又以《綠化樹》獲第三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小說獎。繼其後,2001年,年輕的回族作家石舒清以《清水裡的刀子》搞得第二屆魯迅文學獎(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項)。
2007年10月,郭文斌以一部優美的《吉祥如意》棒回第四屆魯迅文學獎(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桂冠。
石舒清的創作多以西海固為生活背景,以短篇小說為主,具有濃郁的伊斯蘭文化精神和藝術思維特色,他的作品沉靜,深邃,從容,神秘,語言精雕細刻,富於張力,他以“對平凡事物的驚異”,表現西部農民的純樸和善良,頑強和寬厚,他的作品里有一種對生命的尊重和對精神信仰的執著。從總體上說,石舒清小說作品中蘊含著一種美——關於人性、關於生命的美。它不是那種壯美,而是一種讓人在接受過程中逐漸浸潤其中的華美——這也可說是石舒清小說的魅力所在。
《清水裡的刀子》主要內容:石舒清的《清潔的日子》《黃昏》獲第七屆、第八屆《十月》文學獎;小說集《苦土》入選首卷“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並獲第五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駿馬獎;2008年獲莊重文文學獎。
《清水裡的刀子》的成功,不僅得力於它的主題的深刻和敏銳,也得力於小說氛圍的營造和故事的推演。通過對特殊情境下人與物微妙心理的探幽考微,將老人馬子善與一頭即將赴死的牛之間的情感敘寫得看似不動聲色,實則驚心動魄。清水裡靜靜地躺著一把寒光閃閃的刀子。作品蒙上了一層濃濃的宗教色彩,它告訴讀者,它既是清潔的,也是神聖的。這篇小說的獲獎以及在文學界產生的一定程度的衝擊力,表明了石舒清在創作上的一次飛躍,給以西海固(固原地區)為創作母土的所謂“苦難文學”以潔凈的精神內涵。
石舒清,擅長寫細微的感受、情緒及心理波動等等,而又不顯瑣碎、沉悶,這主要緣於他個人在體驗上所達到的深度。現實生活中的石舒清,是一個心性極為敏感的人,他能穿行在各種細微的感受中,又有準確表述這種感受的能力。石舒清,的創作多以西海固為生活背景,以短篇小說為主,具有濃郁的伊斯蘭文化精神和藝術思維特色,他的作品沉靜,深邃,從容,神秘,語言精雕細刻,富於張力,他以‘‘對平凡事物的驚異”,表現西部農民的純樸和善良,頑強和寬厚,他的作品里有一種對生命的尊重和對精神信仰的執著。
前言西北大地上的文學綠蔭/馮劍華
序浸潤生命的華美——略談石舒清的小說/白草
果院
清水裡的刀子
娘家
二爺
父親講的故事
圈1皇
黃昏
疙瘩山
風過林
農事詩
賀禧
羊的故事
顏色
家事
貓事
列車上
四先生——記我的老師們
旱年
恩典
虛日
石舒清創作年表
回望和小結/石舒清
20世紀80年代初,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中國大地,大江南北,春風浩蕩,春意盎然,中國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時代,中國的文學同樣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輝煌。一時間佳作迭出,群星璀璨,照亮了文學的天空。1980年,改刊不久的《朔方》文學月刊發表了張賢亮的短篇小說《靈與肉》,旋即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魯迅文學獎的前身),緊接著由著名劇作家李;隹改編、著名導演謝晉拍攝成電影《牧馬人》在全國放映。小說的情節並不複雜,主人公許靈均通過對自己一生艱難曲折道路的回顧,面對出國問題作出毅然抉擇,他決定永遠留在祖國的西北,他要在勞動人民中間繼續汲取豐富的生活養分,從而完成了一次世界觀的升華。老作家丁玲在讀了《靈與肉》之後,非常誠摯地說:“看得出作者大約是一個胸襟開闊而又很能體味人情和人生苦樂的人吧。”作品也因此被稱為“一首愛國主義的讚歌”。
小說《靈與肉》的發表,以及電影《牧馬人》的上演,使人們知道了偏遠的寧夏有一個張賢亮,更有很多人通過張賢亮知道了偏遠的寧夏。上世紀50年代,張賢亮因一首《大風歌》獲咎,歷盡人生的坎坷和磨難,之後更有長達二十餘年的監役和牢獄之苦,真正是在清水裡、血水裡、鹼水裡泡過、浴過、煮過。
清水裡的刀子
和自己在同一面炕上滾了幾十年的女人終於趕在主麻前頭埋掉了。墳院里只不過添了一個新的墳包而已。這樣一種樸素的結局,細想起來,真是驚心動魄。馬子善老人是最後一個走出墳院的,在走出墳院門的那一剎那,老人突然覺得自己的鼻腔陡然地一酸,似乎聽到一個蒼老而又穩妥的聲音附在自己的耳畔輕輕說,好啊,老東西,你命大,讓你又逃脫了,那麼就再轉悠上幾天,再轉悠上幾天就回來,這裡才是你的家。細想想,你在外面轉的時間也不短了,長得很了啊。馬子善老人誠懇地點著頭,是啊是啊,實在是在外面混得太久了,把那樣一個鮮活的嬰兒,把那樣一個強壯的青年混成了目前這副樣子,這使他覺得尷尬而辛酸。馬子善老人記得,他是孩子的時候,村子小得像一個羊圈,墳院遠沒有現在大,但那時候的墳院也顯得空空的。到如今村子已經很大了,墳院幾經突破,成了眼下幾乎和村子一樣大的規模,而且裡面密密麻麻地排列著墳堆,似乎幾個村子的人都死光了都埋在這裡了,但實際上隨著死人越來越多活人也越來越多。馬子善老人就在死人和活人都增多的過程里一天天一天天活到了七十多歲,衰老成了如今這副樣子。馬子善老人有時在水面上看一看自己蒼老的影子覺得不可理解,他真講不清是什麼將自己變化得如此蒼老。墳頭一多,連墳院里也似乎熱鬧了,這使馬子善老人有些淡淡的失意,他喜歡空曠寂寥的墳院,喜歡墳頭很少,大家相互珍惜著經歷永恆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