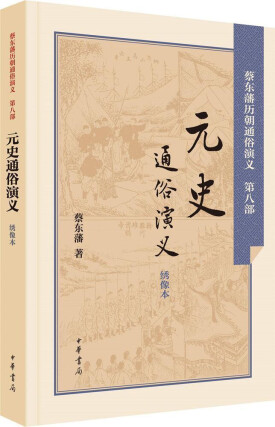通俗文學
通俗文學
通俗文學是大眾文化的一種常見形態,是由文人所創造的、以大眾傳播媒介為載體、按照市場機制運作的、旨在滿足讀者的愉悅性消費的商品性文學。最常見的文類是小說。
“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是指以清末民初大都市工商經濟發展為基礎得以滋長繁榮的,在內容上以傳統心理機製為核心的,在形式上繼承中國古代小說傳統為模式的文人創作或經文人加工再創造的作品,形成了以廣大市民層為主的讀者群,是一種被他們視為精神消費品的,也必然會反映他們的社會。”郭沫若的這個看法一個核心的意思在於,通俗文學的確是在和“市場”的相互關係中逐漸找到自己的歷史位置的。
正如對趙樹理作品的評價在歷史上眾說紛紜一樣,對“通俗文學”這一概念的釐定現在看來也是充滿了內在的矛盾。因為首先,如果說“通俗文學”和市場——如果大家同意,可以包括經濟的市場和觀念的市場——是有巨大關係的,那麼,我們在談論市場的時候,必須注意到市場的多樣性,在現代都市的市民階層之中存在市場,那麼在中國更廣袤的農村社會難道不存在市場嗎?我想當然是有的,趙樹理的存在本身就已經很有力的印證了這個農村文化市場的存在。其次,如果說“通俗文學”是接續了某種中國傳統的,或者承繼了某種傳統的文化趣味的,那麼我想,和程小青等人相比,趙樹理反而是更傳統,更鄉土,更有中國趣味的——他本來就是在毛澤東“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理論指導下寫作的嘛。因此,我理解范先生何以在上述引文中使用“通俗文學”這個概念的時候還冠以“市民”二字。在“通俗文學”和“市民文學”的概念之間容忍某種混淆,把“市民文學”的趣味和標準潛在的化入對“通俗文學”的考察和描述,是我們今天更加難以進入歷史語境了解通俗作品和時代之間關係的一種障礙。相比而言,“市民文學”或者“市民的文學”是更清晰的表明了文學和特定時代特定社會階層的聯繫的。
然而,就是從這樣的矛盾的概念出發,中國的“通俗文學”在今天是獲得了巨大的合法性和確定性。上接唐傳奇、宋話本、明清的章回小說,中承晚清之譴責與黑幕,到張恨水、程小青、李壽民等等,再到是金庸、古龍和瓊瑤,如果算到如今這個“網路時代”,可能就有安妮寶貝之類的作者吧。“通俗文學”成了一個一脈相傳的偉大的傳統,在這個傳統中,形成了自己的古典,自己的過渡和自己的現代化進程。在這個通俗文學的現代化進程當中,趙樹理,包括後來的山藥蛋派,包括後來的黃子平意義上的“革命歷史小說”,我想還應該包括今天像張平這樣的很大眾化的作家,當然就是些異類,更不要說文革時候的東西。對於“八大樣板戲”,范伯群先生的看法是:“總算是用行政手段推行而達到了極致,可以說達到了全民‘大普及’,但這些作品的創作既不符合創作的內在規律,也無法進入民眾的心靈”。
通俗文學就在我們的周圍,最貼近我們的生活,最能迎合大眾的口味,最能反映普通民眾的喜怒哀樂,最能展現人民的審美觀,也最能體現一個民族的人文精神。雖然所有的通俗文學,不一定都能成為名著,但絕大多數的名著,在其誕生之初,都是通俗文學。從這個意義上講,名著是通俗文學這座金字塔的塔尖,高高在上,令讀者敬畏多於親切。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畢竟是少數,能讀懂文學名著的人也是少數。文學名著有其特定的閱讀群體和專家群體,而通俗文學就沒有,它適合各個階層。有的人甚至一輩子都沒讀過一本文學名著,卻可能看了不少通俗文學的作品。我們常常看到有人在閑暇時沏一杯茶,捧一卷書,悠閑愜意的閱讀。讀的什麼書呢?武俠、言情、偵探、科幻,甚至是連環畫。這就是現實生活中大多數人的閱讀。還有一種現象非常有趣。文學名著的影響力往往不是來自作品本身,而是得益於其他藝術形式對名著的通俗化演繹。譬如,正是評書、曲藝、戲劇等通俗化的藝術形式讓《三國》、《水滸》、《紅樓夢》、《西遊記》這樣的古典文學名著走入千家萬戶,貼近尋常百姓。而大部分評書、曲藝、戲劇也是通俗文學的一部分。這不僅是二者定位不同的必然,更為歷史和現實所證明,是不爭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