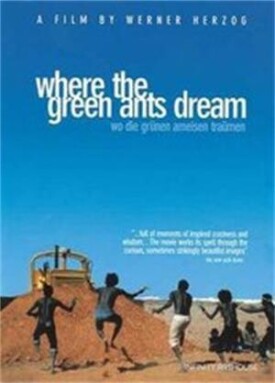綠螞蟻做夢的地方
綠螞蟻做夢的地方
《綠螞蟻做夢的地方》是由沃納·赫爾佐格執導,布魯斯·斯賓斯主演的劇情電影,該片於1984年8月31日在西德上映。導演很用心地告訴觀眾:對土著領地的侵犯,導致對土著文化的侵害,最終會使它消亡。然而導演也沒有提出解決辦法,Hackett最後選擇在土堆間找個破房子住下來,不知明天可以做些什麼。工業發展與環境保護(含地理文化的保護)的衝突是西方電影經常涉及的主題,與其它同類電影中現代社會內部的對立不同,本片是文明社會VS.原始土著,顯然,土著在法律訴訟上難以抗衡。故事以土著的悲傷結束,預告著他們的文化與生存方式只能一步一步消失在歷史中。
電影講述某礦業公司在澳大利亞內陸沙地採礦,在一次堪探過程中被當地土著用靜坐方式阻止。土著說,腳下是綠螞蟻做夢的地方,如果吵醒了它們,它們就會出來毀滅人類。採礦公司當然如聽天書,然而土著視死如歸的信仰力量不可小視,於是公司高層邀請土著代表進城談判,許諾給土著利益,結果土著代表喜歡上了一架綠色的小型運輸機。於是公司買下飛機,並替土著修建了一條飛機跑道。飛機飛來了,為防止被土著點火引燃,汽油被抽走,只留了一點。飛機只是公司示好的禮物,官司還是訴至聯邦法院。在法庭上雖然法官能夠尊重土著的文化,聽取他們講述的傳說,然而裁判依據是英聯邦法律,土著被判敗訴。沉默的土著坐在跑道邊,其中兩個土著人坐上飛機,竟然起動飛機,飛翔而後消失在地平線。警察來尋找,難以找到,有兩個異邦土著來訪,以歌為話,說一隻綠螞蟻飛到他們那裡,結果翅膀斷了。公司地質學家Lance Hackett在整個事件過程中心態發生變化,最後決定離開公司,在沙漠里成為一個環保主義者。電影至此結束。
本片曾獲1984年戛納電影節最佳影片獎的提名。導演是德國著名導演,也是本片編劇之一。
摺疊
製作公司:Werner Herzog Filmproduktion[德國]Zweites Deutsches Fernsehen (ZDF)[德國]
發行公司:New Vision Films[澳大利亞](2005) (Germany) (DVD)Globo Vídeo[巴西](Brazil) (VHS)Home Cinema Group[澳大利亞](Brazil) (VHS)Orion Classics[美國](1985) (USA)VCL Communications GmbH[德國](1985) (USA)人造眼[英國](UK)Kinowelt Home Entertainment[德國](2005) (Germany) (DVD)
西德West Germany1984年8月31日加拿大Canada1984年9月7日......(Toronto Film Festival)丹麥Denmark1984年9月14日英國UK1984年10月18日澳大利亞Australia1985年美國USA1985年1月......(Sundance Film Festival)美國USA1985年2月8日
電影中的法律
本片的法庭戲很不錯,展現了澳大利亞法庭的風貌。聯邦法院大/法官知識淵博,不怒而威。作為控方的土著居民雖然因為出庭身著筆挺西服,卻還是象怪物出現在不適當的場合。其中一個叫“啞巴”的人說話了,卻沒有人能聽懂,因為他是自己部落里最後一個人,這世上已經無人能聽懂他的話。這一種強烈的隔閡,暴露了這一場訴訟的實質,不是權利的衝突,乃是文化的衝突。雖然法官尊重土著文化,然而法律卻沒有能力解決文化衝突。
法庭上土著舉證時,要求所有法庭觀眾迴避,理由是他們拿出的是部落的“聖物”,看的人多了“會導致社會的毀滅”,這雖然是有趣的一幕,卻也是讓人百感交集的一幕:土著們看向法庭的眼神,總是這樣陌生與隔離,而他們鄭重其事的舉動,無法被現代社會的法庭理解。
我想,要在法律上保護土著文化,就要在立法上有其規定,而土著部落在立法會議上的代言人會是誰呢?他們相信在古樹下夢到孩子就能得子,他們相信綠螞蟻飛向的東方就是聖地,他們如何在立法會議上做這種表達?
摺疊
戛納電影節 Cannes Film Festival第37屆(1984)提名
·主競賽單元-金棕櫚獎沃納·赫爾佐格 Werner Herzog
電影開始時是一段龍捲風的錄相,這龍捲風與電影故事所在地沒有關係,顯然是導演的心思。在澳大利亞廣袤的內陸沙地上,一個又一個連綿不絕的土堆展示著採礦公司的工作成效。坐在土堆中間的土著居民表情嚴肅,其中一位吹著一個長木管,發出快節奏的“嗚”音。
導演很同情土著,用電影詳細地記錄了他們。電影中參與解決問題的地質學家Hackett在與土著的交往中慢慢理解他們的文化與風俗,最後成為土著的支持者,可以看成是導演自己的代言人。與此同時,電影也嘲諷了現代文明,所用的道具是一架總是出問題的電梯。
綠螞蟻做夢的地方
王書亞
寫下這個題目,想起德國電影大師赫爾佐格的同名電影。在澳洲廣袤的內陸,土著中的釘子戶,用一個美麗的傳說對抗礦業公司的開發。他們說,腳下是綠螞蟻做夢的地方,如果驚醒它們,鋪天蓋地地出來,就會毀掉這裡的生活。你可以理解為一種革命理論的暗示。那些像綠螞蟻一樣比塵土更低的人們,不要過分地驚動。我見過重慶的釘子戶,也在堪培拉見過支搭帳篷的土著上訪戶,這些被驚醒的綠螞蟻,在國會外的空地上安營紮寨,一住就是幾十年。
《箴言書》說,“螞蟻沒有元帥,沒有君王”,但不等於沒有夢想。很多年前,我讀到一位台灣詩人的《螞蟻螞蟻》,心中暗自喟嘆。以後張楚將它大事宣揚地唱了出來。那時我就和《末代獨裁》中的蘇格蘭醫生尼古拉斯一樣,剛從大學畢業,懷著螞蟻的夢想,在街頭和朋友一起唱這首歌。其實這電影不是關於君王,而是關於螞蟻。在某一類世界,你不是君王就是蟻民,好像好萊塢的動畫大片《蟻兵正傳》,以螞蟻的世界來表現對獨裁的反抗。
蘇格蘭是長老教會根深蒂固的地方,今天的我會覺得,活在缺乏道德感的時代,是多麼可憐。但對當時的尼古拉斯,循規蹈矩的世界,就等於對個人夢想的死刑宣判。影片開始,一群畢業男女一路狂奔,脫去畢業禮服,跳入水中。尼古拉斯和父母道晚安后,躺在床上歇斯底里地叫喊。他起身轉動地球儀,說轉到哪裡我就去哪裡。結果轉到加拿大。可如果能去加拿大,為什麼不能待在蘇格蘭。尼古拉斯要的是另一個世界,另一個夢想。於是他繼續轉到他想要的地方,一個像烏托邦的地名,叫烏干達。
如果這部電影是描寫烏干達軍事獨裁者阿明,它遠沒有1974年那部紀錄片精彩。我手裡有歐洲標準公司幾年前修復的版本。當時阿明邀請一位法國導演,希望向全世界展現他親和的一面。阿明耐心對著鏡頭解釋軍隊的操練,頗浪漫地在自然保護區行舟,聲稱大象是自由的象徵,甚至破例讓導演拍攝一次完整的內閣會議。結果這位紀錄片導演,我應該記下他的名字,巴貝特·施羅德,以貌似順從的態度配合阿明,卻以新聞人的良知和智慧,剪出一部電影史上罕見的獨裁者自我扮演的紀錄片。
阿明的扮演者惠特克說,他至少看這部紀錄片不下100遍。他的表演也為他贏得奧斯卡影帝小金人。但和紀錄片相比,我的沮喪還是難以言傳。《末代獨裁》中的阿明形象,鮮明但是刻意,複雜卻嫌單薄。當我們的世界被虛構文本描敘時,我們就差不多活在另一個世界。這往往是我們想逃離的理由,也是尼古拉斯遠離真實的蘇格蘭,嚮往虛擬的烏干達的渴望。
當他意外地成為獨裁者的私人醫生,坐上總統專車在鄉間賓士。烏干達孩子們在後面一路奔跑,一路揮手。尼古拉斯從此進入一個人物扮演遊戲,他忍不住想象自己是一個總統,向著窗外的螞蟻們揮手,就像阿明,非要想象自己是蘇格蘭的國王。
蘇格蘭的年輕人夢想烏干達,烏干達的獨裁者夢想蘇格蘭。這部電影不僅關於政治,實在關於人類的夢想。前年我在重慶山區,還遇見這一幕的後現代版。盤山公路上的小學生一看見小汽車,就三五成行,退到路邊鞠躬敬禮。我想,一定有一些渴望搖下玻璃向他們揮手的人,叫他們如此,叫他們分辨公共汽車和小汽車。因為一些人的夢想就像小汽車,另一些人的夢想就像公共汽車。
電影中的阿明一身戎裝,紀錄片中的阿明卻常常西服領帶,他粗野、蠻橫,卻也幽默,甚至有幾分靦腆。他一面是殺氣,一面是傻氣。一面精明,一面荒唐。在內閣會議上,他說,你去任何國家,都會發現每個人都愛他們的領袖。我們也要這樣。他說,如果你去其他非洲國家,會發現他們的婦女每天早上5點起來上班,我們也要這樣。他批評外長的手腕太弱。幾個星期後,人們在河裡發現了外長的屍首。阿明告訴人民以色列人會在河裡下毒,不結盟國家會議上,他引用希特勒的文件批評猶太人。他趕走所有亞洲人,沒收他們的財產。他針對戈蘭高地的軍事演習就像一場過家家。阿明在電視上告訴人民,他的行為是上帝的旨意,反對他的人和事,上帝告訴他,他一般會在幾天前就知道。這話令人想起納粹的宗教事務部部長漢斯·凱爾,他對主教們說,“國家社會主義是上帝的旨意,黨就代表了真正的基督教。”
從這個人身上,你能窺見20世紀某一類獨裁者的性情,充滿詩人或精神病人的狂想氣質。看電影的,會想起韓國影片《孝子洞的理髮師》,一個成為總統理髮師的普通人,對國家的一切都充滿了信任。一個溫馨故事折射韓國數十年的政治變遷。
“伴君如伴虎”,或者是對這部電影的東方專制主義式的解讀。但我始終認為,電影的真正主角是年輕的尼古拉斯,這部電影的真正悲劇從畢業生們脫光衣服、扔掉博士帽的那一刻就開始了。當尼古拉斯見識到阿明的殘暴決心逃離時,這部電影的主題,就是從虛擬的烏干達回到循規蹈矩的蘇格蘭。這部電影關於夢想,關於夢想是如何靠不住。當尼古拉斯的地球儀轉到加拿大,他不甘心;轉到烏干達,他就放下一切去了。
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挨近君王,但無數螞蟻的夢想,從古至今,都和一個遙遠的君王的意象有關。北師大附中的女校長卞仲耘,是“文革”中第一個被學生打死的老師。幾十年後,一位當年的女生在一部紀錄片里,回憶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場面。她說,我一直在想,如果當時我上了天安門,我和領袖握了手,我會不會更積極地投入那一場運動,我可不可能參與對卞老師的毆打?
綠螞蟻沒有做夢的地方,它們一旦做夢,甚至和獨裁者一樣危險。尼古拉斯回去蘇格蘭,夢醒之後,我們回去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