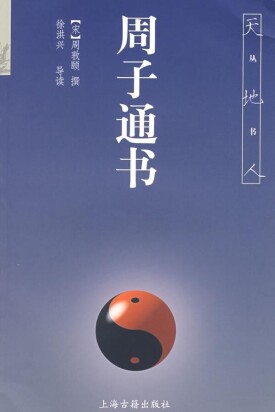通書
宋代理學家周敦頤創作的哲學著作
《通徠書》是宋代理學家周敦頤創作的哲學著作,後人合編為《周子全書》。
周敦頤(1017-1073),原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敦頤,字茂叔,晚年定居廬山蓮花峰下,以家鄉營道之水名"濂溪"命名堂前的小溪和書堂,故學者習稱濂溪先生,北宋道州營道(今湖南道縣)人。北宋儒家學者,哲學家,理學的開創者之一,宋明理學中之"濂學"即由周敦頤而得名的。
《通書·誠上第一》:“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通書·誠下第二》:“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通書·誠幾德第三》:“誠無為,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通書·聖第四》:“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 人”。
《通書·慎動第五》:“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
《通書·道第六》:“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為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
《通書·師第七》:“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干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后覺,暗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通書·幸第八》:“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通書·思第九》:《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
《通書·志第十》: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通書·順化第十一》: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跡、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眾,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通書·治第十二》: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眾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通書·禮樂第十三》: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后。
《通書·務實第十四》: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通書·愛敬第十五》: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眾善,無弗愛且敬焉。
《通書·動靜第十六》: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辟兮,其無窮兮。
《通書·樂上第十七》: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燥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慾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通書·樂中第十八》: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通書·樂下第十九》: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艷辭之化也,亦然。
《通書·聖學第二十》:“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通書·公明第二十一》: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通書·理性命第二十二》:闕彰闕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一實為萬;萬一各正,大小有定。
《通書·顏子第二十三》: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通書·師友上第二十四》: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通書·師友下第二十五》: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通書·過第二十六》: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通書·勢第二十七章》: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
《通書·文辭第二十八》: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通書·聖蘊第二十九》: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通書·精蘊第三十》: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通書·乾損益動第三十一》: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通書·家人睽復無妄第三十二》:冶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厘降二女於媯汭,舜可襌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通書·富貴第三十三》: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通書·陋第三十四》: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通書·擬議第三十五》: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通書·刑第三十六》: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冶。情偽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通書·公第三十七》: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通書·孔子上第三十八》:《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通書·孔子下第三十九》: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通書·蒙艮第四十》: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慎哉,其惟時中乎!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周敦頤的《通書》,據朱熹說共有四十一章,主要的是講所謂“人極”。第一章、第二章標題為《誠上》、《誠下》。第一章說:“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通書》下文解釋《周易》的《無妄》卦說,“無妄”就是沒有虛假,就是實實在在,就是真實,宇宙間的事物及其演化和規律,都是實實在在地如此,並沒有一點虛偽,這就是“無妄”。這樣說本來是一個大實話。“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這幾句話出自《周易》《乾》卦的《文言》,周敦頤引以泛指宇宙間事物的演化及其規律。意思就是說,在這個演化過程開始的時候(其實沒有這個時候),“誠”就開始了。在事物生成長大以後,“誠”也就確立了。這個程序和過程,就是“至善”。“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這幾句話出自《周易·繫辭》,周敦頤引以說明上邊所說的意思。“一陰一陽之為道”指的是宇宙事物的演化及其規律。“繼之者善也”就是說,這個演化的過程就是“至善”。“成之者性也”是說,在這個演化的過程中,每一種事物都成為某一種事物,這就是這種事物的“性”。“元亨利貞”是《周易》《乾》卦的卦辭。周敦頤在這裡把“元亨利貞”作為一個事物的變化過程的四個階段。概括一點說,是兩個階段,“元亨”指的是事物的發展的階段,也就是“誠之通”。“利貞”指的是事物的成熟階段,也就是“誠之復”。
《通書》的第一章開頭就說:“誠者,聖人之本”。第二章講聖人,推廣這個意思。第二章開始所說:“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第一章的第一句說:“誠者聖人之本”。第二章第一句說:“聖,誠而已矣”,這是接著第一章第一句說的。有了誠為本,一切道德原則(“五常”)以及一切道德行為(“百行”),都跟著有了。在自然界中,有事物的生長變化及其規律,它們都是真實的。這個說法是正確的,也是很容易明白的。周敦頤認為這就是“天地之德”,就是“誠”。推而至於社會中的一切道德規則和一切道德行為,如果沒有“誠”為其根本,不是出於誠而是出於虛偽,那都是不道德的。人也是宇宙間的一物,本來也是應該有誠這種品質的,這就是所謂性善。可是事實上,人又往往不能保持這種品質,這是因為“邪暗塞也”。“邪暗”的中心就是私心。人往往為自己的利益而有不道德的思想和行為,這就是私心雜念。私心雜念就是“邪暗”的主要內容。如果能夠克服私心雜念,那就是“誠”,那就沒有事了。這樣說是很容易的,然而實行起來就比較困難。但是如果有決心,困難也是可以克服的。“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是孔子的話。(《論語·顏淵》)“克己”就是去掉私心雜念,周敦頤引用這句話以說明所謂困難也並不是難以克服的。
《通書》的第二十章說明了這種意思。它說:“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所謂無欲就是無私心雜念,道學家們稱私心雜念為欲。欲的主要特點就是私,私的主要表現就是自私自利,道學家簡稱之為利。私的對立面就是公,利的對立面就是義。道學家們認為,義利之辨就是公私之分。無欲就是沒有私心雜念,這就叫“靜虛”。個人如果沒有私心雜念,他的所作所為就是公。因為他們沒有自私自利的考慮,沒有患得患失的私心,他就能作起事來一往直前,這就叫“動直”。沒有私心雜念,他們看事情就沒有偏見,這就叫“靜虛則明”。因為“明”,所以對於是非就看得清楚,這就叫“明則通”。人如果沒有私心雜念,對於是非看得清楚,他們就能夠一往直前地照著“是”的方向走,這就叫作“直則公”。既然是公,所以他的行為必定對於社會的廣大群眾有利,這就叫“公則溥”。
司馬光的學生劉安世說:他跟司馬光五年,得了一個“誠”字。司馬光又教他,求誠要從不說謊(“不妄語”)入手。劉安世說:他初以為這很容易,但自己一反省,才知道自己的言行不符之處很多。用了七年工夫,才作到“不妄語”。他說:“自此言行一致,表裡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他又說:司馬光對他說,“只是一個誠字,更撲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入道。天人無兩個道理。”他還說:“溫公(司馬光)……因舉左右手顧之笑曰:‘只為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疑當作克)之,及其成功一也,。”(《元城道護錄》,轉引自《宋元學案》卷二十)周敦頤講誠,並不是來源於司馬光,但是,劉安世的這兩段話,可以作為了解周敦頤的參考。特別是他所說的“言行一致,表裡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那種精神境界,可以作為“靜虛動直”的註解。
《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就是未誠而求誠,人也是宇宙間之物,應該本來是誠的,但只因有個軀殼,有些事是從軀殼發生的,這就要自私,就有個“己”,就要有“欲”。若能克去己私,就可以得到像劉安世所說的那種精神境界。
因為人有個軀殼,不免受其影響,所以人的思想和行動即使不是邪惡的,也難免因太過或不及而有不恰當之處。《通書》第三章說:“誠無為,幾善惡”。“無為”並不是沒有動作,而是沒有私,照周敦頤所說的,自然界的發展變化都有誠的品質。發展變化就是動作,但是,自然界不考慮這些動作對於自己有什麼後果,這就是“誠無為”。人也是自然界之物,如果不考慮自己的動作對於自己有什麼後果,而一往直前,這就是“誠”,也就是“無為”。一有考慮那就叫“幾”,“幾”可以是善也可以是惡。如果他考慮到這樣做與他自己有利,他就做下去,與他自己有害他就不做,這個“幾”就是惡了。如果他不顧自己的利害,認為這樣做雖然與他自己有害,但是與社會有利,他就做,雖然與自己有利但是與社會有害,他就不做,這個“幾”就是善。《周易·繫辭》說:“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幾”是一個行動的開始,所以說是“動之微”。雖然是個動之微,但是這個行動的吉凶就預先顯示出來了。這個吉凶不一定指禍福。如果行動是善的,雖得禍也是吉;如果行動是惡的,雖得福,也是凶。
《通書》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干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第七章)《繫辭》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就是說,貫穿於天、地、人三者的規律,都是兩個矛盾著的對立面的統一。人是天地間之物,所以他的本性之中也有剛柔。剛柔都可以太過,那就成為惡;若不太過,恰到好處,那就是善。周敦頤說:“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通書》第二十二章)就是說,剛柔都必須恰到好處,沒有太過也沒有不及,這就是中,也就是正。“仁”就是恰到好處的柔,“義”就是恰到好處的剛。所以他在《太極圖說》中說:“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人極”就是作人的標準。
照這樣分析起來,周敦頤對於惡的來源有兩種解釋,一種是人有私慾,一種是剛柔失於偏,這兩種說法周敦頤沒有把它們統一起來。也許他認為,事實上就是如此,就是有兩種的惡。對於前一種惡,他認為應該以“公”克制之,他說:“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通書》第三十七章)對於后一種的惡,他認為應該以“中”克制之。
周敦頤的《通書》所講的主要內容也是“人極”,而且講得比《太極圖說》更詳細,可注意的是周敦頤在《通書》中不突出“靜”,而突出“誠”,“誠”是“聖人之本”,也是“性命之源”。照《通書》所講的“聖人”所立的“人極”就不是“中正仁義而主靜”,而是“中正仁義而主誠”。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很重要。這說明《通書》已經脫離了道家和道教的影響。這是周敦頤哲學思想的一個大發展。
《通書》的表述將“誠”理解為由核心和邊緣組成的一個意義結構。須說明的是,在下文對它的闡發中還要結合先秦儒家的一些典籍,這是由於《通書》的內容過於簡短,其思想脈絡往往隱藏在這些早期儒家典籍中。
第一、“誠”的核心意義是“無妄”,即真實客觀。不過,這裡的“真實客觀”至少是在兩個層面上使用,一是在本體—宇宙論層面,它指的是事物“與生俱來”的“真實客觀”屬性,即事物“是其所是”的本性。這也就是《通書》“‘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的真實涵義,也是《中庸》中“誠者,天之道也”、“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的基本涵義,也是《荀子》“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的主要意思。二是在人的認知—品質層面,它指的是對事物“真實客觀”屬性的肯認和持守,即在人的心靈中“是其所是”、並反對“是其不是”,而且,這種肯認和持守還內化為人的一種穩定心靈素質。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誠信”的意思,也是《通書》中“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的意思,也是《中庸》中“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的意思。第二、在上一層意思的基礎之上,“誠”又衍生出“靜定”的意思。在古人看來,只有我們的心靈處於“靜定”狀態,才能更好地體察和認知天地萬物尤其是“道”“是其所是”的樣子。這也就是《通書》所謂“無為”、“寂然不動”、“誠精故明”的意思,也是《荀子》中“虛壹而靜”、“大清明”的意思,也是《大學》中“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的意思,同時也和《中庸》中“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的意思有接近之處。第三,在“誠”的“真”和“靜”兩層含義的基礎上,它又衍生出兩層意思。一是將它視作事物其它功能和屬性的基礎。比如,《通書》說:“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孟子》中也說:“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這裡便將“誠”視作運動、變化的前提。荀子說:“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則是將“誠”視作化生的前提。二是將它視作其它各種道德基礎的意思,這就是《通書》所謂“誠,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的內涵,也是宋明諸儒將“誠”視為仁、義、禮、智四德之本的意思,而荀子所說的“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它事矣,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中也已經暗含了這一意思。從以上所論我們可以看出,周敦頤實際上是將先秦儒學重要典籍中有關“誠”的思想予以總結、融通、凝鍊,成為他自己建構的心靈世界中最為核心的一種境界,也是他理解的天地萬物的一種根本狀態。從其整個宇宙—心靈架構來看,“誠”處於形上的位置,具有某種本體和超越的色彩。
在“誠”的境界和狀態的基礎上,周敦頤又向上、下兩個方向延伸出其他的境界和狀態,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神”和“幾”兩種狀態。所謂“神”,指的是基於“誠”但又高於“誠”的功能和狀態,它的最大特點是常人“不可察知”、“不可思議”卻又極為奇妙偉大。同於“誠”,“神”也既表現在外內兩個方面:在宇宙—本體層面,它指的是自然或道神奇莫測卻又能不露痕迹地化生、影響萬物的功能,這在《通書》中被描述為“大順大化,不見其跡,莫知其然”、“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在人的心靈層面上,它指的是聖人感知自然和道的運行且毫無滯礙地自覺遵行並使普通百姓遵行的神秘能力,這種能力在《通書》中被描述為“感而遂通”、“神應故妙”、“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如果“誠”的狀態向下、向凡俗的方向延伸或演變則可以成為“幾”,它是一種事物的“萌芽”或“起始”狀態,也是人的心靈之中具體情感和意志的“萌芽”和“起始”狀態,它可以演變成為善,也可以演變成為惡,其形象特點是似有若無、不易為人察知。這種狀態在《通書》中的描述是“誠無為,幾善惡”、“幾微故幽”、“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而《通書》另一處說“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其中的“幾”也大致符合上述意思。從周敦頤的整個宇宙—心靈架構來看,“神”和“幾”也大致處於形上位置,或者說具有本體和超越色彩。
須說明的是,中國傳統學術在使用概念時往往沒有經過細密分析和嚴格界定,常常有些概念在形上和形下、本體和現象之間混合運用,周敦頤思想中的“誠”、“神”、“幾”也是這樣。但是,就主要方面而論,這三個概念應該歸屬於形上和本體層面,這是由於它們明顯具有超越事物的具體狀態和人的現實生活的特徵。有趣的是,這三種形上概念又被周敦頤表述成聖賢境界,《通書》中說得相當明白:“誠、神、幾,曰聖人”。這種狀況的真實思想史含義在於,宋初儒學將聖賢境界和形上層面混融而觀,也可以說,尚沒有出現明確分化二者的理論認知。
在周敦頤看來,雖然“幾”的狀態時仍然屬於聖賢境界或形上境界,但它已經具備了走入形下的可能,如果它進一步向凡俗方向發展則會表現出各種種樣的善惡情狀來。由於《通書》行文相當精簡,我們能尋到的關於善惡情狀的材料很少,其中最為重要的一條是:“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干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在此,周敦頤將善、惡分別劃分為剛、柔兩個類型。“剛”的“善”指的是正直、決斷之類品格,“剛”的“惡”指的是兇猛、強暴之類品性;“柔”的“善”指的是慈善、柔順等品格,“柔的”的“惡”指的是懦弱、陰邪等品性。在當時的人類認知條件下,周敦頤對人之善惡的劃分是相當清晰且有一定深度的,比較起以前儒家的“性三品”說向前邁了一步。而這無疑和他的社會閱歷尤其是長期聽訟斷案的經歷有關,應該說是他人生經驗和知識資源的一種總結。需要說明的是,周敦頤並不認為“善”是一種理想的心靈境界,剛柔善惡中間的“中”境界才是他最為贊成的。這種“中”大概是最為接近“誠”的一種形下狀態。那麼,如何才能達到這種狀態呢?《通書》中說:“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也就是通過一點一滴地壓抑自己的慾望和怒氣、改正自己的錯誤來一點點地修養自己,最後才能達到“中”和“誠”的境界。
可以看出,在《通書》中周敦頤構設了一個心靈世界,這個世界分成兩個部分:一是誠、神、幾組成的形上境界,一是剛、柔、善、惡、中組成的形下狀態。在他的心目中,後者來自於或基於前者,是前者向常人心靈的延伸或流溢。由於他極為看重前者,將前者理解為理想的心靈境界,那麼,從後者恢復到前者或趨向前者就成為他所認為的一個應然甚至必然的人生程序,而這也成為宋明諸儒理解心靈世界的一個基本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