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找到2條詞條名為西西弗的神話的結果 展開
- 加繆創作散文
- 加繆創作散文集
西西弗的神話
加繆創作散文集
《西西弗的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是法國作家阿爾貝·加繆一部哲學隨筆集。這是一部哲學隨筆集,原書的副題是“論荒誕”。阿爾貝·加繆,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這本加繆隨筆集彙集了作家的四篇文章——《荒誕推理》、《荒誕人》、《荒誕創作》和《西西弗的神話》。《西西弗的神話》篇幅最短,但卻是一篇提綱挈領、體現加繆思想要義的文章。他指出:“西西弗斯是荒誕英雄。既出於他的激情,也出於他的困苦。”“在他離開山頂的每個瞬息,在他漸漸潛入諸神巢穴的每分每秒,他超越了自己的命運。他比他推的石頭更堅強。”其他幾篇長文,實際上是從各個側面充分闡述和充實了加繆的這些思想。
哲學散文集《西西弗的神話》是加繆存在主義思想的集中體現。在這部散文集中,作家集中處理了死亡與反抗、幸福與悲劇、存在與拯救、人生的荒謬與荒誕性等一系列重要哲學命題。其中,西西弗這一古老的神話形象是整部隨筆集的核心所在。
《西西弗神話》(以下簡稱神話)分為三個部分:荒誕推理、荒誕人和荒誕創作。荒誕推理”圍繞“荒誕感”、荒誕”展開,並把“荒誕推理”作為一種方法直接運用到“荒誕人”和“荒誕創作”這兩部分中去;“荒誕人”把荒誕概念具體化、形象化加以分析,並逐步推入和拉進荒誕概念的內核;“荒誕創作”更多地體現了神話的文學性質,而且帶有很強的文學評論性,從“荒誕”角度對很多文學作品進行了獨到的分析。全篇從“荒誕”入手,以荒誕與自殺、荒誕與虛無、荒誕與希望作為切入點,經過肯定一否定-再肯定的循環過程,不斷完善有關“荒誕”概念的論述,最後回歸到“西西弗神話”。
【譯序】
【前言】
荒謬的理論
荒謬與自殺
荒謬的牆
哲學自殺
荒謬的自由
荒謬者
唐璜主義
戲劇
征服
荒謬的創造
哲學與虛構
基連洛夫
短暫的創作
西西弗的神話
附錄
弗蘭茲·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和荒謬
阿爾及利亞的夏天
致雅克·歐爾貢
彌諾陶洛斯或停駐奧蘭
致皮埃爾·加林多
街道
奧蘭的沙漠
運動
紀念碑
阿里阿德涅的石頭
海倫的流亡
回到提帕薩
藝術家與他的時代
……
西西弗的神話
阿爾貝·加繆
諸神處罰西西弗不停地把一塊巨石推上山頂,而石頭由於自身的重量又滾下山去,諸神認為再也沒有比進行這種無效無望的勞動更為嚴厲的懲罰了。
荷馬說,西西弗是最終要死的人中最聰明最謹慎的人。但另有傳說說他屈從於強盜生涯。我看不出其中有什麼矛盾。各種說法的分歧在於是否要賦予這地獄中的無效勞動者的行為動機以價值。人們首先是以某種輕率的態度把他與諸神放在一起進行譴責,並曆數他們的隱私。阿索玻斯的女兒埃癸娜被朱庇特劫走。父親對女兒的失蹤大為震驚並且怪罪於西西弗,深知內情的西西弗對阿索玻斯說,他可以告訴他女兒的消息,但必須以給柯蘭特城堡供水為條件,他寧願得到水的聖浴,而不是天火雷電。他因此被罰下地獄,荷馬告訴我們西西弗曾經扼往過死神的喉嚨。普洛托忍受不了地獄王國的荒涼寂寞,他催促戰神把死神從其戰勝者手中解放出來。
還有人說,西西弗在臨死前冒失地要檢驗他妻子對他的愛情。他命令她把他的屍體扔在廣場中央。不舉行任何儀式。於是西西弗重墮地獄。他在地獄里對那恣意踐踏人類之愛的行徑十分憤慨。她獲得普洛托的允諾重返人間以懲罰他的妻子。但當他又一次看到這大地的面貌,重新領略流水、陽光的撫愛,重新觸摸那火熱的石頭、寬闊的大海的時候,他就再也不願回到陰森的地獄中去了。冥王的詔令、氣憤和警告都無濟於事。他又在地球上生活了多年,面對起伏的山巒,奔騰的大海和大地的微笑他又生活了多年。諸神於是進行干涉。墨丘利跑來揪住這冒犯者的領子,把他從歡樂的生活中拉了出來,強行把他重新投入地獄,在那裡,為懲罰他而設的巨石已準備就緒。
我們已經明白:西西弗是個荒謬的英雄。他之所以是荒謬的英雄,還因為他的激情和他所經受的磨難。他藐視神明,仇恨死亡,對生活充滿激情,這必然使他受到難以用言語盡述的非人折磨:他以自己的整個身心致力於一種沒有效果的事業。而這是為了對大地的無限熱愛必須付出的代價。人們並沒有談到西西弗在地獄里的情況。創造這些神話是為了讓人的想象使西西弗的形象栩栩如生。在西西弗身上,我們只能看到這樣一幅圖畫:一個緊張的身體千百次地重複一個動作:搬動巨石,滾動它並把它推至山頂;我們看到的是一張痛苦扭曲的臉,看到的是緊貼在巨石上的面頰,那落滿泥士、抖動的肩膀,沾滿泥士的雙腳,完全僵直的胳膊,以及那堅實的滿是泥士的人的雙手。經過被渺渺空間和永恆的時間限制著的努力之後,目的就達到了。西西弗於是看到巨石在幾秒鐘內又向著下面的世界滾下,而他則必須把這巨石重新推向山頂。他於是又向山下走去。
正是因為這種回復、停歇,我對西西弗產生了興趣。這一張飽經磨難近似石頭般堅硬的面孔已經自己化成了石頭!我看到這個人以沉重而均勻的腳步走向那無盡的苦難。這個時刻就像一次呼吸那樣短促,它的到來與西西弗的不幸一樣是確定無疑的,這個時刻就是意識的時刻。在每一個這樣的時刻中,他離開山頂並且逐漸地深入到諸神的巢穴中去,他超出了他自己的命運。他比他搬動的巨石還要堅硬。如果說,這個神話是悲劇的,那是因為它的主人公是有意識的。若他行的每一步都依靠成功的希望所支持,那他的痛苦實際上又在那裡呢?今天的工人終生都在勞動,終日完成的是同樣的工作,這樣的命運並非不比西西弗的命運荒謬。但是,這種命運只有在工人變得有意識的偶然時刻才是悲劇性的。西西弗,這諸神中的無產者,這進行無效勞役而又進行反叛的無產者,他完全清楚自己所處的悲慘境地:在他下山時,他想到的正是這悲慘的境地。造成西西弗痛苦的清醒意識同時也就造就了他的勝利。不存在不通過蔑視而自我超越的命運。
如果西西弗下山推石在某些天里是痛苦地進行著的,那麼這個工作也可以在歡樂中進行。這並不是言過其實。我還想象西西弗又回頭走向他的巨石,痛苦又重新開始。當對大地的想象過於著重於回憶,當對幸福的憧憬過於急切,那痛苦就在人的心靈深處升起:這就是巨石的勝利,這就是巨石本身。巨大的悲痛是難以承擔的重負。這就是我們的客西馬尼之夜。但是,雄辯的真理一旦被認識就會衰竭。因此,俄狄浦斯不知不覺首先屈從命運。而一旦他明白了一切,他的悲劇就開始了。與此同時,兩眼失明而又喪失希望的俄狄浦斯認識到,他與世界之間的唯一聯繫就是一個年輕姑娘鮮潤的手。他於是毫無顧忌地發出這樣震撼人心的聲音:“儘管我歷盡艱難困苦,但我年逾不惑,我的靈魂深邃偉大,因而我認為我是幸福的。”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里洛夫都提出了荒謬勝利的法則。先賢的智慧與現代英雄主義匯合了。
人們要發現荒謬,就不能不想到要寫某種有關幸福的教材。“哎,什麼!就憑這些如此狹窄的道路……?”但是,世界只有一個。幸福與荒謬是同一大地的兩個產兒。若說幸福一定是從荒謬的發現中產生的,那可能是錯誤的。因為荒謬的感情還很可能產生於幸福。“我認為我是幸福的”,俄狄浦斯說,而這種說法是神聖的。它迴響在人的瘋狂而又有限的世界之中。它告誡人們一切都還沒有也從沒有被窮盡過。它把一個上帝從世界中驅逐出去,這個上帝是懷著不滿足的心理以及對無效痛苦的偏好而進入人間的。它還把命運改造成為一件應該在人們之中得到安排的人的事情。
西西弗無聲的全部快樂就在於此。他的命運是屬於他的。他的岩石是他的事情。
同樣,當荒謬的人深思他的痛苦時,他就使一切偶像啞然失聲。在這突然重又沉默的世界中,大地升起千萬個美妙細小的聲音。無意識的、秘密的召喚,一切面貌提出的要求,這些都是勝利必不可少的對立面和應付的代價。不存在無陰影的太陽,而且必須認識黑夜。荒謬的人說“是”,但他的努力永不停息。如果有一種個人的命運,就不會有更高的命運,或至少可以說,只有一種被人看作是宿命的和應受到蔑視的命運。此外,荒謬的人知道,他是自己生活的主人。在這微妙的時刻,人回歸到自己的生活之中,西西弗回身走向巨石,他靜觀這一系列沒有關聯而又變成他自己命運的行動,他的命運是他自己創造的,是在他的記憶的注視下聚合而又馬上會被他的死亡固定的命運。因此,盲人從一開始就堅信一切人的東西都源於人道主義,就像盲人渴望看見而又知道黑夜是無窮盡的一樣,西西弗永遠行進。而巨石仍在滾動著。
我把西西弗留在山腳下!我們總是看到他身上的重負。而西西弗告訴我們,最高的虔誠是否認諸神並且搬掉石頭。他也認為自己是幸福的。這個從此沒有主宰的世界對他來講既不是荒漠,也不是沃土。這塊巨石上的每一顆粒,這黑黝黝的高山上的每一顆礦砂唯有對西西弗才形成一個世界。他爬上山頂所要進行的鬥爭本身就足以使一個人心裡感到充實。應該認為,西西弗是幸福的。
《西西弗的神話》諸神懲罰西西弗不斷地把巨石滾上山頂,而石頭因為它自身的重量又會滾下去,他們完全有理由相信沒有比這徒勞而無望的工作更可怕的懲罰了,然後西西弗看著石頭馬上朝著更低的地方滾下去,在那裡,他不得不把它重新滾上山頂,我看到他回到山下,邁著沉重而整齊的步子,走向他永遠不知道盡頭的痛苦。當他離開山頂,漸漸沉沒在諸神的領地,他是高於他的命運的,他比那巨石更堅硬。
如果說加繆一生創作和思考的兩大主題就是“荒誕”和“反抗”的話,那麼哲理隨筆《西西弗的神話》就是加繆對於荒誕哲理最深入和集中的考察以及最透徹和清晰的闡釋。西西弗這個希臘神話人物推石上山、永無止境的苦役無疑正是人類生存的荒誕性最形象的象徵;但同時,他又是人類不絕望,不頹喪,在荒誕中奮起反抗,不惜與荒誕命運抗爭到底的一面大纛。因此,與其說《西西弗的神話》是對人類狀況的一幅悲劇性的自我描繪,不如說它是一曲自由人道主義的勝利高歌,它構成了一種既悲愴又崇高的格調,在整個人類的文化藝術領域中,也許只有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在品味上可與之相媲美。
加繆的思想,其核心就是人道主義,人的尊嚴問題,一直是纏繞著他的創作、生活和政治鬥爭的根本問題。《西西弗的神話》和《局外人》構成了加繆文學創作的母題,包含著加繆未來作品的核心問題。書中,西西弗的幸福假設的提出,其本質動機,不在荒誕,荒誕既不能告訴我們幸福,也不能告訴我們不幸,之所以加繆假設西西弗是幸福的,是因為他認為只有幸福的生活才符合人的尊嚴,被責為永罰,卻幸福,這絕對是一種反抗,也是在這種條件下唯一可能的反抗形式,而反抗才能體現尊嚴。加繆在假設西西弗幸福的時候,充分運用了想象和獨斷,其潛台詞,卻是人類尊嚴的需要。由荒誕的出發點,薩特走向焦慮和不安,而加繆走向幸福,薩特是思辨后的結論,加繆卻是激情洋溢的獨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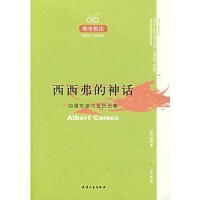
其他版本的《西西弗的神話》
在加繆看來,“所謂荒誕,是指非理性和非清楚不可的願望之間的衝突,弄個水落石出的呼喚響徹人心。”人的一生,會經歷無數的風雨坎坷,現實與理想往往存在巨大的落差。這種落差,就是加繆指出的世界的荒誕性。他讓人們直面現實的殘酷,對人生的荒誕保持清醒的認識。基於此,他否定世間存在所謂的萬能理性,“所謂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實踐的或精神的,所謂決定論,所謂解釋萬象的種種範疇,無一不使正直的人嗤之以鼻”。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人生的最終結局,“瘋狂和死亡,是荒誕人不可救藥的事情。人是不可選擇的。他具有的荒誕和多餘的生命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而取決於其反面,即死亡”。
加謬認為荒誕是人存在的一種必然狀態:“人是這個世界上奇怪的公民:他拒絕現存世界,卻又不願離開它,反而為不能更多地佔有它而痛苦。”既然如此,就有一個如何面對荒誕的問題。實際上,每個人對待荒誕也都有某種態度。加繆從他的荒誕哲理的概念出發,把面對荒誕的態度分為三種:
第一種是生理上的自殺。“我看到許多人由於認為生活不值得活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既然人生始終擺脫不了荒誕的陰影,甚至於生存本身就具有被判了死刑的荒誕性,那麼最簡易的對待方式就是自己結果自己,他想: 人死了,荒誕也就不存在了,他能夠逃避荒誕。問題是你逃避了,其他人沒法逃避,你消除了其他人沒法消除,所以說荒誕始終存在。“自殺就是招供,招供他已被生活超越或不理解生活”。
第二種是哲學上的自殺,這是精神領域裡的一種現象,它不是正視荒誕,而是逃避到並不存在的上帝那裡去,以虛幻的天國作為荒誕的樂園,這是自我理性的自殘。加繆在此,對基督教存在主義進行了批判,認為“他們把擠壓自己的東西奉若神明,而在使他們一貧如洗的東西中去尋找希望的理由”。《鼠疫》里品德善良而正直的神父,他從宗教世界觀出發,認為鼠疫是上帝對人的懲罰,惟一的辦法就是一切聽憑上帝的安排,他代表了依賴虛妄的神而放棄現實抗爭的消極人生態度,正是“哲學自殺”。第三種是反抗。“荒誕能推出的三個結果分別是我的自由、我的激情、我的反抗。”認識到荒誕之後,有尊嚴的生活是為生活而生活。
“我的自由”是指一種擺脫除生命自身以外的所有的一切事物的自由體驗,這是一種對周圍世界的一切事物毫無責任的感覺。
“我的激情”是指對現在與種種現在之延續的不斷的意識,最大限度地意識到自己的生命。對現在說“是”,對未來說“不”! 重要的不是生活的最好,而是生活得最多;要窮盡現在,重要是生活在現在,而不是生活在別處,所以加繆歌頌身體的偉大: 創造、行動、愛撫。加繆這種看重“現在”的觀念,從根源上講,來自阿爾及利亞的平民社會,延續了古希臘文明的特徵: 看重現實,熱愛生命,崇拜肉體,人們赤裸地在海灘上曬太陽,在大海里暢遊,“置身與陽光與苦難之間”。對未來說不,其意是人如果為了尋找生活的意義,為了某種目的或為某種偏見而生活,那就會給自己樹立起生活的柵欄。“我看到有些人荒唐地為著那些所謂賦予他們生活意義的理想或幻想而丟掉了性命。所謂活著的理由,也就是死的極佳理由”,加繆在《反與正》里,嘲諷一位婦女,她每天以造訪自己精心挖掘的墓穴為樂,這就是加繆所說的為未來生活的人。
“我的反抗”中的這個反抗又叫肯定,是比激情更進一步的行動。在加繆的作品中,發現荒誕只是一個出發點,更重要的是對荒誕採取反抗態度。如果僅僅停留在意識到荒誕這一階段,人就會陷入一種憂鬱和軟弱的境地,反抗則帶來行動。“舉起巨石,藐視諸神”,諸神給西西弗的判罰是他逃脫不了的宿命,逃脫不了,他就做,諸神拿他就沒有辦法了。這實際上是一種既悲愴又崇高的格調,與命運交響曲異曲同工。加謬對世界和命運的觀察是殘酷的,對自然、對人生卻充滿了熱愛,為了這個熱愛,就必須歷盡苦難。《鼠疫》主人公里厄日夜奔波,不辭辛勞地與疾病搏鬥,其過程和結局就是20世紀40年代版的西緒福斯的石頭,他深知醫學的力量有限,難以消滅鼠疫,但他仍盡醫生的本份,忠於職守,醫治病人,控制鼠疫繼續流行,不在困難與無效面前低頭,持續地與鼠疫進行鬥爭,其勞頓、其堅韌、其無畏猶如西西弗推石上山。如果他與西西弗還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他身上的抗爭精神、他與荒誕、與惡進行鬥爭的精神更為突出。
反抗,加繆把荒誕定義為一種對立和較量,一種無休止的鬥爭,這種鬥爭意味著取消希望和不斷拒絕。因為生存,就是使荒誕存活。使荒誕存活,首先是正視荒誕。荒誕只在人們與其疏遠時才死亡,選擇反抗,是唯一前後一致的哲學立場。加繆把“反抗”視為從荒誕取得的第一個結果。其次,第二個結果是自由,是一種擺脫生命自身以為的所有一切事物的自由體驗,這種自由是失去上帝,“一切都被允許”的自由,但是這種自由並非為所欲為,而是一種苦澀的確認,伴隨著責任,人要對自己的行動負責。當人們知道了死亡是最大最明顯的荒誕后,便要立足當下抓住現實生活,在自由的局限里生活得最多最好。第三個結果是激情,激情是荒誕的倫理,是要最大限度的生活,也就是最大限度地意識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反抗。無論生活中充滿何種痛苦的經歷,生命仍然值得一過。荒誕人充滿激情意味著現在的種種都將延續,荒誕人沒有足夠的想象力(對上帝、信仰、理性),無法給自己描繪所謂奇特的未來,荒誕人需要憑藉他所知道的一切而生活,如同西西弗的巨石。

阿爾貝·加繆
加繆在他的小說、戲劇、隨筆和論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異己的世界中的孤獨、個人與自身的日益異化,以及罪惡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在揭示出世界的荒誕的同時卻並不絕望和頹喪,他主張要在荒誕中奮起反抗,在絕望中堅持真理和正義,他為世人指出了一條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以外的自由人道主義道路。他直面慘淡人生的勇氣,他“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大無畏精神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不僅在法國,而且在歐洲並最終在全世界成為他那一代人的代言人和下一代人的精神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