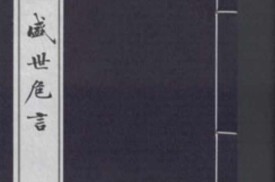盛世危言
清代鄭觀應所著作品
《盛世危言》是鄭觀應編成於公元1894年(光緒二十年)的論文集。全書貫穿著“富強救國”的主題,對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方案,在當時是給甲午戰敗以後沮喪、迷茫的晚清末世開出了一帖拯危於安的良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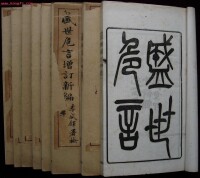
《盛世危言》書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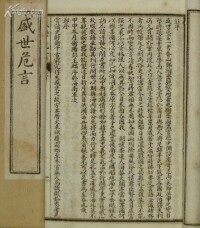
《盛世危言》資料圖片
《盛世危言》對中國近代史的走向有著重要的影響。光緒二十一年,江蘇布政使臣鄧華熙曾將《盛世危言》五卷本推薦給光緒,光緒批示印製2000部,分發給各省高級幹部,國內各書坊立即盜版翻刻,達十餘萬部之多,並成為科舉士子的必讀參考書籍。
鄭觀應所談到的“沒有議院民主,如何凝聚億萬百姓之心為一心”,其實即民眾的國家認同感問題。鄭氏希望在十九世紀末期以一種新制度文明給國民鑄就一種新的國家認同感,在此後的歷史進程中,中國人民在一次又一次的嘗試與失敗,再嘗試中逐漸走出了一種新的道路。雖然這條道路與鄭氏所描繪的大有不同,然而,一以貫之的是對於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不懈追求。鄭氏的“盛世”雖然以另一種形式到來,然而“危言”永不過時,時時告誡我們要居安思危。
現今最具權威性和代表性的《盛世危言》文本,分別是光緒二十年(1894年)的5卷本、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的14卷本《盛世危言增訂新編》和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的8卷本《盛世危言增訂新編》。近代,研究鄭觀應的專家夏東元教授所編的《鄭觀應集》,當中《盛世危言》文本乃其上三個權威性版本之綜合本,共115篇文章。而最早的《盛世危言》5卷本包括57篇文章,其標題分別如下:
《道器》 《學校》 《西學》 《女教》 《考試上》 《考試下》 《藏書》 《議院》 《日報》 《吏治上》 《吏治下》 《遊歷》 《公法》 《通使》 《禁煙上》 《禁煙下》 《傳教》 《販奴》 《交涉》 《書吏》 《廉俸》 《建都》 《教養》 《訓俗》 《獄囚》 《醫道》 《善舉》 《稅則》 《國債》 《商戰》 《商務》 《鐵路》 《電報》 《郵政上》 《郵政下》 《銀行上》 《銀行下》 《鑄銀》 《開礦》 《紡織》 《技藝》 《賽會》 《農功》 《墾荒》 《旱潦》 《治河》 《防海上》 《防海下》 《防邊上》 《防邊中》 《防邊下》 《練兵》 《水師》 《船政》 《民團》 《火器》 《弭兵》
《盛世危言》問世之時,正值中日甲午戰爭一觸即發之時,國內的民族危機感極重,該書出版后隨即轟動社會及以極快的速度傳播。據說《盛世危言》亦曾呈給光緒帝,光緒帝下旨“飭總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閱看”。該著作被當時人稱為“醫國之靈柩金匱”,推動洋務運動的張之洞亦評“上而以此輔世,可為良藥之方;下而以此儲才,可作金針之度。”由此,可窺見該書對治理國家之價值。《盛世危言》乃中日甲午戰爭前著名的政治改良論著。
除清朝社會外,著作對其後的社會亦產生廣泛影響。《盛世危言》的出版,其中對清末的維新派和革命派具承先啟後的作用,亦為1898年開始的百日維新奠下重要根基。蔡元培於《蔡元培年譜》評價該書:“以西製為質,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發揮之。時之言變法者,條目略具矣”。受鄭觀應和《盛世危言》影響的著名人士,其中包括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毛澤東等。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記述毛澤東在1936年曾回憶自己青年時閱讀該書的感想:“這本書我非常喜歡。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義學者,以為中國之所以弱,在於缺乏西洋的器械——鐵路、電話、電報、輪船。”儘管這一自述常被引用——作為《盛世危言》在近代中國影響深遠的例證——但是,如果斯諾記載無誤的話,那麼,13歲的毛澤東其實並未讀懂《盛世危言》。與少年毛澤東的理解恰恰相反,作者鄭觀應對晚清改革專註於引進西方的“鐵路、電話、電報、輪船”其實持批判態度。鄭氏急於要引進中國的,不是技術,而是制度,具體而言,是議會民主制度。同時,《盛世危言》所提出的革新觀念和“以商立國”的商戰理論,對中國近代思想史及商業發展起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