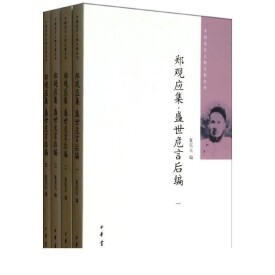共找到2條詞條名為易言的結果 展開
- 劉錫誠
- 鄭觀應著作
易言
鄭觀應著作
19世紀中葉以後,正是中國近代史的危急存亡之秋,內有太平天國、捻軍起義,外有英法聯軍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強迫清政府簽訂《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等不平等條約。這種內憂外患的局勢深深刺激了晚清志士鄭觀應,始在愛國思想指導下“究心泰西政治實業之學” ,逐步形成社會改良思想,在1862年寫了《救時揭要》一書(1873年出版),表達他對時局的感慨,但其思想仍停留在舊的層面,雖然主張學習西方,但卻認為勸人“一心向善,積現前莫大之功”才是救國之道,並未成熟。
此時,中國掀起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洋務運動,鄭觀應積極投身其中,參與洋務企業上海電報局、輪船招商局、漢陽鐵廠等的運營中。在這一過程中,鄭觀應隨著閱歷的豐富,思想不斷發生著變化,逐漸形成了比較系統的社會改良主張。成書於同、光之交的《易言》,就是他改良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標誌。關於《易言》的著述動機,鄭觀應在自序中寫道:
往余同治庚午、辛未(1870、1871年)間,端居多暇,涉獵簡編,偶有所見,隨筆札記。內之積感於寸心,外之眷懷於大局。目擊時艱,無可下手,而一言以蔽之曰:“莫如自強為先。”自強之道不外乎此數大端而已。因是宏綱巨目,次第敷陳。自知但舉其略,語焉不詳。積若干篇存之篋衍,徒自考鏡,未嘗感以論撰自居。而朋好見輒持去,雜付報館,又闌入近人所刻《聞見錄》中。丑不自匿,嘗用蹴然。
由此可見,鄭觀應是在同治後期閱讀了許多著作之後,結合時局,寫下心中感想,並以“自強”為宗旨,由此誕生了《易言》這本書。
“易言”一名取自《詩經·大雅》中之“無易由言”一句,意思是不要輕易發言,表明了鄭觀應對他觀點所持的謙虛謹慎的態度,而其筆名“鐵城杞憂生”也是想說他只是杞人憂天而已。《易言》全書分上、下兩冊。論述的項目如下表:
| 上卷 | 論公法、論稅務、論阿片、論商務、論火車、論電報、論開墾、論治旱、論船政、論籌銀、論監務、論遊歷 |
| 下卷 | 論考試論邊防、論火器、論開礦、論機器、論議政[附論洋學]、論吏治:論交涉、論傳教、論出使、論水師、論練兵、論民團、論治河[附謀君議]、論虛費、論廉俸、論書使、論招工、論醫道、論犯人、論疏流、論借款、論裹足 |
從這些文章的名稱可見,鄭觀應列舉並論述了關於國家制度各方面的廣泛問題。他所議論的內容,一言以蔽之,即消除中國因襲的陋習,接受科學技術,開發產業,獎勵通商,以實現富國強兵;同時主張履行萬國公法,與外國締結對等外交。
鄭觀應在其《易言》筆下充滿了愛國思想,他揭露歐美列強的侵略野心,他強調:“西人有求於中國者,不外通商、傳教兩端”,而“通商則漸奪中國之利權,並侵中國之地;傳教則偵探華人之情事,欲服華人之心,……其中煽害,倍甚通商”。他雖然強烈反對歐美侵略,卻也非盲目排外,而是意識到實行“公法”與國家的強弱密切相關,提出“公法約章宜修也”,同時提出“兵制陣法宜練也”,“槍炮器械宜精也”,“礦務、通商、耕織諸事宜舉也”。他提出學西學主要是為了“制勝”對方,“夫欲制勝於人者,必盡知其成法,而後能變通;能變通,而後能克敵”。鄭觀應還指出:“歐洲各邦皆以通商為大經,以製造為本務。蓋納稅於貨,而寓兵於商也。”在該書的《論商務》、《論開礦》、《論火車》、《論電報》、《論機器》、《論船政》等篇中,他詳細地闡述了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重要性和具體辦法,積極主張近代企業由商民自辦,認為中國商政不興,主要在於政府官員的巧取豪奪和官場腐敗積習的干擾。一旦企業歸商民自辦,“彼將視為身心性命之圖,製造必精,程功必速,成本必廉,虛費必省”。在政治改革方面,他大膽地提出設議院的主張,批評封建專制制度的弊病,“於政事之舉廢,法令之更張,唯在上之人權衡自秉”,上下“情誼相隔”,不如西方議院制度優越。他把西方議院制度比附為士大夫所嚮往的“三代制度”,希望中國能夠“上效三代之遺風,下仿泰西之良法”,實現“長治久安之道”。不過,《易言》仍未脫離“中體西用”思維的束縛,仍希望用“中國五帝三王之道”來作為根本,藉助西法來達到富強的目的。
《易言》成書後,鄭觀應於1875年將手稿郵寄客居香港的名士王韜。王韜閱后讚嘆不已,為其作序、作跋,並由他主持的中華印務總局於1880年刊印發行。
1881年,鄭觀應又請沈穀人、謝綏之將原稿36篇刪並為20篇,由上海淞隱閣排印再版,仍用《易言》之名,而作者改署“鐵城杞憂生”為“鐵城慕雍山人”,取期再現雍熙盛世之意。鄭觀應此次作出的刪改,具有明顯的倒退和保守性質,將1871年所著之原書中的許多精華剔除,而其新筆名也似乎暗示了他正回歸“天朝上國”的心態中,這無疑是由於當時邊疆危機的加劇、俄日法紛紛入侵導致鄭觀應的民族主義的上升所致的。
但是,這並不影響鄭觀應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到1894年,鄭觀應在《易言》的基礎上推出了振聾發聵的巨著《盛世危言》,全面闡述了他學習西方、維新變法的進步思想,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其中核心思想,如“商戰”、“君民共治”等,都可以說是直接繼承發展了《易言》的觀點。然而,或許是由於被《盛世危言》的光芒所掩蓋的因素,《易言》一書並沒有那麼受人矚目,甚至可以說被中國人淡忘了。但是在鄰邦朝鮮的近代化進程中,《易言》卻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鄭觀應後來《盛世危言增訂新編》中談到《易言》“風行日、韓” ,可見《易言》一書在海外日本、朝鮮諸國有很大影響,其中在朝鮮影響尤大。傳入朝鮮的《易言》,是1880年修信使金弘集出使日本時,從中國駐日公使館參贊黃遵憲那裡帶來的,而黃遵憲手上的《易言》當是1879年訪日的王韜帶去的,當時還是沒有公開刊行的二卷三十六篇版本。對此《梅泉野錄》一書記載道:
“庚辰十月,金弘集還自日本,進《易言》二冊。《易言》者,清人黃遵憲所著也,大意處今日而欲致富強,必先學洋制而習洋技,累累數十萬言,大略策士馳騁揣摩之見耳。遵憲攜之游日本,弘集得之,以備乙覽,蓋欲上之默察天下大勢,而亦原隰諮詢之職耳,非有私意包藏也。拘曲之儒謂弘集進天主學,攻駁之論紛然而起。 ”
這段記載說明了《易言》的主要內容及經由黃遵憲贈與金弘集的傳播過程,是證明《易言》傳入朝鮮的關鍵史料。但是,這段記載也錯誤地把《易言》的作者記錄為黃遵憲,而且將黃遵憲贈與金弘集的另一著述《朝鮮策略》(這才是黃遵憲本人所寫)所引發的儒林上疏事件(辛巳斥邪運動)混為一談。事實上當時朝鮮儒生的“攻駁之論”主要集中於《朝鮮策略》而非《易言》,但這並不代表著《易言》不受朝鮮人關注。事實上,《易言》也像《朝鮮策略》那樣被朝鮮知識分子廣為傳閱,也確實遭到了保守人士的一些攻擊。儒學家李承熙在1880年時只有14歲,他在當年閱讀了《易言》后,認為“《易言》憂中國之衰敗,發言多切中時弊,然醉於西歐風潮,不知東洋先王之大道,故特書後以辨之”。 1883年日本《時事新報》中提到了朝鮮人“昔者不識此書(《易言》)之意義,斥為頑夷或天主教”。但是更多的朝鮮人則注意到這本書的積極意義,從而使《易言》極大推動了朝鮮近代開化運動的展開。
1881年10月,朝鮮官員魚允中和李祖淵訪問中國上海,專程拜訪了鄭觀應,第二年夏朝鮮文人姜瑋也去上海拜訪鄭觀應,朝鮮人士對鄭觀應給予特別關注,無疑是《易言》在朝鮮的傳播所致。這一點從鄭觀應方面也可印證,他曾在給李祖淵寫的信中提及“昨奉惠書並還前印《易言》書價銀八十元” ,並寫了一首《高麗使臣魚允中李浣西來購〈易言〉並詢治策書此代柬》詩:
堯舜秉至公,無為天下治。嬴秦雖至強,徇私亡國易。所以賢君相,孜孜為民計。民強國自強,道由策富致。致富勿愚民,廣學開其智。舍此國必衰,賢者皆避位。威武不能屈,直臣諫而死。叵奈諂佞臣,偷生溺富貴。秦檜與嚴嵩,青史嚴擊刺。《易言》慚管窺,宗旨亦如是。遠詢杞憂生,聊達區區意。
從詩歌的題目可以看出,魚允中等朝鮮官員不僅因《易言》而來,更向鄭觀應請教富強之策。鄭觀應也不吝指教,作了這首詩,並且對朝鮮人的來訪頗有知遇之感。《易言》對朝鮮的影響不止於此。1881年底,朝鮮大臣朴定陽在其《從宦日記》中記載“以經理事蒙《易言》二冊賜給” ,可見《易言》是作為“內參文件”在朝鮮高官中免費傳閱的。1882年“壬午兵變”以後,《易言》更是廣泛傳播,這從當時不少知識分子給朝鮮國王的上疏中可以看出。池錫永上疏在長篇大論地闡述了開化思想的最後寫道:“凡自強禦侮之策,具載於《易言》一部書,臣不敢贅進焉”。卞鋈上疏中建議將《易言》、《朝鮮策略》、《萬國公法》刊行於朝鮮八道。金永孝上疏中引用《易言》中“論水師”一篇,主張建立海軍。尹善學上疏更是寫道:“臣看中國人所編《易言》冊子,可謂治世之要訣,而達權知變之士矣。始知天下事,不同於秦漢唐宋之世,而至今日而受變之極也……”。如此種種,不一而足。從這些上疏中可以看出,《易言》一書在當時朝鮮知識分子中非常流行,可以說到了爭相傳閱的地步,而且他們都對《易言》給予很高的評價,將其視為富國強兵的藍本,足見《易言》在朝鮮的巨大影響。其中王韜在《易言》的跋文中寫道:“杞憂生之所欲變者,器也,而非道也。”朝鮮士人尹善學則在上疏中呼籲:“臣之欲變者,是器也,非道也。”完全是效仿《易言》。這句話進而演變為朝鮮穩健開化派的指導思想——“東道西器”,在朝鮮近代史上有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