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樺派
白樺派
白樺派是日本現代文學中的重要流派之一,以創刊於1910年的文藝刊物《白樺》為中心的作家與美術家形成。
他們主張新理想主義為文藝思想的主流,因此也稱為新理想派。該派的作家主要有武者小路實篤、有島武郎、有島生馬、志賀直哉、木下利玄、長與善郎等人。受白樺派的影響而成長起來的日本知名人士有劇作家倉田百三、詩人千家元等。
日本現代文學中一個重要的流派,以文藝刊物《白樺》(創刊於1910年)為中心的作家與美術家所形成。他們主張新理想主義為文藝思想的主流,因此也稱為新理想派。
在日本文學上首次否定了自然主義(十九世紀產生於法國的一種採取自然主義創作手法的文藝流派,以佐拉為代表。是一種文藝創作上的不良傾向,著重描寫現實生活中個別現象和瑣碎細節,但不能正確的反映社會的本質。推出新理想主義,主張個性解放,宣揚人道主義。
1916年至1917年間存活的在日本文壇上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流派。白樺派的創作主題是反對戰爭、反對壓迫、追求和平、反對舊道德對自我的束縛、同情弱小者、表現強烈的自我意識,這一主題是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活躍的民主主義社會思潮緊密聯繫的代表作家有武者小路實篤、有島武郎、志賀直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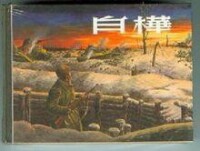
白樺派
武者小路實篤在《白樺運動》一文中提出:“白樺運動是尊重自然的意志和人類的意志,探索個人應該怎樣生活的運動。”他主張,“通過個人或個性發揮人類意志的作用”。這是緊接純客觀主義的自然主義思潮之後的新的主觀主義運動。他們的理想無一定的方向,僅以個人與個性的成長作為運動的口號。
除了這一根本主張,流派中主要的成員,絕大多數在道德與倫理上保持高度的潔癖,富有人道主義的色彩,因而他們容易被看作一種人道主義者的團體。他們反對文學藝術上的自然主義流派,也自稱為精神的自然主義者。在這一派的作家中,有的站在嚴正的現實主義的立場,有的則具有空想的非現實主義的傾向。
在日本大正時期(1912~1926)的資產階級文學中,曾哺育了不少在思想上藝術上處於高峰地位的作家。他們是徹底自由主義的個性尊重者,能夠從各種舊傳統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在作品的形式與表現方法上有許多創新。直接受白樺派的影響而成長起來的。有以劇作家倉田百三、詩人千家元麿等為首的一大批知名作家,包括後來成為無產階級作家的江馬修等人。

白樺派
以1914年所發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為契機,在世界範圍內形成的民主主義思想運動的高潮,強烈地影響了日本。日本知識分子對人類光明的理想與不斷地前進的可能性懷抱希望。白樺派的文學藝術在這種思潮下進入了全盛時期,成為大正時期文學的主流,並給以後的日本文學留下深遠的影響。
由於有島武郎傾向於唯物史觀社會主義思想的主張,與白樺派一般為唯心主義的觀念,逐漸地發生矛盾。這一流派的主持者武者小路實篤從事於組織空想的“新村運動”,遭到失敗。
1924年東京大地震導致了《白樺》的停刊。特別是唯物主義思潮的發展,使白樺派的文學藝術思想逐漸衰微。
1910年4月創刊,1923年8月停刊,共計出版發行160期。由武者小路實篤和志賀直哉等的傳閱雜誌《望野》(后改稱《白樺》 )、里見弴等的傳閱雜誌《麥》和柳宗悅等的傳閱雜誌《桃園》合併而成,另有有島武郎、有島生馬等人加入,成員大多屬於上流階層。創刊時具有濃厚的反自然主義色彩,同時致力於介紹歐洲美術,尤其是後期印象派畫家。
《白樺》
既是文學雜誌,又是美術雜誌。該刊強調尊重個性,成員傾向各不相同;但就整體而言,起初利己主義色彩較濃,其後則理想主義和人道主義傾向較強。在該刊周圍,還有《利己主義》和《生命之川》等一系列衛星雜誌,其勢力逐漸擴展,成為當時文壇的中軸。白樺派的主要作家及其作品有志賀直哉的《到網走去》、《在城崎》、《好人物夫婦》、《赤西蠣太》和《和解》,武者小路實篤的《他的妹》、《幸福者》和《一個青年的夢》,有島武郎的《一個女人》 、《給幼小者》和《該隱的末裔》,里見弴的《你與我》,長與善郎的《盲目之川》和《項羽和劉邦》,木下利玄的短歌,千家元麿的詩歌等。除主辦《白樺》雜誌外,該派還組織白樺演劇社、白樺美術館和白樺音樂會,出版《白樺之森》、《白樺之林》、《白樺之園》和《白樺腳本集》等同人合著集。《白樺》停刊后,該派又陸續創辦《不二》、《新村》、《大調和》、《獨立人》和《心》等,其影響達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白樺派
這自然不失為一種美好的理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人類主義”本身卻包含著與它的表層意義背道而馳的國家主義的甚至是法西斯主義的潛在邏輯:當今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是孤立存在,全人類密切相關,而每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又有所差異。因此,文明先進的國家有義務向文明落後的國家輸出文明,這是文明先進的國家對人類所承擔的神聖義務。而這種觀點正是現代法西斯主義思想的一個核心。遺憾的是,武者小路實篤正是自覺不自覺地漸漸地沿著這條邏輯思路來發展他的思想的。

白樺派
誠然,武者小路實篤講這些話時,也許並沒有後來對中國人民的那種惡意,但是,這裡卻隱含了這樣一種觀點:中國和別的國家,和日本比較起來,還不能做所謂“人類的”事業。換句話說,中國的文明程度比“別的獨立國”要低。按照他的邏輯,文明程度低的國家“便逃不出世界的侮辱,也逃不出制裁”。在這裡,武者小路實篤的立論根據顯然是當時日本思想界所崇奉的文明進化論。這種進化論認為世界各國的文明進化有先後高低之分,因此,先進的文明國家可以向落後的國家“輸出文明”。早在明治維新初期,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渝吉就極力宣揚這種觀念。福澤渝吉把甲午戰爭(日本稱之為日清戰爭)說成是“文明與野蠻之戰”,“他認為日本是在文明的大義之下與中國作戰的,在這一意義上,使中國屈服乃是‘世界文明之洪流賦予日本的天職’”。
這種觀念其實也是明治維新之後日本人的主流觀念,如三十年代日本學者秋澤修二就曾聲稱,“日本皇軍的武力”侵華,就是為了打破中國社會的“停滯性”,推動中國的發展。武者小路實篤一方面在《一個青年的夢》中反對戰爭,但另一方面又在思想深處接受了這種觀念,這就是他日後狂熱支持日軍侵華的內在原因。武者小路實篤是一步步發展這一觀念的。在1921年出版的劇本《無能為力的朋友》(中譯本為《未能力者的同志》)也是以日俄戰爭為背景的。其中的主要人物“先生”顯然是作者思想的代言人。在那裡,《一個青年的夢》那樣高亢激昂的反戰論不見了,反戰的調子大大降低了,只不過是說:“這一次戰爭,我至少也當作無意味看。”同時又聲稱:“然而作為國民,不得不去(戰爭)”,甚至一反過去的人道主義同情,說什麼:“C君(按:戰死者)是很可惜的,在愛C君的人也很可悲,然而自然卻命令我們要冷淡。每日不知道死去多少人,倘使……悲傷起來,這世界便成為哭泣的海洋了。”正如劇中人物A和B所指出的,“先生”在戰爭問題上態度“含糊”了。《無能為力的朋友》顯示了武者小路實篤在反戰上的倒退。然而,包括《無能為力的朋友》在內的武者小路實篤的作品集《人的生活》卻又被譯成了中文,而且周作人還為這個譯本做了序。周作人在序中對所收作品展開評論,但顯然是懷讚賞之意的。總的看來,對武者小路實篤由激烈而明確的反戰,到態度含糊曖昧的變化過程,周作人渾然不覺,魯迅則未及留意。魯迅在譯出《一個青年的夢》之後,除了譯出了幾文學論文以外,對於武者小路實篤的其他作品便不再留意了。對於武者小路,魯迅同樣是奉行“拿來主義”的。
有島武郎(1878年3月4日-1923年6月9日)是近代日本的小說家。於學習院畢業后,因有志於向農學發展而升讀札幌農業學校。信奉基督教,後來更接受洗禮。1903年到美國留學。歸國后參與文藝雜誌《白樺》的編製工作,是白樺派的代表人物之一。1923年,於輕井澤別院凈月庄中,與波多野秋子共同殉情。其作品《カインの末裔》(該隱的末裔)、《或る女》(一個女人)等都是膾炙人口的佳作。
寫作經歷:歸國后,有島武郎曾任職預備見習士官與及大學英語講師。後來在透過弟弟有島生馬的引介下,認識後來的白樺派代表人物誌賀直哉及武者小路實篤,並參與同人雜誌《白樺》的創作。在《白樺》工作期間,有島先後發表了《かんかん蟲》(硬殼蟲)、《お末の死》(阿末之死),並創作很多小說及評論,其活躍的表現令他很快便成為了白樺派的中心人物之一。1916年,妻子神尾安子及父親有島武相繼亡故,有島武郎在失去家庭羈絆后成為全職的作家,接著發表《カインの末裔》、《生まれ出づる悩み》(與生俱來的煩惱)及《迷路》等作品,繼而於1919年發表代表作之一的《或る女》。
殉情結局:輕井澤凈月庄可是,隨著上述作品陸續推出后,有島武郎開始感到江郎才盡,更在撰寫作品《星座》的途中忽然宣布封筆,並於1922年發表《宣言一つ》(一則宣言),表示要在北海道狩太村經營“有島農場”,正式終止作家生涯。1923年,有島武郎遇上了女性雜誌《婦人公論》記者波多野秋子,並與其產生戀情。可是波多野秋子本身是有夫之婦,他們的戀情很快便被秋子的丈夫波多野春房所悉破,二人一直備受壓迫,終於在6月9日二人決定於輕井澤的別墅凈月庄中雙雙自縊殉情。直至7月7日二人的屍首才被發現,由於已經經歷一個月之久,而且又遇上了梅雨的節氣,當二人遺體被發現的時候早已腐爛發臭,並已出現蛆蟲(蛆蟲的數量甚至多得從莊院中的天井爬出屋外),要經由二人所留下的遺書證實后才可確認二人的身份。魯迅《現代日本小說集》中曾提及並分析有島武郎的作品。在有島武郎死後,魯迅弟弟周作人曾經寫過一篇文章,以追懷故人。
志賀直哉:日本作家。1883年2月20日生於宮城,,祖父是相馬藩府的家臣。3歲即隨父母上京,開始受貴族子弟式的教育。18歲從學於宗教家內村檻三,21歲入學習院高等科,有志於文學創作。1904年發表處女作《菜花與少女》。1906年入東京帝國大學文科英文系,兩年後轉國文學科,中途輟學。與武者小路實篤、木下利玄共同創辦傳閱雜誌《望野》。創作短篇小說《某晨》、《到網走去》,向《帝國文學》投稿被退回。繼續創作《速夫之妹》、《荒娟》等小說。1910年,與有島武郎、有島生馬、武者小路實篤、木下利玄等共同創辦《白樺》雜誌。圍繞於這個刊物的一些年輕作家與美術家,對當時主張純客觀主義的自然主義文藝思潮不滿,要求肯定積極的人性,主張尊重個性,發揮人的意志的作用,提倡人道主義與理想主義的文學,形成“白樺”一派。志賀為“白樺派”代表作家之一。1910年發表曾被《帝國文學》退稿的《到網走去》與新作《剃刀》,1912年發表短篇小說《克羅諦思日記》,顯示他出眾的才華,為文藝界矚目。1917年發表的著名中篇小說《和解》,寫他立志於文學與父親發生衝突而終於得到和解的經歷。作者從此進入創作旺盛時期。《在城崎》(1917)、《佐佐木的場合》、《好人物夫婦》(1917)等名著,以及歷史小說《赤西蠣太》(1917)相繼問世。從1921年開始,著手寫他生平唯一的長篇小說《暗夜行路》,歷時15年之久,於1937年完成。這是他的代表作,寫一個孤獨的知識分子在不幸的生活中與思想苦悶的道路上探索的歷程。主人公時任謙作是祖父和母親的私生子,在兄弟間一直遭受歧視,在母親死後,他與祖父及其年輕的妾共同過著寂寞的生活。為立志從事文學事業與父親發生衝突,婚後又發現妻子不忠,便獨自流浪,最後在旅途中病倒。妻子趕到時,只見病床上的丈夫睜開柔和而充滿愛情的眼睛。
志賀直哉於1918年經過短暫停頓后,重新執筆,以創作上新的成就,蜚聲於大正文壇,被稱為新現實主義的第一人。他對人性作深邃的觀察,對於庸俗與虛偽有驚人的敏感與強烈的憎惡。他具有理想主義的熱情。1917年的中篇小說《好人物夫婦》,表現了他心境的轉移,從生氣蓬勃與激越的性格轉變為蒼勁沉著的態度。
志賀的作品大多從自己及和自己有直接關係的生活中取材,是現代日本文學中從自我經驗中取材最多的作家。在創作方法上的現實主義的精神,對同時代的日本作家有深刻的影響。
志賀一向關心社會事務,在政治上和文學上表現堅貞不屈。早年關懷足尾礦工中毒事件,同情小林多喜二的犧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保持沉默,以示對侵略戰爭的抗議。後期的作品還有《萬曆紅瓷瓶》(1933)、
《颱風》(1934)、《早春的旅行》(1941)、《寂寞的一生》(1941)以及戰後創作的《灰色的月亮》和《被腐蝕的友情》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