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魯什
讓·魯什
讓·魯什1917年5月13日生於巴黎。真實電影創始人,法國紀錄片大師。魯什早先是人種學家,在法國國立研究中心工作。他用攝影機作為記錄手段在去非洲的旅行中拍攝了《割禮》 (1949)、Rainmakers 《求雨先生》 (1951)、《獵河馬》等8部短片。1958年,盧什在影片《我是一個黑人》中,試圖把碼頭工人的日常生活直接搬上銀幕,為此他邀請了3個碼頭工人,即席發揮表演,形成了一種虛構與生活混合一體的影片。1961年,盧什拍攝了影片《夏日紀事》。

讓·魯什
·魯巴黎,紀始,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拍攝當地風光、社會和人文等影片,數量超過140部。近年來,80多歲高齡的魯什仍到處奔波,拍攝有關非洲的影片。2004年2月19日凌晨在尼日遭遇車禍身亡。
,魯研究研究義拍攝短片《割禮》、《求雨》,短紀錄片談“影”。
1958年的《我這個黑人》起,他對所拍攝的素材進行了個人干預,把虛構加入原始的真實事件中。
1959年《人類的金字塔》已離開人種學的軌道,而是按照社會——心理學來表現人的行為。
1960年的《夏日紀事》是他的成名作,影片觸及了“生活的纖維”。
1962年的《懲罰》,他開始強調調和真理電影和純故事片。
1964年的《北站》反映了魯什眼中的巴黎。在這部影片中,他儘力使故事片和真理電影融合起來:虛構在劇本中,即興在技術中。
1947年:《在黑巫師的國家》。
1946年:《萬捷爾伯的魔術師》,《割禮》。1952年:《河流之子》。
1955年:《瘋狂的主人》(中型影片)。
1959年:《我是一個黑人》。
1960年:《疊羅漢》。
1961年:《夏日記事》。
1963年:《懲罰》。
1954—1968年:《雅加爾》。
1971年:《漸漸地》。
| 戛納國際電影節 |
| ▪ 1976 第29屆戛納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金棕櫚獎 Babatu (提名) |
| 威尼斯國際電影節 |
▪ 1984 第41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金獅獎 酒神狄厄尼索斯 (提名) ▪ 1979 第37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費比西特別獎 Le vieil Anaï (獲獎) |
| 柏林國際電影節 |
| ▪ 1993 第43屆柏林國際電影節和平電影獎 水夫人 (獲獎) |
| 洛迦諾國際電影節 |
| ▪ 1959 第12屆洛迦諾國際電影節最佳娛樂電影獎 我是一個黑人 (獲獎) |

《夏日紀事》
首先,當然存在著有意識的“表演”。他們對自己說,“觀眾在看,我必須給他們一個好的印象。”但是這種表演只會持續一小會兒,然後非常迅速,他們會開始——也許是第一次真誠的——考慮他們自身的問題,考慮自己到底是誰,開始表現他們的心靈。這種時刻非常短暫,所以必須知道怎樣去充分利用。這就是製作一部電影(類似於《夏日紀事》)的藝術表現手法。
在《夏日紀事》的拍攝過程中,莫蘭(Morin)和一直與那些時刻關注並參與影片進展的人保持著持久而密切的聯繫;歲月匆匆,在拍攝的幾個月里,這部片子成了他們繼續生活的原因。時過境遷,那些曾經參與到這場“拍攝遊戲”的人們,在看到銀幕上的自己之後,開始認真地思考起自己曾經極不情願扮演的人物——對於各自的人物角色,他們當時是那麼地渾然不覺,以至在銀幕上重新審視自己的時候,竟然一個個瞠目結舌!從那一刻起,他們開始脫胎換骨,去扮演一種與從前的不一樣的角色!有關電影中的這種現象,還有很大的探索空間。你還記得瑪斯琳(Marcelline)嗎,那個猶太女孩沿著協和廣場(1J9 Placede la Concorde)走著,喚起了她在佔領期間被關進集中營的記憶。
瑪斯琳總是談論被驅逐出境的事情。每當她說起這件事,就會產生一種強烈的表現癖。許多有過類似經歷的人,在試圖讓你明白他們所經歷過的全部恐慌時,都會產生這種表現癖。
一個經受了心理創傷的孤僻、失去了父親,並自傷白憐的角色!一個她通常不會表現出來的角色!

讓·魯什作品
影片的某種非常奇怪的側面開始顯現出來了,瑪斯琳和讓·皮埃爾住在一起時,雙方之間存在很多棘手的問題,包括那些讓莫蘭日夜冥思苦想以及雙方相處不融洽等問題。這樣,像在其他影片中注意到的那樣,也親眼見證了這種令人稱奇的事情,即電影一躍成為這些人解決問題的借口。而對於他們自己來說,不通過電影,他們根本無法解決這些問題。
讓·魯什拍攝最後一場戲時,瑪斯琳和讓·魯什在那兒,一天晚上他們開始為一件毫無意義的事情爭吵。莫蘭對他們說:“需要睡覺!如果你們要吵架,請等到明天,可以在攝像機前打起來。”於是他們吵架的聲音小了一點,等第二天到了碼頭,讓他們大聲吵架。當然,這有點強迫性質,但是莫蘭和相信他們在攝像機前面說的話有90%是絕對真誠的,在那90%裡面至少有10%的話是他們以前從來不會說給對方的。決不!決不!決不!決不!電影能夠提供的不尋常的借口就是,只要你願意,在攝像機前可能說任何事情,而之後只要解釋為這是“為了電影”就夠了。表現出自己的一面卻當做是在飾演角色,而事後卻可以不承認,因為這只是自己的一個形象,這種非同尋常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第一,“鬧劇式的”人為自覺意識;
第二,自我反省以及展示某些隱藏的自我,而所展示的部分自己可能從未意識到;
第三,對於藉由這種展示來定義的角色,自我通過接近於有意識的嘗試將其演繹出來,並且將電影作為借口解決其中包含的若干問題。
人們有機會將構成他們本質存在的要素以一種心理戲劇的形式展現出來,如果攝影機不在場的時候他們怎麼辦經常考慮這個問題,知道沒有權利這樣做。真的,相信沒有這個權利,因為一旦你開始了這樣一件事,不僅給予人們可能來表現隱含在他們內心從未表現出來過的人物性格,而且還應該讓他們生活在這個角色之外。當然,電影在進行的同時,生活也沒有停止。它仍在繼續。
可以使用這種技巧幫助那些想將自己內心的一切抒發出來的人們,而且除此之外,他們沒有其他解決自身問題的辦法;或者,你可以使用這種手法講述純凈無瑕、簡潔樸實的小說——故事,並且隨著故事的結束,整部小說也將終結。
直接電影或者真理電影兩種可能的發展方向:
其一是當有重要事件發生時去記錄現實,比如時代的問題等

《冷酷的世界》
第二種方向是利用這些技術轉向虛構,一方面通過虛構來編造故事,另一方面又要防止你的觀眾完全沉浸其中。這是剛開始探索的方向。
用這些技巧來虛構,再給觀眾看真實,就會認為那些也是虛構的。其實早就明白這一點了,事實上,並沒有什麼理由說明為什麼不能用虛構來搭建影像的“真實感”。儘管謝萊·克拉克(Shirley Clarke)在她的《冷酷的世界》(The Cool World)中運用了非常接近於利科克的那些手法,但她從來沒有想過要刻意地通過某種“嚴謹”的講述方式來證明告訴是一個真實的故事,電影所深深打動。當一位導演具有了這樣一種誠實的態度:坦白地告訴他給看的是一個拍攝出來的真實——雖然這不是一個真實的事實,但它卻是一個真實的產物一就像一些人在《巴黎的秘密》里嘗試去做的那樣——那麼不認為有什麼理由阻止這位導演運用他所希望的任何技巧,為了讓一個故事達到最大可能的真實所作的一切努力,這並沒有什麼錯。電影經常被用來重現發生在某個並非攝製時間、空間里的真實情況,用這種方法攝製的西部片也一定會很好看。所以,像利科克那樣從哲學角度對運用這些技巧進行批判是荒謬的。說白了,這就是這個行業如何去界定誠實的度的問題。當你拍攝《正義的橄欖樹》(Les Oliviers de la Justice)時你不能說是在“報道”阿爾及利亞,你是在講述一個故事,並且運用一些這種技巧使它更貼近於某種真實,某種在你看來體現了那個時代的基本元素的真實。沒人會認為你是在對撒謊。
讓·魯什從往兩個方向發展:
技術來記錄真實
其一是用技術來記錄真實。舉個例子,在《獵獅者》 (The LionH unters)中試圖用影像和聲音來更接近事實——那簡直困難得可怕
嘗試講一個故事
第二種方向是嘗試講一個故事,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即興創作,總之,是很隨機的。在這個方向上可能是受了超現實主義的影響。事件的偶然性是其本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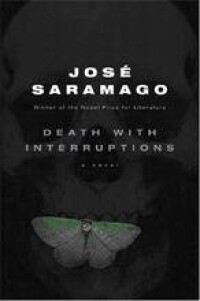
《獵獅者》
過去就是明天。只有當人們對明天進行創造的時候,過去才會有價值。而明天,人們將給予這些至今仍認為可以接受一個政府並且應該追隨這個政府的年輕人一些什麼贊成即使冒著生命危險也要進行徹底反抗。

讓·魯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