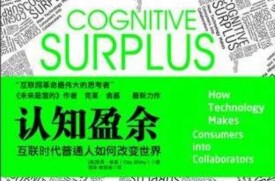認知盈餘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12月20日出版
《認知盈餘》是2011年12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社的中譯圖書,作者是克萊·舍基。主要講述隨著在線工具促進了更多的協作,人們該怎樣學會更加建設性地利用自由時間和閑暇來從事創造性活動,而不僅僅是消費。
克萊·舍基說,美國人一年花在看電視上的時間大約2000億個小時,而這幾乎是2000個維基百科項目一年所需要的時間。如果我們將每個人的自由時間看成一個集合體,一種認知盈餘,那麼,這種盈餘會有多大?我們已經忘記了我們的自由時間始終屬於我們自己,我們可以憑自己的意願來消費它們,創造它們和分享它們,我們可以通過積累將平庸變成卓越。
《認知盈餘》編輯推薦:看自由時間如何成就“有閑”世界,看克萊·舍基如何引領“有閑”經濟與“有閑”商業的未來。《認知盈餘》作者克萊·舍基被譽為“網際網路革命最偉大的思考者”,他對網際網路給人類所帶來的行為舉止以及文化的變遷洞若觀火。其作品《未來是濕的》曾在國內掀起閱讀風潮,《認知盈餘》一書在國內尚未正式出版,就得到包括騰訊CEO馬化騰在內的社會各界讀者一致關注。
《認知盈餘》可以說是《未來是濕的》一書的續篇。《未來是濕的》關注的是社會化媒體的影響。
克萊·舍基(Clay Shirky)(1964年-)研究網際網路技術的社會和經濟影響的美國作家,顧問和老師。近年來,舍基在紐約大學的(NYU)互動電信項目中任教,其諮詢客戶包括諾基亞、寶潔、BBC、美國海軍和樂高公司等。此外,舍基的課程報告還包括社會性網路和技術網路的拓撲結構之間相互關聯的影響,以及網路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
從1996年起,舍基開始撰寫關於網際網路的報道,其專欄文章和著作刊登在 Business 2.0《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商業評論》和《連線》雜誌等多家媒體。
其代表作《未來是濕的》在中國讀者中亦深受好評。
| 推薦序 網際網路時代的晨光 |
| 推薦序 網際網路時代的晨光 |
| 譯者序 認知盈餘作為一種可能 |
|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新媒介批評者 胡泳 |
| 第1章 當自由時間累積成認知盈餘 |
| 美國人一年花在看電視上的時間大約為2000億個小時,這幾乎是2000個維基百科項目每年所需要的時間。想像一下,如果我們將全世界受教育公民的自由時間看成一個集合體,一種認知盈餘,那麼,這種盈餘會有多大?我們已經忘記了我們的自由時間始終是屬於我們自己的,我們可以憑自己的意願來消費它們,我們可以通過積累將平庸變成優秀,而真正的鴻溝在於什麼都不做和做一些事情。 |
| 第2章 工具賦予的可能性 |
| 當韓國民眾在首爾市中心展開轟轟烈烈的的示威遊行時,誰也不會想到,在遊行中,一半以上的參與者,竟然都是十幾歲的小女孩兒。是什麼讓這些年幼到連選舉權都沒有的小姑娘接連數周,夜以繼日地出現在公園裡抗議?對認知盈餘的利用使人們得以用更慷慨、更公開、更加社會化的方式來表現自己。現在,除了時間,我們還擁有任由我們支配的工具,並不是我們的工具塑造了我們的行為,但是工具賦予了行為發生的可能。 |
| 第3章 分享,無酬的動機 |
| 為什麼“葛洛班之友慈善組織”的參與者不僅沒有報酬,還會搭上自己的錢,卻樂此不疲?為什麼一群業餘愛好者做的連專業設計師的作品的邊兒都夠不著的網站,會風靡美國?網路意味著我們最終發現,人們真正感興趣的領域是如此之廣闊,廣闊到瘋狂的地步。數字網路讓分享變得廉價,讓全世界的人都成為潛在的參與者。想要分享的動機才是驅動力,而技術僅僅是一種方法。 |
| 第4章 “我們”為“我們”創造機會 |
| 20世紀70年代,一群自稱“西風少年”的滑板玩家,創造了現代滑板文化;19世紀70年代,印象派畫家的團體聚在一起,通過互動產生出新洞見;音樂分享軟體Napster的發明,既不是因為青年們比老一輩更加有犯罪傾向,也不僅是因為他們胸懷分享的偉大精神。將我們的自由時間和特殊才能匯聚在一起,共同創造,做有益之事,構成了這個時代巨大的新機遇之一。誰能充分利用這一機遇,誰就能就能改變人們的行為方式。 |
| 第5章 創造慷慨的共享文化 |
| 當日托中心對接孩子遲到的家長增加了罰金,遲到的家長沒有減少反而增多了;同樣靠酒精燈和天平起步,“無形學院”卻能從鍊金術飛躍到正兒八經的化學學科;“同病相憐”網站不再是醫務人員單方持有信息,不讓病人知道,而是讓患有相同慢性病的病友分享信息,人人受益。有些價值是市場創造不出來的,這些價值的創造只能靠一系列分享和相互協調性的假設,當更多人開始期待業餘參與作為一種開放的選擇時,這些期待就會改變文化。 |
| 第6章 從公用價值到公民價值 |
| 一個是“沙發旅行”網站,一個是“粉色內衣”運動,前者為寄宿在他人家中的女士提供參考,後者則以一種公開的女權姿態保護婦女的利益。從面向參與者的公用價值,到受益對象是所有女性的公民價值,兩者大不相同。作為人類,無可救藥地既想滿足個人的需求,又想實現集體的效率,全心全意致力於為社會或公眾服務的團體很難長久維持。從個人、群體到公眾、社會,我們在多大程度上願意利用認知盈餘來創造真正的公民價值? |
| 第7章 尋找滑鼠,世界是“閑”的 |
| 一個四歲的小女孩在看DVD,突然她毫無徵兆地從沙發上跳起來,圍著屏幕背後的電線繞來繞去。爸爸問:“你在做什麼?”小姑娘從屏幕後方探出頭來說,“我在找滑鼠。” “我們在尋找滑鼠”,後來成了我的座右銘。我們四處尋找讀者、觀眾、患者或者市民,他們有的被鎖在創造和分享之外,有的享受著消極的或被禁錮的經驗,我們發出叩問:如果我們能開鑿出一點點認知盈餘,加以利用,我們能讓好事發生嗎?我敢打賭,答案是肯定的。 |
認知盈餘作為一種可能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新媒介批評者胡泳
自由時間的利用
克萊·舍基很高產,2008年出版了《未來是濕的:無組織的組織力量》,僅隔兩年,又推出一部力作《認知盈餘:互聯時代的創造與慷慨》。
《認知盈餘》可以說是《未來是濕的》一書的續篇。《未來是濕的》關注的是社會性媒介的影響;而《認知盈餘》的核心主題是,隨著在線工具促進了更多的協作,人們該怎樣學會更加建設性地利用自由時間也即閑暇,來從事創造性活動而不僅僅是消費。用舍基自己的話來說:“本書從上一本書遺留的地方開始,觀察人類的聯網如何讓我們將自由時間看待成一種共享的全球性資源,並通過設計新的參與及分享方式來利用它們。”該書進而分析了這些嶄新的文化生產形式背後的路徑和動機,它們無一例外地與人類的表達相關。
舍基對傳統媒體在相當程度上採取了鄙夷的態度,他認為,哪怕是網上最愚蠢和瘋狂的創造和分享的舉措(例如彙集數千張“大笑貓”的圖片)也比坐在電視機前被動消費數以千億計小時的節目強。(根據舍基的統計,美國人一年花在看電視上的時間大約兩千億個小時。)
認為新媒體與傳統媒體判若鴻溝的人通常也強調代際的變化。舊媒體對新媒體感到不安,很大程度上緣於上一代人對年輕人所擁有的新科技感到不安,尤其是上一代人對於已進入年輕人文化核心的新媒體感到不安。從過去媒體恐慌症的歷史(如漫畫、搖滾樂、電子遊戲機、電視等等)來看,大人對網路內容的一切恐懼,不過是來自於對孩子自主與自行界定媒體品味需求的不安感。比如,年輕人接受遊戲,而年長的人則大多拒絕它。一旦年輕人長大,年長的人逝去,遊戲也會像昔日的搖滾樂成為無足爭論之事。所以,反對遊戲的人不僅需要面對事實,還需要面對歷史。
舍基這樣的新媒體鼓吹者一般堅信,歷史站在自己的一邊。他觀察到,在電視歷史上首次出現了一部分年輕人看電視的時間少於他們父輩的現象。擁有更快捷的互動媒介的年輕一代正在把他們的行為從單純對媒介的消費中轉變過來。甚至當他們觀看在線視頻的時候,看似和電視沒什麼兩樣,但他們卻有機會針對這些素材發表評論、分享、貼上標籤、評分或者排名,當然還可以和世界上其他的觀眾一起討論。這個區別實際上是參與同圍觀的區別:參與者會給反饋,而圍觀者不會。對參與社區的人們來說,電影、書籍和電視劇創造的不僅是一種消費的機會;它們創造的還是一種回應、討論、爭辯甚至創造的機會。舍基把媒介消費的這種轉變稱為凈的“認知盈餘”。
導致媒介消費量減少的選擇可以是微小的,同時又是龐大的。微小的選擇是一種個人行為;某人只是簡單地決定下一個小時要用來創造一些事物,而不是單純地看電視。然而數以百萬計的微小選擇的集合最終可能導致龐大的集體行為。全世界的認知盈餘太多了,多到即使微小的變化都能累積為巨大的結果。
而一旦改變了認知盈餘的使用方法,我們將不得不重新界定“媒介”(media)這個詞能代表什麼。媒介在過去意味著一種商業的集合,今天,由於我們不僅消費,也創造和分享,並且我們還有能力彼此聯繫,所以,媒介正從一種特殊的經濟部門轉變為一種有組織的廉價而又全球適用的分享工具。
舍基最愛講的故事是一個四歲小姑娘的軼事。他在公開演講中提過這個故事,在本書中它也出現了,甚至成為本書最後一章的標題:“尋找滑鼠”。這個故事是這樣的:舍基的一位朋友和他四歲的女兒一起看DVD。電影放到一半時,小姑娘毫無徵兆地從沙發上跳起來跑到電視機屏幕背後去。他的這位朋友以為她想看看電影里的演員是不是真的躲在屏幕背後。但是這並不是小姑娘要找的。
小姑娘圍著屏幕後面的電線繞來繞去。她爸爸問:“你在做什麼?”小姑娘從屏幕後方探出頭來說,“找滑鼠。”這個故事可以再一次看出舍基對年輕人使用新媒體的方式寄予的厚望:年輕人足以開始吸收身處的文化,但是對其文化的前身卻知之甚少,所以完全不必受過去的媒介文化的污染。
消費、創造與分享
關掉電視的人幹什麼呢?年輕人越來越多地用電腦、手機和其他聯網設備取代電視。這並非簡單的硬體轉移,而是用戶習慣的重大遷移:人們現在可以一起做很多更有用、更好玩的事情了。舍基在書中列舉了大量協同行動的例子,比如維基百科的編纂就是他最愛引證的證據之一,還有些例子聽上去頗有些匪夷所思:在韓國民眾持續抗議進口美國牛肉的事件當中,一群某個韓國男孩樂隊組合的少女粉絲通過在網上的鬆散聯繫,竟然幾乎迫使政府下台。
對舊媒體、舊機構做事方式的憎厭,對新技術的擁抱以及對下一代年輕人的期許,所有這些混合起來,導致舍基傾向於講述從電視中解放的社會革命故事的一半:在《認知盈餘》中,以及在更早的著作《未來是濕的》裡面,舍基筆下的幾乎所有網路集體行動都是積極的,每個人似乎都在使用網際網路令我們這個世界變得更加美好。對於這樣的論證方式,那些反技術決定論者當然也會樂於舉出成打的例子,證明數字科技在生活品質的創造上,其摧毀能力大於貢獻能力。
舍基的另外一個問題是,他低估了文化消費的價值。在網路上創造愚蠢的東西的價值,果真高於比如說閱讀一本複雜的偵探小說?是不是只要是創造就擁有了某種神聖性,而只要是消費就顯示了低級智慧?美國的文化批評家史蒂文·約翰遜在他2005年出版的著作《壞事變好事》(Everything Bad Is Good for You)中,曾以遊戲和電視劇為例,直接向下述說法發起挑戰:大眾文化是一種致人愚蠢的東西。
例如,約翰遜爭辯說,情節簡單、黑白分明的電視劇早已失去市場,今天再看《豪門恩怨》,我們會十分驚異於它的天真做作。現在的電視劇敘述線索紛繁錯亂,人物曖昧難明,常常含有需要觀眾主動填補的隱喻空間,要靠觀眾自行猜測人物與事件、人物與人物之間的關係。甚至連真人秀節目都在調動觀眾的預測性想象。在這種情況下,電視也和遊戲一樣,向人們提出了更高的認知能力上的要求。由此,大眾文化使現代人變得聰明了,而不是相反。
約翰遜的結論很難說是證據充足的,但同樣應該指出,責難大眾文化消費對大眾的頭腦充滿損害性,也並不完全站得住腳。舍基低估了創造性生產的質量問題——平庸是創造性生產的供應增加所必然帶來的副作用。由此,我們是不是可以確定,消費一些偉大的文化產品,要勝於創造另一隻“大笑貓”?
在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到舍基犯了其他媒介消費的批判者(比如說波茲曼)所易犯的同樣毛病:我們不需要引用德里達的觀點也可以知道,文本閱讀本身就是一個創造性行為,我們必須不斷地向字句的模糊性之中注入意義。頭腦在這裡並不是簡單地被浪費;我們要懷疑舍基對於創造的定義:並不是只有我們的想法結晶為物理的或者可見的剩餘物才算是創造。況且,在我們真正創造出任何有意義的產物之前,我們必得經歷一個消費和吸收的過程,並對我們所消費和吸收的進行思考。這也就是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所言,我們必須先變成啜飲一切水的駱駝,才會成為獅子。
當然,只要舍基不把他對媒介和認知盈餘的觀察弄得那麼兩極化,這些批評其實也是無的放矢。舍基正確地指出,人們使用媒介具有三種目的:消費、創造與分享。二十世紀的媒介作為一種單一事件發展著:消費。但眼下我們正在越來越多地創造和分享媒介,這是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情。不過,消費的行為並不會全然消失,甚至會繼續扮演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