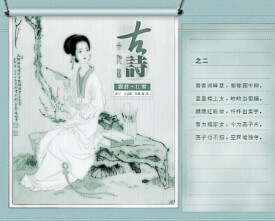青青河畔草
漢代文人五言詩
《青青河畔草》是產生於漢代的一首文人五言詩,是《古詩十九首》之一。此詩運用了第三人稱的寫法,寫出了少婦渴望愛情,渴望夫妻相依相偎,甚至舉案齊眉的平凡生活。此詩結構直中有婉,虛實相映;描寫細膩,突出細節;運用疊詞,富有情韻。
青青河畔草
青青河畔草,鬱郁園中柳。
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
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
昔為倡家女,今為盪子婦。
盪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
⑴鬱郁:茂盛的樣子。
⑵盈盈:形容舉止、儀態美好。
⑶皎皎:皎潔,潔白。牖(yǒu):古建築中室與堂之間的窗子。古院落由外而內的次序是門、庭、堂、室。進了門是庭,庭后是堂,堂后是室。室門叫“戶”,室和堂之間有窗子叫“牖”,室的北面還有一個窗子叫“向”。上古的“窗”專指在屋頂上的天窗,開在牆壁上的窗叫“牖”,后泛指窗。
⑷娥娥:形容女子姿容美好。《方言》:“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
⑸倡家:古代指從事音樂歌舞的樂人。《說文》:“倡,樂也,就是指歌舞妓。”
⑹盪子:即“遊子”,辭家遠出、羈旅忘返的男子。《列子》里說“有人去鄉土游於四方而不歸者,世謂之為狂盪之人也”可以為證。
河邊的草地草兒青綠一片,園中茂盛的柳樹鬱鬱蔥蔥。
站在綉樓上的那位女子體態盈盈,她靠著窗戶容光照人好像皎皎的明月。
她打扮得紅裝艷麗,伸出纖細白嫩的手指扶著窗兒向遠方盼望她的親人。
從前她曾經是個青樓女子,她希望過上正常人的生活才成了遊子的妻子。
不想遊子遠行在外總是不回來,丟下她一個獨守空房實在難以忍受寂寞。
此詩是代思婦設想的閨怨之作,是《古詩十九首》之一。關於《古詩十九首》的時代背景有多種說法。宇文所安認為中國早期詩歌是一個複製系統,找不到“古詩”早於建安時期的確鑿證據。木齋提出《古詩十九首》及建安詩歌的重要組成大部分詩作是曹植之作。李善注《昭明文選·雜詩上》題下注曾釋之甚明:“並雲古詩,蓋不知作者。”並認為作於東漢時期,這也是二十世紀以來的主流觀點。今人綜合考察這十九首詩所表現的情感傾向、所折射的社會生活情狀及其純熟的藝術技巧,一般認為並不是一時一人之作,其所產生的年代應當在東漢獻帝建安之前的幾十年間。至於《青青河畔草》的具體創作時間,則難以確考。
此詩敘述的是一個生活片斷,大致描述如下:女主人公獨立樓頭,體態盈盈,如臨風憑虛;她倚窗當軒,容光照人,皎皎有如輕

青青河畔草
此詩寫的就是這樣一個重演過無數次的平凡的生活片斷,用的也只是即景抒情的平凡章法、“秀才說家常話”(謝榛語)式的平凡語言;然而韻味卻不平凡。能於平凡中見出不平凡的境界來,就是此詩——也是《古詩十九首》——那後人刻意雕鐫所不能到的精妙。
這首詩其實就是一首歌詞,是能夠歌唱的詩句,也是《古詩十九首》中唯一使用了第三人稱敘說的形式。
詩的結構看似平直,卻直中有婉,極自然中得虛實相映、正反相照之妙。詩境的中心當然是那位樓頭美人,草色柳煙,是她望中所見,但詩人——他可能是偶然望見美人的局外人,也可能就是那位遠行的盪子——代她設想,則自然由遠而近,從園外草色,收束到園內柳煙,更匯聚到一點,園中心那高高樓頭。自然界的青春,為少婦的青春作陪襯;青草碧柳為艷艷紅妝陪襯,美到了極至。而唯其太美,所以篇末那突發的悲聲才分外感人,也只是讀詩至此,方能進一步悟到,開首那充滿生命活力的草樹,早已抹上了少婦那夢思般的哀愁。這也就是前人常說的《十九首》之味外味。如以後代詩家的詩法分析,形成前後對照,首尾相應的結構。然而詩中那朴茂的情韻,使人不能不感到,詩人並不一定作如此巧妙營構,他,只是為她設想,以她情思的開展起伏為線索,一一寫成,感情的自然曲折,形成了詩歌結構的自然曲折。
詩的語言並不經奇,只是用了民歌中常用的疊詞,而且一連用了六個,但是貼切而又生動。青青與鬱郁,同是形容植物的生機暢茂,但青青重在色調,鬱郁兼重意態,且二者互易不得。柳絲堆煙,方有鬱郁之感,河邊草色,伸展而去,是難成鬱郁之態的,而如僅以青青狀柳,亦不足盡其意態。盈盈、皎皎,都是寫美人的風姿,而盈盈重在體態,皎皎重在風采,由盈盈而皎皎,才有如同明月從雲層中步出那般由隱綽到不鮮的感覺,試先後互易一下,必會感到輕重失當。娥娥與纖纖同是寫其容色,而娥娥是大體的讚美,纖纖是細部的刻劃,互易不得。六個疊字無一不切,由外圍而中心,由總體而局部,由朦朧而清晰,烘托刻畫了樓上女盡善盡美的形象,這裡當然有一定的提煉選擇,然而又全是依詩人遠望或者懸想的的過程逐次映現的。也許正是因為順想象的層次自然展開,才更幫助了當時尚屬草創的五言詩人辭彙用得如此貼切,不見雕琢之痕,如憑空營構來位置辭藻,效果未必會如此好。這就是所謂“秀才說家常話”。
六個疊字的音調也富於自然美,變化美。青青是平聲,鬱郁是仄聲,盈盈又是平聲,濁音,皎皎則又為仄聲,清音;娥娥,纖纖同為平聲,而一濁一清,平仄與清濁之映襯錯綜,形成一片宮商,諧和動聽。當時聲律尚未發現,詩人只是依直覺發出了天籟之音,無怪乎南朝鍾嶸《詩品》要說“蜂腰鶴膝,閭里已具”了。這種出於自然的調聲,使全詩音節在流利起伏中仍有一種古樸的韻味,細辨之,自可見與後來律調的區別。
六個疊詞聲、形、兩方面的結合,在疊詞的單調中賦予了一種豐富的錯落變化。這單調中的變化,正入神地傳達出了女主人公孤獨而耀目的形象,寂寞而煩擾的心聲。
這位詩人不可能懂得個性化、典型化之類的美學原理,但深情的遠望或懸想,情之所鍾,使他恰恰寫出了女主人公的個性與典型意義。這是一位倡女,長年的歌笑生涯,對音樂的敏感,使她特別易於受到陽春美景中色彩與音響的撩拔、激動。她不是唐代王昌齡《閨怨》詩中那位不知愁的天真的貴族少女。她凝妝上樓,一開始就是因為怕遲來的幸福重又失去,而去痴痴地盼望行人,她娥娥紅妝也不是為與春色爭美,而只是為了伊人,痴想著他一回來,就能見到她最美的容姿。因此她一出場就籠罩在一片草色凄凄,垂柳鬱郁的哀怨氣氛中。她受苦太深,希望太切,失望也因而太沉重,心靈的重壓,使她迸發出“空床難獨守”這一無聲卻又是赤裸裸的情熱的吶喊。這不是“悔教夫婿覓封侯”式的精緻的委婉,而只是,也只能是倡家女的坦露。也唯因其幾近無告的孤苦吶喊,才與其明艷的麗質,形成極強烈的對比,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詩人在自然真率的描摹中,顯示了從良倡家女的個性,也通過她顯示出在遊宦成風而希望渺茫的漢末,一代中下層婦女的悲劇命運。這就是個性化的典型性。
現代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第一卷:“這是思婦中春光明媚的季節經受不住寂寞,發出的感嘆。”
現代李錦文《古詩十九首評析》:“本篇寫一個妓女從良后卻嫁給了一個遊子,這個遊子遠離家鄉很久不回來,使得她獨守空房,這種日子實在難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