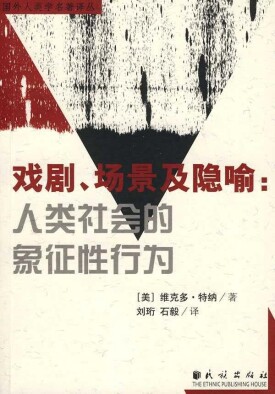象徵人類學
象徵人類學
象徵人類學(Symbolic anthropology),有時或稱象徵與闡釋人類學〈symbolic and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是文化人類學主要學派之一,主要人物有克利弗德·紀爾茲(Clifford Geertz)、維克多.透納〈Victor Turner〉與大衛.許柰德(David M. Schneider)等。象徵人類學興起於1960年代,其視文化為一套由象徵與意義構成的象徵體系,因此人類學家必須視異文化為文本,藉由田野調查等長時間的研究方式,解讀並細膩地詮釋當地文化。雖然象徵人類學家對文化的概念主張各有不同,一般而言其主張觀點與結構主義人類學相似,與文化唯物論的看法相對,同時也反對結構功能論等人類學家對於親屬等結構性研究的觀點與主張。在後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中,象徵人類學的文化概念往往成為其質疑與批判的對象。
如同其他人類學派,象徵人類學的理論基礎建立在其文化理論的討論之上。雖然象徵人類學強調象徵在文化里的角色,以及個人與文化之間的相互關係,然而由於對文化與個人的角色解釋不同,其文化理論可大略分成“紀爾茲”與“透納”兩種理論取向。
一、象徵人類學的形成
象徵(symbol,又譯作“符號”)是人類重要的表達方式。人類學對象徵研究的歷史由來已久,率先進行象徵研究的是法國社會學年鑒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塗爾干的弟子———羅伯特·赫爾茲,他的《右手的優越———一項關於宗教兩極性的研究》開創了兩元對立象徵研究的先河,並對後世的如羅德尼·尼達姆、瑪麗·道格拉斯和愛德蒙·利奇等人的結構象徵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象徵人類學(又譯“符號人類學”)產生於英國和美國人類學界。其形成的學術背景是對盛極一時、影響人文學科多學科的結構主義思潮開始質疑,人類學家對人類學的理論範式、使命和方法論的等一系列問題重新進行思考。在象徵人類學家看來,文化不是封閉在人的頭腦中的東西,而是通過象徵手段來表達的意義系統,人們對於其周遭環境和社會其他成員的行為和言語的理解和解釋會在社會成員中間構成一個共享的文化意義系統,而象徵人類學家的主要任務就是研究這些人們為了表達關於社會生活的根本性問題而賦予意義的象徵和象徵過程。象徵具有多重意義,人們在共同的社會交往中創造並使用象徵。對於不同文化的認識要求我們區分其中的不同象徵,認識它們的意義,並研究它們如何結合體系並進而對行動者的世界觀、精神和感知產生影響。
作為“后結構人類學”的一種,象徵人類學一方面延續了結構主義人類學對象徵符號的關注,一方面又在研究的出發點、主旨和研究方法上與結構主義人類學有著截然的不同。對於象徵符號研究,結構主義人類學的出發點是人類普同性;象徵人類學的出發點則是文化相對性。結構主義的研究主旨是通過對象徵符號的研究發現“文化的深層語法結構”,注重的是具有普遍性質的、屬於心理範疇的世界觀;而象徵人類學家的研究主旨則是通過對構成文化體系的象徵的意義的理解和解釋,探討該文化所獨有的、屬於意識形態範疇的“社會情感”和“社會心理”。在研究方法上,結構主義人類學採取的是從研究者的、文化外部的視角來研究的“客位的”研究方法;象徵人類學採取的是從被研究者的、文化內部的視角來研究的“主位的”的研究方法。
二、象徵人類學主要代表人物的觀點
象徵人類學派的最主要、也最有影響的代表人物是克利福德·格爾茨、維克多·特納和大衛·施耐德等,他們在對文化與象徵的研究上雖有上述一些共識,但是由於秉承的傳統和所受的影響不同,他們的學術主張在這些共識之上還有很多不同。
在對象徵、文化和人類學的實質和它們的相互關係的認識上,格爾茨認為象徵符號是指“作為觀念載體的物、行為、事項、性質和關係———觀念是象徵的‘意義’”;文化是指“從歷史沿襲下來的體現於象徵符號中的意義模式,是由象徵符號體系表達的傳承概念體系,人們以此達到溝通、延存和發展他們對生活的知識和態度”。文化的各個層面,如宗教、藝術、常識、法律、意識形態等都可以說是一種文化系統。受馬克斯·韋伯的影響,格爾茲認為人是懸掛在由他們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上的動物,文化便是這張“意義之網”,因而作為對文化的分析的人類學不是一種探索規律的實驗科學,而是“一門尋求意義的闡釋學科”。
在對文化象徵體系的研究取向上,格爾茨強調“對其他的民族符號象徵體系的系統闡述必須以行動者為取向”,強調從“文化持有者內部視角”分析文化。格爾茨對象徵、文化和人類學本質的探討,對文化研究的“深描”方法的提倡,和對文化研究的行動者取向的強調,已經廣泛影響到了文化研究的各個領域,除人類學外,還在哲學、語言學、宗教研究、文學批評等各方面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相對象徵人類學的另外兩位重要代表人物格爾茨和施耐德所受的美國文化人類學傳統的熏陶,特納的學術思想更多的受到英國社會人類學傳統的影響,較之前兩者對象徵與文化的關係的關注和在象徵人類學理論體系的建構方面的建樹,特納的學術貢獻更多的表現在他通過具體生動的民族志寫作所闡釋的關於儀式和象徵與社會的關係。
在儀式研究理論方面,特納更多的受到杜爾干社會學和結構—功能主義的影響,側重於從儀式的象徵解釋中去把握特定社會秩序的再生,關注儀式的結構與功能,但是他所關注的並非靜態的儀式結構與功能,而是把儀式放在運動的社會過程中加以考察,重在把握儀式在整個社會運作過程中的功能。在特納看來,儀式對於社會並不是像塗爾乾和功能論者拉德克利夫·布朗所認為的那樣是單純的凝聚和整合作用,因此他的分析更多的關注儀式在社會衝突和成員身份變動所發揮的作用。特納的《儀式過程》一書以恩丹布人為對象,將儀式在這個群體中的地位進行了詮釋,並發展了范·根納普提出的通過儀式理論。根納普認為,所有“伴隨著地點、狀態、社會位置和年齡的每一次變化而舉行的儀式”都是通過儀式,可以分為分離、閾限和聚合三個階段。特納拓展了“閾限”與“交融”的概念,用一個專門的拉丁文術語“communitas”(拉丁語,意為“交融”、“共同體”)來描述他所認為的通過儀式的閾限(中介)階段的特點,即非結構性、平等和人的相關性。這樣,通過儀式就可以被看作是從結構到反結構,然後再回到結構的運動,社會則可以被看作是交融與結構的辯證統一。特納的這一儀式分析模式不僅可以用來分析與個人成長有關的通過儀式,還可以用來分析生命危機儀式、年度性儀式和宗教儀式等諸多儀式。
施耐德的學術思想集中體現在他於1968年出版的《美國的親屬制度:一種文化的解說》一書中。在人類學史上,這本書既是象徵人類學的一部重要的代表作,也是西方人類學回歸本土研究的典範。親屬制度是傳統人類學研究的重要領域,在這一領域中,人類學家們運用關係稱謂來分析研究對象現實中存在的權利義務關係,並認為依據親屬制度締造的社會是非西方的文化特色。在這部民族志著作中,施耐德將研究的視角投射到了他自身所在的西方文明社會,他通過對芝加哥白人中產階級的調查和綜合分析,系統地闡述了美國人關於何為個人和何為親屬的觀念,以及他們如何看待血緣和性別與生物學、自然與法律、物質與符碼的觀念。在該書中,施耐德首次嘗試將親屬制度作為一個象徵和意義體系來系統的分析,而不是簡單的將它視為有著功能性的內部家庭角色的網路來看待。他認為親屬制度並不是一個建立在血緣基礎上的自然體系,因此也並不是一個存在於各文化間的基本一致的體系,而是一個因群體的不同而不同的文化體系。對一個像他自身的文化那樣高度分化的社會的研究,對於了解親屬制度的本質,要比人類學家對於那些他們所熟知的尚未分化的社會的研究更有啟發意義。他通過簡短而風格化的敘述和分析,提出了他對親屬制度的不同看法,指出西方人類學家長期用來“反映”非西方社會關係體系的親屬制度概念,並非是他們從對非西方社會的研究中提煉出來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分析概念”,而實際上是將源自西方社會內部並在當代美國人的生活中仍然在被運用著的文化建構映射到了對非西方的社會的研究中。施耐德的《美國親屬制度》最大的貢獻之一,就是發展了一種關於文化的理論,這一理論既是他分析論證的基礎,也在此後日益證明其對其他文化分析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