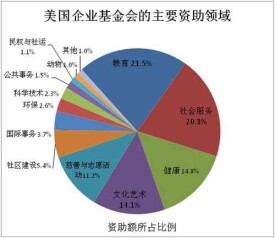美國基金會
美國基金會
美國基金會,英文名American Foundation,成立於1901年。以各種慈善為目標而運作的,掌握了巨大的社會財富和經濟力量,市場上的各種變化、國家政治、意識形態之中這些基金會的影響無所不在。
目錄
基金會既強壯又脆弱。當金融市場萎縮時,基金會不象其它非營利機構和企業那樣容易遭受經濟風暴的襲擊,而使其財產免受損失。其私人性質的、自我更新發展的董事會成員不受公眾選票的左右,沒有市場規則的限制,只有很低限度的政府規定和監督。然而,它們又是脆弱的。因為在一個民主社會,必須保持機構的合法地位,它們經常被懷疑為斂財、秘密決策、蔑視專家和空想的社會改革者。在本世紀,政府部門和市場的地位與作用都發生了變化,基金會也必須順應這些變化重新定位自己的作用。由於非營利部門的規模與形式均發生了變化(通常是基金會驅動的結果),基金會必須找到新的運營方式。從基金會採取的方法和策略講,美國基金會一直不是一種固定的機構形式;更深入地講,它們必須在不同的時代找到新的理由以保持自己的公共法律地位。
訓練有素的學者們提出了一系列理論證據,證明我們的社會對非營利機構,幾乎是很明確地對基金會的依賴。他們的闡述涉及經濟、政治理論:公共產品的供給、加強信託機構、提高機構效率和靈活性、保持多元化和多樣化、社會變革的深化、社會資本的提供,還有其它如公民社會的建設等等。隨著研究非營利部門的學者隊伍的擴大和基金會工作人員專業化水平的提高,這些理論見解在基金會項目官員考慮項目戰略和結果時就會得到一些回應。但是,此時的話語和見解已不同於一個世紀以前那些捐贈人及其顧問們最初思考基金會問題所使用的了。接下來,就是基於為數不多的檔案資料,簡略概括在不同時期基金會作為我們國家的一種機構存在的大概情況。
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捐贈人、顧問、基金會官員在籌劃他們的工作時是如何頻繁使用科學字眼兒為隱喻的。十九世紀末期,一批新的慈善活動在進行的時候,生物醫學提供了一個基於細菌理論的吸引人的概念。作為隱喻,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交替時,細菌理論對美國的慈善事業確實起了很大作用,在1890年代到1920年代影響了它的發展方向。細菌理論開始引導對社會現象的探求,幫助改變那些支持社會調查和社會行動的機構。路易·巴斯德的疾病細菌理論在實踐中的應用—衛生殺菌和疫苗—改變了醫學實踐和醫學研究的目的。細菌理論認為特定的疾病是由特定的作用物質引起的。隨著人們對各種疾病的逐漸了解和能夠治療,知識界認為細菌理論是超越各學科的科學,對於每一個問題,在明確原因與最終解決問題之間都存在著直接的聯繫。
十九世紀後期,那些思考社會問題的人不僅把細菌理論看做是找出疾病特定根源的希望,而且是一種思考和解決社會問題的醫學話語。細菌理論使慈善家和社會改革家有希望確信,長期存在的社會問題不僅可以通過科學的調查方法予以了解,而且能夠永久性地根除或防止其發生。有很多人使用這種新的生物醫學話語;洛克菲勒的顧問,曾為浸禮教牧師的弗里德里克T·蓋茨比大多數人對這種話語更有熱情、更充滿信心。 1897年的夏天,他大部分時間都埋頭於威廉·奧斯勒的教科書>。他後來談到假期的奇怪選擇時說,閱讀這本書“從一開始我就被它牽著鼻子,一頁一頁地往下看”。不久蓋茨就敦促洛克菲勒按照巴黎巴斯德研究院和柏林的克科研究院的模式建立一個美國研究機構,在這個機構中研究人員可以全力探究疾病的原因。洛克菲勒醫學研究院(建於1901年,現為洛克菲勒大學)和根除鉤蟲病衛生委員會的故事是很有名的。
蓋茨經常提到疾病與社會苦難的聯繫。最著名的一次是在洛克菲勒醫學研究院成立十周年紀念會上的演講:“疾病是各種弊端的根源,身體的、經濟的、精神的、道德的、社會的,…… 疾病與其相伴而隨的不幸毫無疑問是人類苦難的主要根源”。他抱怨:“世界上大部分慈善機構都認為自己直接或間接地在解除或緩解這些源於疾病的社會不幸和苦難。但是,儘管這些慈善機構的工作是必要的、美好的,卻不能使我們滿意。因為它們沒有觸及這些苦難和不幸的根源、沒有減少它的程度……。不幸的是,我們還沒有對疾病進行理智地、廣泛地和科學地研究,更沒有運用足夠的儀器和資源進行研究。我們對於疾病的起因和發病過程知之甚少,更不必說治癒了”。洛克菲勒響應蓋茨的話,他認為慈善是找出社會弊端根源的一種工具。他寫到
“最好的慈善就是不斷地尋找終極目的——找出原因,在其源頭根治弊端。”
細菌的隱喻對新型基金會的任務有暗示作用,不僅對洛克菲勒的慈善事業,對其它的大基金會也一樣。羅素·塞奇基金會的工作人員在開展項目工作時,疾病這個因素使他們考慮是否把肺結核作為城市困境的根源、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對婦女境況的調查,根據瑪麗·里士滿的研究,在失去丈夫的婦女中,近三分之二是由於肺結核、斑疹傷寒、肺炎或者瘧疾而造成的。結果,有的基金會著手研究特定的幾種疾病,並在幾十年前找到病因;有的把資金投向醫學研究和教育;有的把資源用於社會科學,使它能夠向生物醫學領域所表現的那樣成為科學、實用的學科;很多使研究人員緊密聯繫的新的研究機構建立了。這些促進了從醫學、公共健康到經濟學、社會學、政治科學很多領域的專業化和職業化。所有這一切——以直接參與預防項目為目的的大規模機構研究的模式——早在1913年就已開始了。當時,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執行秘書傑羅姆·格林曾講基金會作為一種機構應該象一所“人類需要大學”那樣運作,內部組織應比照大學的系;他強調:“科學研究的重要性應該貫穿慈善事
業”。
科學的隱喻作用就象沉積物一樣一層壓著一層。細菌的隱喻作用為新的科學思考奠定了基礎。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化學和物理學的成功促使卡內基、洛克菲勒和塞奇基金會更為關注量化技術和統計技術。卡內基基金會斥巨資投入國家經濟研究局的建立,而此時,塞奇基金會則成為社會調查運動的中心。對數字和方法的強調使人們意識到社會科學的進展要慢於自然科學。到1920年代,有的基金會高級官員甚至開始懷疑,他們是否對在社會經濟領域採取預防行動有足夠的了解。正如共同基金會懂事長巴里C·史密斯在1926年評估基金會項目時指出的,基金會“不但減少強調預防青少年犯罪,而且減少了強調對任何事情的預防”。
經濟大蕭條的襲擊更進一步損害了對社會科學研究的信心。1934年,洛克菲勒基金會指派的一個委員會對基金會項目進行評估, “如果嚴格定義,知識的進步,是非常有限的、範圍狹小的、目的性很強的”。基金會懂事長雷蒙德·福斯迪克對機會主義的政策提出質疑,尤其是在人類急需要幫助的時候還要奉行機會主義政策嗎?其實, 1930年代早期,一種新的隱喻開始滲透到基金會所使用的話語中。當時,人們在談論對精神失調和導致身體突然不適的系統平衡原因的探索。這些隱喻,多半兒來自物理學和相對新興的心理學原理。 1930年代早期,這些有關調節、平衡的隱喻開始了定義基金會工作方式的一個新時代。特別是在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社會科學項目中有關經濟穩定的問題中,平衡與調節話語不斷被使用。用基金會的埃德蒙E·戴的話說,經濟周期的起伏“是我們遭受的身體痛苦、疾病、精神錯亂、家庭分裂、犯罪、政治動蕩和社會不穩定的主要原因”。
如果基金會的任務是平衡和調節,那麼它的項目就必需是靈活的和機會主義的。 1934年,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評估委員會號召:“基金會的項目和組織均要有適應性,從而使基金會能夠對外界的變化及時作出調整……。如果要使我們的工作免於陳腐、如果我們要避免挫折和停滯,我們的項目就必需保持靈活、新穎、生命力並且是廣泛的”。平衡與調節的概念確定了基金會在經濟危機和二戰期間的態度,特別是,在其資源減少的情況下,轉向一系列政府緊急援助項目,最後徹底轉向聯邦政府為其確定的作用。
二次大戰結束后的幾年標誌著另一個慈善時代的開始。 1940年代後期,大基金會開始重新評價它們的項目。不久,福特基金會也加入到這些老的基金會中來了,福特基金會自1930年代就已經在進行具有地方色彩的密歇根慈善事業。但是,此時它們正在準備接受福特汽車公司的巨額股票。 1948年羅恩·蓋瑟被邀請探索福特基金會如何追求其提高人類福利的總目標時,該基金會已開始計劃戰後項目。 1945年和1946年洛克菲勒基金會的項目評價也已看到了戰爭的影響和慈善事業面臨的挑戰:“它對社會組織、知識機構和對人類信仰與規則的實質性的和巨大的破壞。戰前存在於所有領域的無數的自我調節平衡點現在已不起作用了;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在廣泛領域規範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規則也已經失去作用”。洛克菲勒基金會上下一致認為,基金會應該開始集中關注人類行為、使民主更為有效、加深國際間了解的方式等問題。
蓋瑟委員會關於福特基金會的報告也提到基本價值、自由、權利、社會責任;它從國際角度重新全面肯定了民主原則。福特基金會的國際項目致力於五大目標:通過國際的法律和公正制度維護世界和平;確保對自由與民主原則的忠誠;通過經濟增長提高全人類的福利;擴大對教育的贊助;增加關於管理人類行為的知識。蓋瑟委員會指出: “事實證明,今天的關鍵問題是社會性質的而非自然性質的——即這些問題產生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不是人與自然的關係。”
要從這些宏偉的目標來定義基金會後來的行動是有風險的。戰勝法西斯隨後而來的冷戰陰影,使修改戰爭剛結束時制訂的項目帶有明顯的政治價值取向。與此同時,基金會的活動也更為制度化。如果需要建立新的機構,那麼就建立;如果需要進行長期的職業培訓和教育,基金會會毫不猶豫地進行工作。所有這一切都基於半個世紀慈善事業經驗的積累和優秀基金會中工作人員專業化水平的提高。如果誰要用隱喻來描述戰後二十多年基金會的這些活動,那一定是工程學,在這門學科中,知識的實際應用是無與倫比的。還可能是頗有爭議的行為研究和系統分析,這兩門在戰爭中興起的學科,在戰後改變了政策思想庫和政府機構的行為方法。結果,基金會的作用經常是設計、建立和試驗綱領性的模型,然後這些模式被政府採納。
慈善事業的工程學時代隨著1969年稅法修正案的通過、 1973—1974年金融市場的崩潰,尤其是隨著人們對大規模政府參與喪失信心而結束。我們離這個時代太近了以至無法為其命名或者找出其結束的標誌。但是,我們可以詳述它的一些顯著特點。首先,處於世紀交替時期的基金會慈善事業似乎是通過研究和評價政策改革超越政治分歧的工具,對有些基金會來說,慈善事業成為自我意思很強的意識形態行為。明顯的意識形態界限使我們對專門知識的定義和基金會團體對以大學為基地的研究的資助更具影響。至少在社會和經濟舞台,基金會已經從過去構建知識的做法,轉變為通過以保守的法律和政治策略、賦予政治和
經濟權利(既從左的方面又右的方面)或者通過在很多領域的公共政策遊說來尋求一套促進社會公正的方法。
其次,基金會團體和整個非營利部門對於自己在做什麼都格外清醒。採取專業協會的形式,成立了基金會與獨立部門委員會,它是一個非營利研究的團體,在過去的十年裡迅速成長。與此同時,基金會面臨著承擔更多責任、評價和測量其工作成果的內外壓力。儘管承擔更大責任的壓力會使我們的時間視野狹隘、限制我們的想象力和預見能力,但是一種使這一切更為開闊的力量同時存在。隨著世界各國不斷開放市場和政治體制開始向民主制度邁進,人們也越來越意識到非營利部門在世界範圍內的重要性。無論是在亞洲、東歐或拉丁美洲,公民社會——這個詞兒是十八世紀發明的,在過去的十年裡被重新發現並被賦予新的意義——的出現使我們從新的視角思考基金會在不同的政治文化、不同的社會背景下的作用。我們基本上從兩個方面觀察美國基金會的歷史:慈善事業與政府(或者公制定共政策)的關係和慈善事業與專門知識的關係。公民社會的概念拓寬了基金會活動的公共領域的範圍,並迫使我們去研究基金會與市場的關係和基金會與不太正式的志願部門的關係。越來越多地使用“公民社會”這個詞兒是否意味著美國基金會的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它是否繼承了細菌理論時代、平衡與調節時期、工程學時代和意識形態慈善哲學時代?公民社會的概念能否幫助我們在歷史的長河之中找到一席位置?是否還有一種更鼓舞人心的慈善概念或者一種新的更具說服力的隱喻能推進我們的工作?對待這些問題,本文不可避免地帶有個人傾向。回答這些問題不僅是歷史學家的責任更是基金會工作人員在向捐贈人諮詢、向新的受託人和工作人員解釋基金會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時所面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