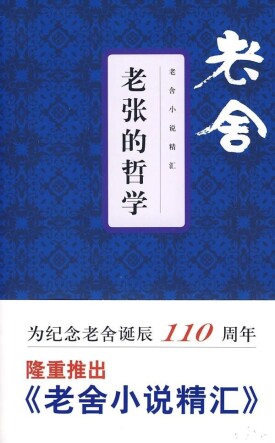共找到2條詞條名為老張的哲學的結果 展開
- 老舍長篇小說
- 同名話劇
老張的哲學
老舍長篇小說
徠《老張的哲學》描寫了20年代前後北京各階層市民的生活及思想感悟。主人公老張,是舊北京一個無惡不作的無賴惡棍。他身兼兵、學、商三種職業,信仰回、耶、佛三種宗教;他信奉的是“錢本位而三位一體”的人生哲學,“老張哲學”的內涵和實質是赤裸裸的市儈哲學。

老舍
抗日戰爭爆發後到武漢和重慶組織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對內總理會務,對外代表“文協”,創作長篇小說《四世同堂》,並對現代曲藝進行改良。1946 年赴美講學,四年後回國,主要從事話劇劇本創作,代表作有《龍鬚溝》(1950年)、《茶館》(1957年),榮獲“人民藝術家”稱號,被譽為語言大師。曾任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全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及北京文聯主席。1966年“文革”初受嚴重迫害后自沉於太平湖中。有《老舍全集》十九卷。
《老張的哲學》是老舍獨特藝術個性形成的一個起點。老舍的幽默有自己的特點,其作品中的幽默總帶著難以掩飾的或濃或淡、或隱或現的悲劇色彩,他的幽默是使人啼笑皆非的幽默,在微笑中藏著苦澀的幽默,是喚起人們同情的幽默,是具有豐富語言技巧的幽默。
老張的哲學是“錢本位而三位一體”的。他的宗教有三種:回,耶,佛;職業是三種:兵,學,商。言語是三種:官話,奉天話,山東話。他的……三種;他的……三種;甚至於洗澡平生也只有三次。洗澡固然是件小事,可是為了解老張的行為與思想,倒有說明的必要。
老張平生只洗三次澡:兩次業經執行,其餘一次至今還沒有人敢斷定是否實現,雖然他生在人人是“預言家”的中國。第一次是他生下來的第三天,由收生婆把那時候無知無識的他,像小老鼠似的在銅盆里洗的。第二次是他結婚的前一夕,自動的到清水池塘洗的。這次兩個銅元的花費,至今還在賬本上寫著。這在老張的歷史上是毫無可疑的事實。至於將來的一次呢,按著多數預言家的推測:設若執行,一定是被動的。簡言之,就是“洗屍”。
洗屍是回教的風俗,老張是否崇信默哈莫德呢?要回答這個問題,似乎應當側重經濟方面,較近於確實。設若老張“嗚乎哀哉尚饗”之日,正是羊肉價錢低落之時,那就不難斷定他的遺囑有“按照回教喪儀,預備六小件一海碗的清真教席”之傾向。(自然慣於吃酒弔喪的親友們,也可以藉此換一換口味。)而洗屍問題或可以附帶解決矣。
不過,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後肉價的漲落,實在不易有精密的推測;況且現在老張精神中既無死志,體質上又看不出頹唐之象,於是星相家推定老張尚有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之壽命,與斷定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後肉價之增減,有同樣之不易。
豬肉貴而羊肉賤則回,豬羊肉都貴則佛,請客之時則耶。為什麼請客的時候則耶?
耶穌教是由替天行道的牧師們,不遠萬里而傳到只信魔鬼不曉得天國的中華。老教師們有時候高興請信徒們到家裡談一談,可以不說“請吃飯”,說“請吃茶”;請吃茶自然是西洋文明人的風俗。從實惠上看,吃飯與吃茶是差的多;可是中國人到洋人家裡去吃茶,那“受寵若驚”的心理,也就把計較實惠的念頭勝過了。
這種妙法被老張學來,於是遇萬不得已之際,也請朋友到家裡吃茶。這樣辦,可以使朋友們明白他親自受過洋人的傳授,至於省下一筆款,倒算不了什麼。滿用平聲仿著老牧師說中國話:“明天下午五點鐘少一刻,請從你的家裡走到我的家裡吃一碗茶。”尤為老張的絕技。
營商,為錢;當兵,為錢;辦學堂,也為錢!同時教書營商又當兵,則財通四海利達三江矣!此之謂“三位一體”;此之謂“錢本位而三位一體”。
依此,說話三種,信教三樣,洗澡三次,……莫不根據於“三位一體”的哲學理想而實施。
老張也辦教育?
真的!他有他自己立的學堂!
他的學堂坐落在北京北城外,離德勝門比離安定門近的一個小鎮上。坐北朝南的一所小四合房,包著東西長南北短的一個小院子。臨街三間是老張的雜貨鋪,上自鴉片,下至蔥蒜,一應俱全。東西配房是他和他夫人的卧房;夏天上午住東房,下午住西房;冬天反之;春秋視天氣冷暖以為轉移。既省涼棚及煤火之費,長遷動著於身體也有益。北房三間打通了~*段,足以容五十多個學生,土砌的橫三豎八的二十四張書桌,不用青灰,專憑墨染,是又黑又勻。書桌之間列著洋槐木作的小矮腳凳:高身量的學生,蹲著比坐著舒服;小的學生坐著和吊著差不多。北牆上中間懸著一張孔子像,兩旁配著彩印的日俄交戰圖。西牆上兩個大鐵帽釘子掛著一塊二尺見方的黑板;釘子上掛著老張的軍帽和陰陽合曆的憲書。門口高懸著一塊白地黑字的匾,匾上寫著“京師德勝汛①公私立官商小學堂”。
老張的學堂,有最嚴的三道禁令:第一是無論春夏秋冬閏月不準學生開教室的窗戶;因為環繞學堂半里而外全是臭水溝,無論刮東西南北風,永遠是臭氣襲人。不準開窗以絕惡臭,於是五十多個學生噴出的炭氣,比遠遠吹來的臭氣更臭。第二是學生一切用品點心都不準在學堂以外的商店去買;老張的立意是在增加學生愛校之心。第三不準學生出去說老張賣鴉片。因為他只在附近煙館被官廳封禁之後,才作暫時的接濟;如此,危險既少,獲利又多;至於自覺身份所在不願永遠售賣煙土,雖非主要原因,可是我們至少也不能不感謝老張的熱心教育。
老張的地位:村裡的窮人都呼他為“先生”。有的呢,把孩子送到他的學堂,自然不能不尊敬他。有的呢,遇著開殃榜,批婚書,看風水,……*家餃找簿筒*能不有相當的敬禮。富些的人都呼他為“掌柜的”,因為他們日用的油鹽醬醋之類,不便入城去買,多是照顧老張的。德勝汛衙門裡的人,有的呼他為“老爺”,有的叫他“老張”,那要看地位的高低;因為老張是衙門裡挂名的巡擊。稱呼雖然不同,而老張確乎是鎮里——二郎鎮——一個重要人物!老張要是不幸死了,比丟了聖人損失還要大。因為那個聖人能文武兼全,陰陽都曉呢?
老張的身材按營造尺是五尺二寸,恰合當兵的尺寸。不但身量這麼適當,而且腰板直挺,當他受教員檢定的時候,確經檢定委員的證明他是“脊椎動物”。紅紅的一張臉,微點著幾粒黑痣;按《麻衣相法》說,主多材多藝。兩道粗眉連成一線,黑叢叢的遮著兩隻小豬眼睛。一隻短而粗的鼻子,鼻孔微微向上掀著,好似柳條上倒掛的鳴蟬。一張薄嘴,下嘴唇往上翻著,以便包著年久失修漸形垂落的大門牙,因此不留神看,最容易錯認成一個夾餡的燒餅。左臉高仰,右耳幾乎扛在肩頭,以表示著師位的尊嚴。
批評一個人的美醜,不能只看一部而忽略全體。我雖然說老張的鼻子像鳴蟬,嘴似燒餅,然而決不敢說他不好看。從他全體看來,你越看他嘴似燒餅,便越覺得非有鳴蟬式的鼻子配著不可。從側面看,有時鼻窪的黑影,依稀的像小小的蟬翅。就是老張自己對著鏡子的時候,又何嘗不笑吟吟的誇道:“鼻翅掀著一些,哼!不如此,怎能叫婦人們多看兩眼!”
那是五月的天氣,小太陽撅著血盆似的小紅嘴,忙著和那東來西去的白雲親嘴。有的唇兒一挨慌忙的飛去;有的任著意偎著小太陽的紅臉蛋;有的化著惡龍,張著嘴想把她一口吞了;有的變著小綿羊跑著求她的青眼。這樣艷美的景色,可惜人們卻不曾注意,那倒不是人們的錯處,只是小太陽太嬌羞了,太潑辣了,把要看的人們曬的滿臉流油。於是富人們支起涼棚索興不看;窮人們倒在柳蔭之下作他們的好夢,誰來惹這個閑氣。
一陣陣的熱風吹去的柳林蟬鳴,荷塘蛙曲,都足以增加人們暴躁之感。詩人們的幽思,在夢中引逗著落花殘月,織成一片閑愁。富人們乘著火艷榴花,繭黃小蝶,增了幾分雅趣。
老張既無詩人的觸物興感,又無富人的及時行樂;只伸著右手,仰著頭,數院中杏樹上的紅杏,以備分給學生作為麥秋學生家長送禮的提醒。至於滿垂著紅杏的一株半大的杏樹,能否清清楚楚數個明白,我們不得而知,大概老張有些把握。
“咳!老張!”老張恰數到九十八上,又數了兩個湊成一百,把大拇指捏在食指的第一節上,然後回頭看了一看。這輕輕的一捏,慢慢的一轉,四十多年人世的經驗!“老四,屋裡坐!”
“不!我還趕著回去,這兩天差事緊的很!”
“不忙,有飯吃!”老張搖著蓄滿哲理的腦袋,一字一珠的從薄嘴唇往外蹦。
“你盟兄李五才給我一個電話,新任學務大人,已到老五的衙門,這就下來,你快預備!我們不怕他們文面上的,可也不必故意冷淡他們,你快預備,我就走,改日再見。”那個人一面擦臉上的汗,一面往外走。
“是那位大……”老張趕了兩步,要問個詳細。“新到任的那個。反正得預備,改天見!”那個人說著已走出院外。
老張自己冷靜了幾秒鐘,把腦中幾十年的經驗匆匆的讀了一遍,然後三步改作兩步跑進北屋。
“小三!去叫你師娘預備一盆茶,放在杏樹底下!快!小四!去請你爹,說學務大人就來,請他過來陪陪。叫他換上新鞋,聽見沒有?”小三,小四一溜煙似的跑出屋外。“你們把《三字經》,《百家姓》收起來,拿出《國文》,快!”“《中庸》呢?”
“費話!舊書全收!快!”這時老張的一雙小豬眼睜得確比豬眼大多了。
“今天把國文忘了帶來,老師!”
“該死!不是東西!不到要命的時候你不忘!《修身》也成!”
“《算術》成不成?”
“成!有新書的就是我爸爸!”老張似乎有些急了的樣子。“王德!去拿掃帚把杏樹底下的葉子都掃乾淨!李應!你是好孩子,拿條濕手巾把這群墨猴的臉全擦一把!快!”
拿書的拿書;掃地的掃地;擦臉的擦臉;乘機會吐舌頭的吐舌;擠眼睛的擠眼;亂成一團,不亞於遭了一個小地震。老張一手摘黑板上掛著的軍帽往頭上戴,一手掀著一本《國文》找不認識的字。
“王德!你的字典?”
“書桌上那本紅皮子的就是!”
“你瞎說!該死!我怎麼找不著?”
“那不是我的書桌,如何找得到!”王德提著掃帚跑進來,把字典遞給老張。
“你們的書怎樣?預備好了都出去站在樹底下!王德快掃!”老張一手按著字典向窗下看了一眼。“哈哈!叫你掃杏葉,你偷吃我的杏子。好!現在沒工夫,等事情完了咱們算賬!”
“不是我有意,是樹上落下來的,我一抬頭,正落在我嘴裡。不是有心,老師!”
“你該死!快掃!”
“你一萬個該死!你要死了,就把杏子都吃了!”王德自己嘟囔著說。
王德掃完了,茶也放在杏樹下,而且擺上經年不用的豆綠茶碗十二個。小四的父親也過來了,果然穿著新緞鞋。老張查完字典,專等學務大人駕到,心裡越發的不鎮靜。“王德!
你在門口去瞭望。看見轎車或是穿長衫騎驢的,快進來告訴我。臉朝東,就是有黃蜂螫你的後腦海,也別回頭!聽見沒有?“
“反正不是你腦袋。”王德心裡說。
“李應!你快跑,到西邊冰窖去買一塊冰;要整的,不要碎塊。”
“錢呢?”
“你衣袋裡是什麼?小孩子一點寬宏大量沒有!”老張顯示著作先生的氣派。
李應看了看老張,又看了看小四的父親——孫八爺——一語未發,走出去。
這時候老張才想起讓孫八爺屋裡去坐,心裡七上八下的勉強著和孫八爺閑扯。
孫八爺看著有四十上下的年紀,矮矮的身量,圓圓的臉。一走一聳肩,一高提腳踵,為的是顯著比本來的身量高大而尊嚴。兩道稀眉,一雙永遠發困的睡眼;幸虧有隻高而正的鼻子,不然真看不出臉上有“一應俱全”的構造。一嘴的黃牙板,好似安著“磨光退色”的金牙;不過上唇的幾根短須遮蓋著,還不致金光普照。一件天藍洋緞的長袍,罩著一件銅鈕寬邊的米色坎肩,童叟無欺,一看就知道是鄉下的土紳士。
不大的工夫,李應提著一塊雪白的冰進來。老張向孫八說:
“八爺來看看這一手,只准說好,不準發笑!”
孫八隨著老張走進教室來。老張把那塊冰接過來,又找了一塊木板,一齊放在教室東牆的洋火爐里,打著爐口,一陣陣的往外冒涼氣。
“八爺!看這一手妙不妙?洋爐改冰箱,冬暖夏涼,一物兩用!”老張挑著大拇指,把眼睛擠成一道縫,那條笑的虛線從臉上往裡延長,直到心房上,撞的心上癢了一癢,才算滿足了自己的得意。
原來老張的洋爐,爐腔內並沒有火瓦。冬天擺著,看一看就覺得暖和。夏天遇著大典,放塊冰就是冰箱。孫八看了止不住的誇獎:“到底你喝過墨水,肚子里有貨!”
正在說笑,王德飛跑的進來,堵住老張的耳朵,霹靂似的嚷了一聲“來了!”同時老張王德一人出了一身情感不同而結果一樣的冷汗!
門外拍拍的撣鞋的聲音,孫八忙著迎出來,老張扯開喉嚨叫“立——正!”五十多個學生七長八短的排成兩行。小三把左腳收回用力過猛,把腳踵全放在小四的腳指上,“哎喲!老師!小三立正,立在我腳上啦!”
“向左——轉!擺隊相——迎!”號令一下,學生全把右手放在眉邊,小四痛的要哭,又不敢哭,只把手遮著眼睛隔著眼淚往外看。前面走的他認識是衙門的李五,後面的自然是學務大人了。
“不用行禮,把手放下,放下,放下!”學務大人顯著一萬多個不耐煩的樣子。學生都把手從眉邊摘下來。老張補了一句:“禮——畢!”
李五遞過一張名片,老張低聲問:“怎樣?”李五偷偷的應道:“好說話。”
“大人東屋坐,還是到講堂去?”老張向學務大人行了個舉手禮。
“李先生,你等我一等,我大概看看就走。行家一過眼,站在學堂外邊五分鐘,就知道辦的好壞,那算門裡出身。”學務大人聳著肩膀,緊著肚皮,很響亮的嗽了兩聲,然後鼓著雙腮,只轉眼珠,不扭脖項的往四外一看。把一口痰用舌尖捲成一個滑膩的圓彈,好似由小唧筒噴出來的唾在杏樹底下。拿出小手巾擦了擦嘴,又順手擦擦鼻凹的汗。然後自言自語的說:“哼!不預備痰盂!”
“那麼老五,八爺,你們哥倆個東屋裡坐,我伺候著大人。”老張說。
“不用‘大人’‘大人’的!‘先生’就好!新辦法新稱呼,比不得七八年前。把學生領到‘屋裡’去!”
“是!到‘講堂’去?”
“講堂就是屋裡,屋裡就是講堂!”學務大人似乎有些不滿意老張的問法。
“是!”老張又行了一個舉手禮。“向左——轉!入講——堂!”
學生把腳抬到過膝,用力跺著腳踵,震得地上冬冬的山響,向講堂走來。
老張在講台上往下看,學生們好似五十多根小石樁。俏皮一點說,好似五十多尊小石佛;瞪著眼,努著嘴,挺著脖子,直著腿。也就是老張教授有年,學務大人經驗宏富,不然誰吃得住這樣的陣式!五十多個孩子真是一根頭髮都不動,就是不幸有一根動的,也聽得見響聲。學務大人被屋裡濃厚的炭氣堵的,一連打了三個噴嚏;從門袋裡掏出日本的“寶丹”,連氣的往鼻子里吸,又拿出手巾不住的擦眼淚。老張利用這個機會,才看了看學務大人:學務大人約有四十五六歲的年紀。一張黑黃的臉皮,當中鑲著白多黑少的兩個琉璃球。一個中部高峙的鷹鼻,鼻下掛著些干黃的穗子,遮住了嘴。穿著一件舊灰色官紗袍,下面一條河南綢做的洋式褲,系著褲腳。足下一雙短筒半新洋皮鞋,露著本地藍市布家做的襪子。乍看使人覺著有些光線不調,看慣了更顯得“新舊咸宜”,“允執厥中”。或者也可以說是東西文化調和的先聲。
老張不敢細看,打開早已預備好的第三冊《國文》,開始獻技。
“《新國文》第三課,找著沒有?”
“找著了!”學生都用最高的調子喊了一聲。
“聽著!現在要‘提示注意’。”老張順著教授書的程序往下念。
“王德!把腰挺起來!那是‘體育’,懂不懂?”
王德不懂,只好從已然板直的腰兒,往無可再直里挺了一挺。
“聽著!現在要‘輸入概念’。這一課講的是燕子,燕子候鳥也。候鳥乃鳥中之一種,明白不明白?”
“明白呀!老師!”學生又齊喊了一聲。小三差一點把舌尖咬破,因為用力過猛。
“不叫‘老師’,叫‘先生’!新事新稱呼,昨天告訴你們的,為何不記著?該……該記著!”老張接續講下去:“燕子自北海道飛過小呂宋,渡印度洋而至特耳其司坦,此其所以為候鳥,明白不明白?”
“明白!老師,啊……啊……先生!”這一次喊的不甚齊整。
學務大人把一支鉛筆插在嘴裡,隨著老張的講授,一一記在小筆記本上。寫完一節把舌頭吐在唇邊,預備往鉛筆上沾唾液再往下寫。寫的時候是鉛筆在舌上觸兩下,寫一個字。王德偷著眼看,他以為大人正害口瘡;麗小三——學務大人正站在他的右邊——卻以為大人的鉛筆上有柿霜糖。“張先生,到放學的時候不到?”老張正待往下講書,學務大人忽然發了話。
“差二十分鐘,是!”
“你早些下堂,派一個大學生看著他們,我有話和你說。”“是!李應,你看著他們念書!立——正!行——禮!”
學生們都立起來,又把手擺在眉邊,多數乘著機會抓了抓鬢邊的熱汗,學務大人一些也沒注意,大搖大擺的走出講堂。
“誰要是找死,誰就乘著大人沒走以前吵鬧!”老張一眼向外,一眼向里,手扶著屋門,咬著牙根低聲而沈痛的說。大人來到東屋,李五,孫八立起來。孫八遞過一碗茶,說:“辛苦!多辛苦!大熱的天,跑這麼遠!”
“官事,沒法子!貴姓?”大人呷了一口茶,咕嚕咕嚕的嗽口。嗽了半天,結果,咽下去了。
“孫八爺,本地的紳士。”老張替孫八回答,又接著說:“今天教的好壞,你老多原諒!”
“教授的還不錯,你的外國地名很熟,不過不如寫在黑板上好。”大人很鄭重的說。
“不瞞先生說,那些洋字是跟我一個盟兄學的。他在東交民巷作六國翻譯。據他說,念外國字只要把平仄念調了,準保沒錯。”老張又一擠眼自外而內的一笑。
“何必你盟兄說,那個入過學堂的不曉得中西文是一理。”大人掏出煙斗擰上了一袋煙,一面接著問:“一共有多少學生?”
“五十四名。是!今天有兩個告假的:一個家裡有喪事,一個出‘鬼風疹’。”
大人寫在筆記本上。
“一年進多少學費?”
“進的好呢,一年一百五十元;不好呢,約合一百元的光景。”
大人寫在筆記本上,然後問:“怎麼叫進的好不好?”老張轉了轉眼珠,答道:“半路有退學的,學費要不進來,就得算打傷耗。”
“嘔!教科書用那一家的,商務的還是中華的?”“中華書局的!是!”
大人寫在筆記本上。把鉛筆含在口內,像想起什麼事似的。慢慢的說:“還是用商務的好哇,城裡的學堂已經都換了。”“是!明天就換!明天就換!”
“不是我多嘴,按理說‘中華’這個字眼比‘商務’好聽。前幾天在城裡聽宣講,還講‘中華大強國’,怎麼現在又不時興了呢?”孫八侃侃的說著。
“你怎能比大人懂的多,那一定有個道理。”老張看看孫八,又看了看大人。
大人咳嗽了兩聲,把手巾掩著嘴像要打哈欠,不幸卻沒打成。
“官事隨時變,”李五乘機會表示些當差的經驗:“現在不時興,過二年就許又復原。當差的不能不隨著新事走。是這樣說不是?大人!”
“是!是極了!張先生!不是我在你面前賣好,錯過我,普天下察學的,有給教員們出法子的沒有?察學的講究專看先生們的縫子,破綻,……”
“大人高明,”李五,孫八一齊說。
“不過,”大人提高了嗓子說:“張先生,有一件事我不能不挑你的錯。”
李五,孫八都替老張著急。老張卻還鎮靜,說:“是!先生指教!”
“你的講台為什麼砌在西邊,那是‘白虎台’,主妨礙生家長。教育乃慈善事業,怎能這樣辦呢!”大人一字一板的說。
“前任的大人說什麼教室取左光,所以我把講台砌在西邊。實在說,我還懂一點風水陰陽。上司的命令不敢不遵,先生還得多原諒!”
“不用說前任的話,他會辦事,還不致撤了差。不過我決不報上去。要是有心跟你為難,我就不和你當面說了,是不是?”大人笑了,李五,孫八也笑了。
大人又呷了一口茶,立起來。李五,孫八也立起來,只是老張省事,始終就沒坐下。
“天熱,多休息休息。”孫八說。
“不!下午還打算趕兩處。李先生!”
“大人!”李五臉笑的像小酒醉螃蟹似的。
“我們上五里墩,還是黃魚店?”
“大人請便,守備派我護送大人,全聽大人的吩咐!”
“老五!好好伺候大人,我都得請你喝茶,不用說大人……”老張要說又吞回去了。
“黃魚店罷!”大人似乎沒注意老張說什麼。
“大人多美言!老五,你領著大人由王家村穿東大屯由吳千總門口走,那一路都是柳樹,有些遮掩,日光太毒。”老張說。
大人前面走,孫八跟著不住的道“辛苦”。李五偷偷的扯著老張的袖子,伸了伸大指,老張笑了。
孫八告辭回家。老張立在門外,直等學務大人和李五走進樹林,才深深的喘了一口氣走進來。學生們在樹底下擠熱羊似的搶著喝茶。屋裡幾個大學生偷著砸洋爐里要化完的那塊冰。
“哈哈!誰的主意喝我的茶!”老張照定張成就打。“老師!不是我的主意,是小四頭一個要喝的!”張成用手遮著頭說。
“小四要喝?他拿多少學錢,你拿多少?他吃大米,你吃棒子麵!喝茶?不怕傷了你的胃!都給我走進去!”老張看了看茶盆,可憐大半已被喝去。老張怒沖沖的走進教室,學生又小石樁一般的坐好。王德的嘴還滿塞著冰渣。“小三,小四,卜鳳,王春,……你們回家去吃飯!對家裡說,學務大人來了,老師給大人預備的茶水點心,給學生泡的小葉茶,叫家裡看著辦,該拿多少拿多少。大人察的是你們的學問,老師不能幹賠錢。聽明白沒有?去罷!”小三們夾起書包,小野鹿似的飛跑去了。
“你們怎麼樣?是認打,認罰?”
“回象對父親說,多少送些東西給老師!”七八個學生一齊說。
“說個准數,別含糊著,親是親,財是財!”
“老師!我們要是說了,父親遇上一時不方便呢?”幾個大學生說。
“不方便?起初就別送學生來念書!要念書,又要省錢,作老師的怎那麼天生的該餓死!不用費話,怕打的說個數目,身上發癢的,板子現成!”
老張把軍帽摘下來,照舊掛在掛黑板的帽釘上。脫了長袍,把小汗衫的袖子高高挽起。一手拿起教鞭,一手從講桌深處扯出大竹板。掄了掄教鞭,活動活動手腕。半惱半笑的說:
“給我個乾脆!燒香的還願,跳山澗的也還願,錢是你們的,肉也是你們的。願打,願罰,快著定!一寸光陰一寸金,耽誤我的光陰,你們賠得起黃金嗎?”
五六個心慈面善的學生,覺得大熱的天吃板條,有些不好意思。他們立起來,有人從家裡拿一隻小雛雞的;有人拿五百錢的;老張一一記在賬本上,放他們回家。其餘的學生認清了:到家要錢也是挨打,不如充回光棍賣給老張幾下。萬一老張看著人多,也許舉行一回大赦呢。
打人就要費力氣,費力氣就要多吃飯,多吃飯就要費錢,費錢就是破壞他的哲學,老張又何嘗愛打人呢?但是,這次不打,下次就許沒有一個認罰的,豈不比多吃一碗飯損失的更大?況且,萬一打上心火來,吃不下東西,省一兩碗飯也未可知。於是學生們的萬一之望,敵不過哲學家萬一之望,而要充光棍的少年們苦矣!
學生們紛紛擦拳磨掌,增高溫度,以備抵抗冰涼鐵硬的竹板。有的乾乾的落淚,卻不哭喊出來。老張更怒了:“好!你是不服我呀!”於是多打了三板。有的還沒走到老張跟前早已痛哭流涕的央告起來。老張更怒了:“好!你拿眼淚軟我的心,你是有意罵我!”於是多打了三板。有的低聲的哭著,眼淚串珠般的滾著。老張更怒了:“好!你想半哭半不哭的騙我,狡猾鬼!”於是又打了三板。
老張和其他的哲學家一樣,本著他獨立不倚的哲學,無論如何設想,是不會矛盾的。
學生們隨打隨走,現在只剩下李應和王德二個,李應想:“我是大學長,自然不會挨打,何況我已給他買了一塊冰?”王德呢,自知吃杏子,吃冰等罪案,是無可倖免的,把手搓的鮮紅,專備迎敵。
“李應!你怎樣?”老張放下竹板,舒展著自己的手腕。“我不知道!”李應低著頭說。
“你以為我不打大學長嗎?你不攔著他們喝茶,吃冰,是你的錯處不是?”
“茶本來是該喝的,冰是我買的,錯不錯我不知道。”李應把臉漲紅,理直氣壯的說。
徠“哈哈……”老張狂笑了一陣,這回確是由內而外的笑,惟其自內而外,是最難測定是否真笑,因為哲學家的情感是與常人不同的。
“你不錯,我錯,我要打你!”老張忽然停住了笑聲,又把竹板拾起來。
“我要是告退不念呢,叔父不允許。”李應自己想:“叫他打呢,有什麼臉去見人。”
“我告退不念了!”李應想來想去,覺得叔父怎樣也比老張好說話。
“什麼?不念了?你要不念就不念!”
“我叔父不叫我念書了!”李應明知自己說謊,可是舍此別無搪塞老張的話。
“你叔父?嘔!你叔父!去,叫你叔父把咱老張的錢連本帶利今天都還清,你是愛念不念!”
李應明白了!明白一切的關係!眼淚止不住的流下來。“哭?會哭就好!”老張用板子轉過去指著王德:“你怎麼樣?”
“看著辦,好在誰也沒吃板條的癮。”王德笑嘻嘻的說。
王德慢慢的走過去,老張卻把板子放下了。王德倒吃了一驚,心裡說:“老手要是走運,老屁股許要糟糕。”繼而又想到:“好在一家人,也該叫老屁股替老手一回了。反正你們挨打,疼都在我心上,樂得不換換地方呢!”王德永遠往寬處想,一這樣想,心裡立覺痛快,臉上就笑出來,於是他笑了。“王德!你跟我到東屋去!”
“我倒不挑選地方挨打。也別說,東屋也許比西屋涼爽一些。”王德說畢,隨著老張往東屋走。老張並沒拿著板子。“王德,你今年十幾歲?”老張坐下,仰著臉把右手放在鬢邊。
“我?大概十九歲,還沒娶媳婦,好在不忙。”“不要說廢話,我和你說正經事。”老張似乎把怒氣全消了。
“娶媳婦比什麼也要緊,也正經。要是說娶妻是廢話,天下就沒有一句正經話。”王德一面說著,一面找了一條凳子坐下。
“你知道李應的家事不知道?”老張閉著一隻眼問。“我知道他叔父也姓李。”
“別的呢?”
“我還沒研究過。”王德說完,哈哈的笑起來。他想起二年前在《國文》上學了“研究”兩個字,回家問他父親:“咱們晚飯‘研究’得了沒有?”被他父親一掌打在臉上,至今想起來還覺得干辣辣的發燒。父親不明白兒子說“研究”,你說可笑不可笑。王德越發笑的聲音高了。
“你是非打不可,有什麼可笑呢?”
“是可笑!人要把鼻子倒長著,下雨的時候往嘴裡灌水,難道不可笑?人要把鬍子長在手掌上,長成天然小毛刷子,隨便刷衣裳,難道不可笑?挨打是手上疼,管不著心裡笑!”“你不知道李應家裡的事?”老張早知道王德是寧挨打不止笑的人物,不如聽著他笑。
“我不知道。”
“好!你今年十九,李應也十九;他可以作大學長,你為何不可以?假如我要派你作大學長,你干不幹?”王德和李應是最好的學友,他只有一件事不滿意李應,就是李應作大學長。王德以為凡是老人都可恨,他的父親因為他說“研究”就打得他臉上開花。老人,在王德想,就是專憑勢力不懂人情的老古董。除了老人要算年青而學老人行為的為可惡。街坊邳三年青青的當軍官,打部下的兵丁比父親打兒子還毒狠。城裡的錢六才二十多歲,就學著老人娶兩個媳婦。邳三,錢六該殺!至於李應呢,歲數不大,偏板著面孔替老張吹鬍子瞪眼睛的管束同學。如今老張要派王德作大學長,他自己笑著說:“王德!還沒娶媳婦,就作大學長,未免可笑,而且可殺!”王德於是突然立起來,往外就走。
“你別走!”老張把他攔住。“有你的好處!”“有什麼好處?”
“你聽著,我慢慢對你說。”老張把王德又推在小凳上。“你要當大學長,我從此不打你。可是你得幫我算鋪子的賬目。”
王德滴溜溜的轉著兩隻大眼睛,沒有回答。
“還有好處!你現在拿多少學錢,每天領多少點心錢?”
“學錢每月六吊,點心錢不一定,要看父親的高興不高興。”
“是啊!你要是作大學長,聽明白了,可是幫我算賬,我收你四吊錢的學費。”
“給父親省兩吊錢?”
“你不明白,你不用對你父親說,每月領六吊錢,給我四吊,那兩吊你自己用,你看好不好?”
“不告訴父親?他要是知道了,你替我挨打?”王德又笑了:設若父親照打我一般的打老張一頓,多麼有趣。“你我都不說,他怎會知道,不說就是了!”
“嘴裡不說,心裡難過!”
“不會不難過?”
“白天不說,要是夜裡說夢話呢?”
“你廢話!”
“不廢話!你們老人自然不說夢話,李應也許不說,可是我夜夜說。越是白天不說的,夜間越說的歡。”“少吃飯,多喝水,又省錢,又省夢!”
“省什麼?”
“省——夢!你看你師母,永遠不作夢。她餓了的時候,我就告訴她,‘喝點水。’”
王德止不住又高聲笑起來。他想:“要是人人這樣對待婦女,過些年婦人不但只會喝水,而且變成不會作夢的動物。嘔!想起來了,父親常說南海有‘人頭魚’,婦人頭,魚身子,不用說,就是這種訓練的結果。可是人頭魚作夢不作?不知道!父親?也許不知道。哼!還是別問他,問老人不知道的事情,結果是找打嘴巴!”
“王德!我沒功夫和你廢話,就這麼辦!去,家去吃飯!”老張立起來。
“這裡問題太多,”王德屈指一一的算:“當大學長,假充老人,騙父親的錢,幫你算賬,多喝水,少吃飯,省錢省夢,變人頭魚!……不明白,我不明白!”
“明白也這麼辦,不明白也這麼辦!去!滾!”王德沒法子,立起來往外走。忽然想起來:“李應呢?”“你管不著!我有治他的法子!去!”
第五節
老張把李應,王德的事,都支配停妥,呷了一口涼茶。茶走下去,肚裡咕碌碌的響了一陣。“老張你餓了!”他對自己說:“肚子和街上的乞丐一樣,永遠是虛張聲勢,故作醜態。一餓就吃,以後他許一天響七八十次。”他按了按肚皮:“討厭的東西,不用和我示威,老張有老張的辦法!”命令一下,他立刻覺得精神勝過肉體,開始計劃一切:“今天那兩句‘立正’叫得多麼清脆!那些鬼子地名說的多麼圓熟!老張!總算你有本事!……”“一百四,加節禮三十,就是一百七。小三的爹還不送幾斗穀子,夠吃一兩個月的。學務大人看今天的樣子總算滿意,一報上去獎金又是三十。一百七,加三十就是二百,——二百整!鋪子決不會比去年賺的少,雖然還沒結賬!……”“李應的叔父欠的債,算是無望,辭了李應叫他去挑巡擊①,坐地扣,每月扣他餉銀兩塊,一年又是二十四。李應走後,王德幫咱算賬,每月少要他兩吊錢,可是省找一個小徒弟呢。狠心罷!舍兩吊錢!……”
他越想越高興,越高興肚子越響,可是越覺得沒有吃飯的必要!於是他跑北屋,拿起學務大人的那張名片細看了一看。那張名片是紅紙金字兩面印的。上面印的字太多,所以老張有幾個不認識,他並不計較那個;又不是造字的聖人,誰能把《字典》上的字全認得?
名片的正面:
“教育講習所”修業四月,參觀昌平縣教育,三等英美煙公司銀質獎章,前十一師二十一團炮營見習生,北京自治研究會會員,北京青年會會員,署理京師北郊學務視察員,上海《消閑晚報》通信員。南飛生,旁邊注著英文字:NanFiSheng。
背面是:
字雲卿,號若艇,投稿署名亦雨山人。借用電話東局1015。拜訪專用。
“這小子有些來歷!”老張想:“就憑這張名片,印一印不得一塊多錢?!老張你也得往政界上走走啊!有錢無勢力,是三條腿的牛,怎能立得穩!……”“哼!有來歷的人可是不好鬥,別看他嘻皮笑臉的說好話,也許一肚子鬼胎!書用的不對,講台是‘白虎台’,院里沒痰盂,……照實的報上去,老張你有些吃不住哇!”
老張越想越悲觀,白花花的洋錢,一塊擠著一塊雪片似的從心裡往外飛。“報上去了!‘白虎台’,舊教科書,獎金三十塊飛了!公文下來,‘一切辦法,有違定章,著即停辦!’學生們全走了,一百四加節禮三十,一百七飛了!……”
老張滿頭冷汗,肚裡亂響,把手猛的向桌上一拍,喊:“飛了!全飛了!”
“沒有,就飛了一隻!”窗外一個女人有氣無力的說。“什麼飛了?”
“我在屋裡給你作飯,老鷹拿去了一隻!”窗外的聲音低微得好似夢裡聽見的怨鬼悲嘆。
“一隻什麼?”
“小雞!”窗外嗚咽咽的哭起來。
“小雞!小雞就是命,命就是小雞!”
“我今天晚上回娘家,把我哥哥的小雞拿兩隻來,成不成?”
“你有哥哥?你恐嚇我?好!學務大人欺侮我,你也敢!
你滾蛋!我不能養著:吃我,喝我的死母豬!”
老張跑出來,照定那個所謂死母豬的腿上就是一腳。那個女人像燈草般的倒下去,眼睛向上翻,黃豆大的兩顆淚珠,嵌在眼角上,閉過氣去。
這時候學生吃過午飯,逐漸的回來;看見師母倒在地上,老師換著左右腿往她身上踢,個個白瞪著眼,像看父親打母親,哥哥打嫂子一樣的不敢上前解勸。王德進來了,後面跟著李應。(他們並沒回家吃飯,只買了幾個燒餅在學堂外面一邊吃,一邊商議他們的事。)王德一眼看見倒在地下的是師母,登時止住了笑,上前就要把她扶起來。
“王德你敢!”老張的薄片嘴緊的像兩片猴筋似的。“師母死啦!”王德說。
“早就該死!死了臭塊地!”
王德真要和老張宣戰了,然而他是以笑為生活的,對於打架是不大通曉的。他渾身顫著,手也抬不起來,腿在褲子里轉,而且褲子像比平日肥出一大塊。甚至話也說不出,舌頭頂著一口唾沫,一節一節的往後縮。
王德正在無可如何,只聽拍的一聲,好似從空中落下來的一個紅楓葉,在老張向來往上揚著的左臉上,印了五條半紫的花紋。李應!那是李應!
王德開始明白:用拳頭往別人身上打,而且不必挑選地方的,謂之打架。於是用盡全身力量喊了一聲:“打!”
老張不提防臉上熱辣辣的挨了一掌,於是從歷年的經驗和天生來的防衛本能,施展全身武藝和李應打在一處。王德也掄著拳頭撲過來。
“王德!”李應一邊打一邊嚷:“兩個打一個不公道,我要是倒了,有膽子你再和他干!”
王德身上不顫了,臉上紅的和樹上的紅杏一樣。聽見李應這樣說,一面跑回來把師母攙起來,一面自己說:“兩個打一個不公道,男人打女人公道嗎?”
小三,小四全哭了,大些的學生都立著發抖。門內站滿了閑人,很安詳而精細的,看著他們打成一團。“多辛苦!多辛苦!李應放開手!”孫八爺從外面飛跑過來捨命的分解。“王德!過來勸!”
“不!我等打接應呢!”王德拿著一碗冷水,把幾粒仁丹往師母嘴裡灌。
“好!打得好!”老張從地上爬起來,撣身上的土。李應握著拳一語不發。
“李應!過來灌師母,該我和他干!”王德向李應點手。老張聽王德這樣說倒笑了。孫八爺不知道王德什麼意思,只見他整著身子撲過來。
“王德你要作什麼?”孫八攔住他。
“打架!”王德說:“兩個打一個不公道,一個打完一個打!”“車輪戰也不公道!你們都多辛苦!”孫八把王德連推帶抱的攔過去。又回頭對老張說:“張先生你進屋裡去,不用生氣,小孩子們不知事務。”然後他又向看熱鬧的人們說:“諸位,多辛苦!先生責罰學生,沒什麼新奇,散散罷!”
老張進西屋去,看熱鬧的批評著老張那一腳踢的好,李應那一捏脖子捏的妙,紛紛的散去。
孫八又跑到張師母跟前說:“大嫂!不用生氣,張先生是一時心急。”
張師母已醒過來,兩眼獃獃的看著地,一手扶著王德,一手托著自己的頭,顫作一團。
“八爺!不用和她費話!李小子你算有膽氣!你,你叔父,一個跑不了!你十九,我四十九,咱們睜著眼看!”老張在屋裡嚷。
“閉著眼看得見?廢話!”王德替李應反抗著老張。
“好王德,你吃裡爬外,兩頭漢奸,你也跑不了!”“姓張的!”李應靠在杏樹上說:“拆你學堂的是我,要你命的也是我,咱們走著看!”
“拆房不如放火熱鬧,李應!”王德答著腔說。他又恢復了他的笑的生活:一來見師母醒過來,沒真死了;二來看李應並沒被老張打傷;三來覺得今天這一打,實在比平日學生挨打有趣得多。
“你們都辛苦!少說一句行不行?”孫八遮五蓋六的勸解。“大嫂你回家住一半天去,王德你送你師母去!李應你暫且回家!你們都進屋去寫字!”孫八把其餘的學生全叫進教室去。王德,李應扶著師母慢慢的走出去。
老張把李應,王德的事,都支配停妥,呷了一口涼茶。茶走下去,肚裡咕碌碌的響了一陣。“老張你餓了!”他對自己說:“肚子和街上的乞丐一樣,永遠是虛張聲勢,故作醜態。一餓就吃,以後他許一天響七八十次。”他按了按肚皮:“討厭的東西,不用和我示威,老張有老張的辦法!”命令一下,他立刻覺得精神勝過肉體,開始計劃一切:“今天那兩句‘立正’叫得多麼清脆!那些鬼子地名說的多麼圓熟!老張!總算你有本事!……”“一百四,加節禮三十,就是一百七。小三的爹還不送幾斗穀子,夠吃一兩個月的。學務大人看今天的樣子總算滿意,一報上去獎金又是三十。一百七,加三十就是二百,——二百整!鋪子決不會比去年賺的少,雖然還沒結賬!……”“李應的叔父欠的債,算是無望,辭了李應叫他去挑巡擊①,坐地扣,每月扣他餉銀兩塊,一年又是二十四。李應走後,王德幫咱算賬,每月少要他兩吊錢,可是省找一個小徒弟呢。狠心罷!舍兩吊錢!……”
他越想越高興,越高興肚子越響,可是越覺得沒有吃飯的必要!於是他跑北屋,拿起學務大人的那張名片細看了一看。那張名片是紅紙金字兩面印的。上面印的字太多,所以老張有幾個不認識,他並不計較那個;又不是造字的聖人,誰能把《字典》上的字全認得?
名片的正面:
“教育講習所”修業四月,參觀昌平縣教育,三等英美煙公司銀質獎章,前十一師二十一團炮營見習生,北京自治研究會會員,北京青年會會員,署理京師北郊學務視察員,上海《消閑晚報》通信員。南飛生,旁邊注著英文字:NanFiSheng。
背面是:
字雲卿,號若艇,投稿署名亦雨山人。借用電話東局1015。拜訪專用。
“這小子有些來歷!”老張想:“就憑這張名片,印一印不得一塊多錢?!老張你也得往政界上走走啊!有錢無勢力,是三條腿的牛,怎能立得穩!……”“哼!有來歷的人可是不好鬥,別看他嘻皮笑臉的說好話,也許一肚子鬼胎!書用的不對,講台是‘白虎台’,院里沒痰盂,……照實的報上去,老張你有些吃不住哇!”
老張越想越悲觀,白花花的洋錢,一塊擠著一塊雪片似的從心裡往外飛。“報上去了!‘白虎台’,舊教科書,獎金三十塊飛了!公文下來,‘一切辦法,有違定章,著即停辦!’學生們全走了,一百四加節禮三十,一百七飛了!……”
老張滿頭冷汗,肚裡亂響,把手猛的向桌上一拍,喊:“飛了!全飛了!”
“沒有,就飛了一隻!”窗外一個女人有氣無力的說。“什麼飛了?”
“我在屋裡給你作飯,老鷹拿去了一隻!”窗外的聲音低微得好似夢裡聽見的怨鬼悲嘆。
“一隻什麼?”
“小雞!”窗外嗚咽咽的哭起來。
“小雞!小雞就是命,命就是小雞!”
“我今天晚上回娘家,把我哥哥的小雞拿兩隻來,成不成?”
“你有哥哥?你恐嚇我?好!學務大人欺侮我,你也敢!
你滾蛋!我不能養著:吃我,喝我的死母豬!”
老張跑出來,照定那個所謂死母豬的腿上就是一腳。那個女人像燈草般的倒下去,眼睛向上翻,黃豆大的兩顆淚珠,嵌在眼角上,閉過氣去。
這時候學生吃過午飯,逐漸的回來;看見師母倒在地上,老師換著左右腿往她身上踢,個個白瞪著眼,像看父親打母親,哥哥打嫂子一樣的不敢上前解勸。王德進來了,後面跟著李應。(他們並沒回家吃飯,只買了幾個燒餅在學堂外面一邊吃,一邊商議他們的事。)王德一眼看見倒在地下的是師母,登時止住了笑,上前就要把她扶起來。
“王德你敢!”老張的薄片嘴緊的像兩片猴筋似的。“師母死啦!”王德說。
“早就該死!死了臭塊地!”
王德真要和老張宣戰了,然而他是以笑為生活的,對於打架是不大通曉的。他渾身顫著,手也抬不起來,腿在褲子里轉,而且褲子像比平日肥出一大塊。甚至話也說不出,舌頭頂著一口唾沫,一節一節的往後縮。
王德正在無可如何,只聽拍的一聲,好似從空中落下來的一個紅楓葉,在老張向來往上揚著的左臉上,印了五條半紫的花紋。李應!那是李應!
王德開始明白:用拳頭往別人身上打,而且不必挑選地方的,謂之打架。於是用盡全身力量喊了一聲:“打!”
老張不提防臉上熱辣辣的挨了一掌,於是從歷年的經驗和天生來的防衛本能,施展全身武藝和李應打在一處。王德也掄著拳頭撲過來。
“王德!”李應一邊打一邊嚷:“兩個打一個不公道,我要是倒了,有膽子你再和他干!”
王德身上不顫了,臉上紅的和樹上的紅杏一樣。聽見李應這樣說,一面跑回來把師母攙起來,一面自己說:“兩個打一個不公道,男人打女人公道嗎?”
小三,小四全哭了,大些的學生都立著發抖。門內站滿了閑人,很安詳而精細的,看著他們打成一團。“多辛苦!多辛苦!李應放開手!”孫八爺從外面飛跑過來捨命的分解。“王德!過來勸!”
“不!我等打接應呢!”王德拿著一碗冷水,把幾粒仁丹往師母嘴裡灌。
“好!打得好!”老張從地上爬起來,撣身上的土。李應握著拳一語不發。
“李應!過來灌師母,該我和他干!”王德向李應點手。老張聽王德這樣說倒笑了。孫八爺不知道王德什麼意思,只見他整著身子撲過來。
“王德你要作什麼?”孫八攔住他。
“打架!”王德說:“兩個打一個不公道,一個打完一個打!”“車輪戰也不公道!你們都多辛苦!”孫八把王德連推帶抱的攔過去。又回頭對老張說:“張先生你進屋裡去,不用生氣,小孩子們不知事務。”然後他又向看熱鬧的人們說:“諸位,多辛苦!先生責罰學生,沒什麼新奇,散散罷!”
老張進西屋去,看熱鬧的批評著老張那一腳踢的好,李應那一捏脖子捏的妙,紛紛的散去。
孫八又跑到張師母跟前說:“大嫂!不用生氣,張先生是一時心急。”
張師母已醒過來,兩眼獃獃的看著地,一手扶著王德,一手托著自己的頭,顫作一團。
“八爺!不用和她費話!李小子你算有膽氣!你,你叔父,一個跑不了!你十九,我四十九,咱們睜著眼看!”老張在屋裡嚷。
“閉著眼看得見?廢話!”王德替李應反抗著老張。
“好王德,你吃裡爬外,兩頭漢奸,你也跑不了!”“姓張的!”李應靠在杏樹上說:“拆你學堂的是我,要你命的也是我,咱們走著看!”
“拆房不如放火熱鬧,李應!”王德答著腔說。他又恢復了他的笑的生活:一來見師母醒過來,沒真死了;二來看李應並沒被老張打傷;三來覺得今天這一打,實在比平日學生挨打有趣得多。
“你們都辛苦!少說一句行不行?”孫八遮五蓋六的勸解。“大嫂你回家住一半天去,王德你送你師母去!李應你暫且回家!你們都進屋去寫字!”孫八把其餘的學生全叫進教室去。王德,李應扶著師母慢慢的走出去。
第二天早晨,王德歡歡喜喜領了點心錢,夾起書包上學來,他走到已經看見了學堂門的地方,忽然想起來:“老張忘了昨天的事沒有?老張怎能忘?”他尋了靠著一株柳樹的破石樁坐下,石樁上一個大豆綠蛾翩翩的飛去,很謙虛的把座位讓給王德。王德也沒心看,只顧思:“回家?父親不答應。上學?老張不好惹。師母?也許死了!——不能!師母是好人;好人不會死的那麼快!……”
王德平日說笑話的時候,最會想到別人想不到的地方。作夢最能夢見別人夢不到的事情。今天,腦子卻似枯黃的麥莖,只隨著風的扇動,向左右的擺,半點主意也沒有。柳樹上的鳴蟬一聲聲的“知了”!“知了”!可是不說“知道了什麼”。他於是立起來坐下,坐下又起來,路上趕早市和進城作生意的人們,匆匆的由王德面前過去,有的看他一眼,有的連看也不看,好像王德與那塊破石樁同樣的不惹人注意。 “平日無事的時候,”王德心裡說:“鳥兒也跟你說話,花草也向著你笑,及至你要主意的時候,什麼東西也沒用,連人都算在其內。……對,找李應去,他有主意!萬一他沒有?不能,他給我出過幾回主意都不錯!”
王德立起來,嘴裡嘟嘟囔囔的向西走去,平日從學堂到李應家裡,慢慢的走有十分鐘也到了;今天王德走了好似好幾十個十分鐘,越走像離著越遠。而且不住的回頭,老覺著老張在後面跟著他。
他走來走去,看見了:李應正在門外的破磨盤上坐著。要是平日,王德一定繞過李應的背後,悄悄的用手蓋上李應的眼,叫他猜是誰,直到李應猜急了才放手。今天王德沒有那個興趣,從遠遠的就喊:“李應!李應!我來了!”
李應向王德點了點頭,兩個人彼此看著,誰也想不起說話。
“王德,你進來看看叔父好不好?”倒是不愛說話的李應先打破了這個沉寂。
李應的家只有北屋三間,一明兩暗。堂屋靠牆擺著一張舊竹椅,孤獨的並沒有別的東西陪襯著。東裡間是李應和他叔父的卧室,順著前檐一張小矮土炕,對面放著一條舊楠木條案,案上放著一個官窯五彩瓶和一把銀胎的水煙袋。炕上堆著不少的舊書籍。西裡間是李應的姐姐的卧室,也是廚房。東西雖少,擺列得卻十分整潔。屋外圍著短籬,籬根種著些花草。李應的姐姐在城裡姑母家住的時候多,所以王德不容易看見她。
李應的叔父有五十多歲的年紀,看著倒像七八十歲的老人。黃黃的臉,雖洗得乾淨,只是罩著一層暗光。兩隻眼睛非常光銳,顯出少年也是精幹有為的。穿著一件舊竹布大衫,洗得已經退了色。他正卧在炕上,見王德進來微微抬起頭讓王德坐下。待了一會兒,他叫李應把水煙袋遞給他,李應替他燃著紙捻,他坐起來一氣吸了幾袋煙。
“王德,”李應的叔父半閉著眼,說話的聲音像久病的人一樣的微細。“我明白你們的事,我都明白,然而……”“昨天我們實在有理,老張不對!”王德說。
“有理無理,不成問題。昨天的事我都明白,不必再說。只是此後應該怎樣對付。現在這個事有幾層:你們的師母與老張;我與老張;你們兩個和老張。”李應的叔父喘了一口氣。“我的事我自有辦法;你們的師母我也替她想了一想。至於你們兩個,你們自然有你們自己的意見,我不便強迫你們聽我的囑咐。”他的聲音越說越弱,像對自己說一樣,王德,李應十分注意的聽著。“李應,你和王德出去,告訴他我昨天告訴你的話。”
王德起來要往外走。
“回來!你們也商議商議你們的事,回來我或者可以替你們決定一下。”他說完慢慢的卧下。兩個少年輕輕的走出去。兩個走出來坐在磨盤上。
“你知道我叔父的歷史?”李應問。
“他作過知縣,我知道,因為和上司講理丟了官。”“對!以後呢?”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可是昨天叔父告訴我了,叔父自從丟了官,落得一貧如洗。他心灰意冷,無意再入政界,於是想經營一個買賣,自食其力的掙三頓飯吃。後來經人介紹,和老張借了二百塊錢,又借了一百,共總三百。這是叔父與老張的關係。”
“介紹人是城裡的衛四。”李應停頓了一會,接著說:“衛四後來就自薦幫助叔父經理那個小買賣。後來衛四和老張溝通一氣,把買賣拆到他自己手裡去,於是叔父可是無法逃出老張的債。叔父是個不愛錢的人,因為不愛錢就上了人家的暗算。我和我姐姐自幼跟著叔父,我的父母,我甚至於想不起他們的面貌。”李應說著,把嘴唇接著淚珠往嘴裡咽。“叔父決不會把我送在老張的學堂去讀書要不是欠老張的債。老張拿我當奴隸,現在我才知道,那是他強迫叔父答應他的。叔父昨天哭的說不出話,他明白,然而他……他老了,打不起精神去抵抗一切了!這是他最痛心的事,也就是他只求一死的原因!前幾天老張又和叔父說,叫我去挑巡擊,他的意思是把我送在那個腐敗衙門裡,他好從中扣我的錢。叔父明白這麼一辦,不亞如把我送入地獄,可是他答應了老張。他只求老張快離開他,他寧可死了,也不肯和老張說話,他不惜斷送一切,求老張快走。叔父是明白人,是好人,然而——老了!”
“我明白了!我們怎麼辦?”王德臉又漲紅。
“不用說‘我們’,王德!你與老張沒惡感,何苦加入戰團?我決不是遠待你!”
“李應!我愛你,愛你叔父!不能不加入!我父親是受了老張的騙。他見了父親,總說:‘快復辟了,王德的舊書可是不能放下,要是放下,將來恢復科考,中不了秀才,可就悔之晚矣!’我早就想不在那裡念書,然而沒有機會。現在我總算和老張鬧破了臉,樂得乘機會活動活動。我有我的志願,我不能死在家裡!”
“我明白你的志願,可是我不願你為我遭些困苦!”
“我們先不必爭執這一點,我問你,你打算作什麼?”“我進城去找事!只要我能掙錢,叔父的命就可以保住!”“找什麼事?”王德問。
“不能預料!”
“老張放你走不放?”
“不放,拚命!”
“好!我跟你進城!跟父親要十塊錢!”王德以為有十塊錢是可以在城裡住一年的。
“我一定要進城,你不必。”
“我有我的志願,我進城不是為你,還不成?”
兩個人從新想了許多方法,再沒有比進城找事的好,李應不願意同王德一齊進城,王德死說活說,才解決了。他們一同進來見李應的叔父。
“叔父!我們決定進城一同找事。”王德首先發言:“我要看看世界是什麼樣子,李應有找事的必要。兩個人一同去呢,彼此有個照應。”
“好!”李應的叔父笑了一笑。
“我所不放心的是老張不放李應走。”
“我是怕我走後,老張和叔父你混鬧。”
“你們都坐下,你們還是不明白這個問題的內容。老張不能不叫李應走,他也不能來跟我鬧。現在不單是錢的問題,是人!”
“自然我們都是人。”王德笑著說。
“我所謂的人,是女人!”
“自然張師母是女人!”
“王德!此刻我不願意你插嘴,等我說完,你再說。”李應的叔父怕王德不高興,向王德笑了一笑。然後他燃著紙捻,連氣吸了幾口煙。把煙袋放下,又和李應要了一碗冷水漱了漱口。立起來把水吐在一個破瓦盂內,順手整了整大衫的折縫。
“王德,李應,”李應的叔父看了看那兩個少年,好像用眼光幫助他表示從言語中表示不出來的感情。“現在的問題是一個女人。李應!就是你的姐姐!”
李應不由的立起來,被叔父眼光的引領,又一語未發的坐下。
“不用暴躁,聽我慢慢的說!”那位老人接續著說:“張師母是她哥哥賣給老張的,這是十幾年前的事,他欠老張的債,所以她就作了折債的東西。她現在有些老丑,於是老張想依法炮製買你的姐姐,因為我也欠他的錢。他曾示意幾次,我沒有理他……我不是畜……李應!拿碗冷水來!”
他把頭低的無可再低,把一碗冷水喝下去,把碗遞給李應,始終沒抬頭。
“可是現在這正是你們的機會。因為在我不允許他的親事以前,他決不會十分毒辣,致使親事不成。那末,李應你進城,我管保老張不能不放你走。至於你們的師母,等老張再來提親的時候,我要求他先把她釋放,然後才好議婚。我想他一定要些個贖金,果然他吐這樣的口氣,那末,就是我們奪回你師母自由的機會。那個五彩瓶,”他並沒抬頭,只用手大概的向桌上指了一指。“是我寧挨餓而未曾賣掉的一件值錢的東西。李應,那是你父親給我的。你明天把那個瓶拿進城去,托你姑父賣出去,大概至少也賣一百塊錢。你拿二十元在城裡找事,其餘的存在你姑父那裡,等老張真要還你師母自由的時候,我們好有幾十元錢去贖她。她以後呢,自己再凍餓而死,我們無力再管,自然我們希望管。可是我們讓她死的時候明白,她是一條自由的身子,而不是老張的奴隸。你們師母要是恢復了她的自由,老張一定強迫我寫字據賣我的侄女。”
李應的叔父停住了話,把水煙袋拿起來,沒有吸煙,只不錯眼珠的著著煙袋。
“死是不可免的;我怕老張的笑聲,然而不怕死!”“叔父!”李應打斷他叔父的話:“你不用說‘死’成不成?”老人沒回答。
“老張!你個……”王德不能再忍,立起來握著拳頭向東邊搖著,好像老張就站在東牆外邊似的。
“王德!坐下!”李老人獃獃的看著案上的五彩瓶。王德坐下了,用拳頭邦邦的撞著炕沿。
“我對不起人,對不起老張,欠債不還,以死搪塞,不光明,不英雄!”老人聲音更微細了,好像秋夜的細雨,一滴一滴的冷透那兩個少年的心情。“你們,王德,李應,記住了:好人便是惡人的俘虜,假如好人不持著正義和惡人戰爭。好人便是自殺的砒霜,假如好心只是軟弱,因循,怯懦。我自己無望了,我願意你們將來把惡人的頭切下來,不願意你們自己把心挖出來給惡人看。至於金錢,你們切記著:小心得錢,小心花錢。我自己年少的時候,有一片傻好心,左手來錢,右手花去,落得今日不能不死。死,我是不怕的,只是死了還對不起人,至少也對不起老張。以前的我是主張‘以德報怨’,現在,‘以直報怨’。以前我主張錢可以亂花,不準苟得,現在,錢不可苟得,也不可亂花。……王德,你用不著進城。李應去后,老張正需人幫助,他決不致於因為你和他打架而慢待你。你要是天天見老張,至少也可以替我打聽他對於我的擺布。不過,你的志願我不敢反對,進城與否,還是你自己決定。從事實上看,好似沒有進城的必要。我的話盡於此,對不對我不敢說。你們去罷!不必懷念著我的死,我該死!”
李老人舒展了舒展大衫,慢慢的卧下去,隨手拿起一本書,遮住自己的臉;周身一動也不動,只有襟部微微的起伏,襯著他短促的呼吸。
“設若你能還老張的錢,你還尋死嗎,叔父?”王德問。“我怎能還他的錢?”
“我回家對父親說,他借與你錢,將來李應再慢慢的還我父親。”
“傻孩子!你父親那是有錢的人!”
“他有!一收糧就有好幾十塊!”
“幾十塊?那是你們一年的用度!傻孩子,我謝謝你!”“嘔!”王德疑惑了。“原來幾十塊錢不算富人,那麼,多少才可以算富足呢?”
多麼難堪夏日午時的靜寂!樹上的紅杏,田中的晚麥,熱的都不耐煩了!陣陣的熱風,吹來城內的喧鬧,困的睡了,不睡的聽著聽著哭了。這時王德和李應又坐在破磨盤上,王德看著那翎毛凋落的丑老鴉,左顧右盼的搖著禿頭腦,要偷吃樹上的紅杏。李應低著頭注視著地上的群蟻圍攻一個翠綠的嫩槐樹蟲。老鴉輕快的一點頭,銜起一個圓紅杏,拍著破翅擦著籬笆飛去。王德隨著老鴉把眼睛轉到東邊的樹上,那面丑心甜的老鴉把杏遞進巢內,啞啞的一陣小鴉的笑聲,布散著朴美的愛情。
李應不知不覺的要用手撥散那條綠蟲身上叮著的小黃蟻。他忘了他的手被王德緊緊的握著。他一抽手,王德回過頭來:“李應!”“啊!王德!”兩個人的眼光遇在一處,觸動了他們的淚腺的酸苦。他們毫不羞愧的,毫不虛偽的哭起來。
對哭——對著知己的朋友哭——和對笑,是人類僅有的兩件痛快的事。
“你哭完了沒有?我完了!”王德抹著紅眼。
“不哭了!”
“好!該笑了!今天這一哭一笑,在這張破磨盤上,是我們事業的開始!李應!你看前面,黑影在我們後面,光明在我們前頭!笑!”
王德真笑了,李應莫名其妙不覺的也一樂,這一樂才把他眼中的淚珠擠凈。
“王德,我還是不贊成你進城!”
“非去不可!我有我的志願!”王德停頓了一會兒:“李應,你姐姐怎樣呢?”他的臉紅了。
“有我姑父姑母照應著她。”
“是嗎?”王德沒有說別的。
“你該回家吃飯,老人家要是不准你進城,不必固執。”“父親管不了,我有我的志願!”王德說著往四下一看。“李應,我的書包呢?”
“放在屋裡了罷?進來看看。”
兩個人輕輕的走進去,李老人似乎昏昏的睡去。李應爬上炕去拿王德的書包。老人微微的睜開眼。
“王德呢?”
“在這裡。”
“王德!不用和別人說咱們的事。你過來!”
王德走過去,老人拉住他手,嘆了一口氣。王德不知說什麼好,只扭著脖子看李應。
“王德!少年是要緊的時候!我,我完了!去吧!告訴你父親,沒事的時候,過來談一談。”
王德答應了一聲,夾起書包往外走。老人從窗上鑲著的小玻璃往外望了王德一望,自言自語的說:“可愛!可愛的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