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軍東征
陝軍東征
陝軍東征是20世紀90年代的一種文學現象,這一現象曾經震動文壇,成為陝西乃至中國文學史上都值得記錄的輝煌。五位作家的創作激情被當時文學評論家稱為“井噴”。
“陝軍東征”這個詞一出現,立即成為當年文化界最火爆的現象。後來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科書,也承認陝軍東征“產生了空前的轟動效應”,全國的長篇小說創作由此走向高潮。一些文學評論家認為這是非常值得關注的文學、文化現象。但是有些人並不把它們看作一種文學、文化現象,或者認為那是“精心策劃的商業性事件”,或者認為那是“討好主流意識形態”的政治現象,將“陝軍東征”打入了文學、文化之外的另冊。具體如何還有待時間的考驗,後人評說。
陝西省作協滿眼都是白花,充耳都是哀樂,被低沉、陰鬱的氛圍所籠罩。對陝西作家和陝西作協來說,滿眼都是黑色的。
雖然置身於這樣一種環境氛圍,但陝西的作家並沒有停止思考和探索,也就是在1992年,陳忠實完成了《白鹿原》,賈平凹創作了《廢都》,京夫改定了《八里情仇》,程海拿出了《熱愛命運》,高建群寫就了《最後一個匈奴》,“陝軍”一下子打響了文壇。”
陝軍東征有五位作家:高建群、賈平凹、陳忠實被稱為“東征三駕馬車”,加之京夫和程海被人們稱為“東征五虎將”。他們的作品如下:
陳忠實:《白鹿原》(1997年榮獲茅盾文學獎)
高建群:《最後一個匈奴》
賈平凹:《廢都》
高建群:《最後一個匈奴》
賈平凹:《廢都》
陳忠實:《白鹿原》
京夫: 《八里情仇》
程海:《熱愛命運》
1993年上半年,《白鹿原》《廢都》《最後一個匈奴》《八里情仇》和《熱愛命運》不約而同被京城五家出版社推出。“陝軍東征”這一提法是在作家出版社為《最後一個匈奴》舉行的座談會上,當時一位北京的評論家說“陝西幾位小說家先後在首都各家出版社推出了他們的長篇小說”,大家便你一言我一語地補充,開玩笑說”陝西人要來個揮馬東征啊”。
1993年,記者韓小蕙在《光明日報》發表了題為《“陝軍東征”火爆京城》的文章,介紹了陝西幾部引起轟動的長篇小說和作家創作的內幕。
接著《文藝報》也做了相關報道,“京城的報道像點著了的爆竹一樣,很快引燃了陝西各級刊物的連鎖性反響以及整版的評論、特寫和創作體會。這些報道大大鼓舞了‘陝軍’們,成了陝西省作家協會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熱門話題。”
五部長篇一經問世,就引來無數的讚譽與批評。但是不得不承認在爭議中《白鹿原》等作品帶來了長篇小說閱讀熱潮。
《白鹿原》出版后,在普通讀者中引起了巨大反響,評論界評價其“達到了一個時期以來長篇小說所未達到的高度”
——馮牧
是一部激動人心的作品,怎麼評價都不過分,必將載入中國、世界文學史冊
——張韌
幾乎總括了新時期中國文學全部思考、全部收穫的史詩性作品。
——白燁
(對於《廢都》再版)原版中的“(此處作者刪去××字)”本來就是個噱頭,我覺得那都是瞎編的,因為沒有這些方框,文章也是完整的。當時就是這些框框顯得很觸目,有誘惑力,現在變成省略號了,這是出版商狡猾的規避了這個問題。
——張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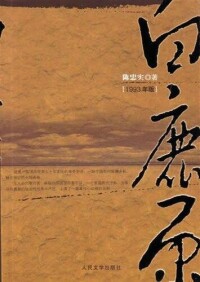
1993年版《白鹿原》封面
“好的作品應該有超前性、前瞻性。(20世紀)90年代初,知識界精神沉悶,文學也不像80年代中期活躍,不知道咋弄。寫《廢都》時我的身體最不好,加上社會的、家庭的變故,很沉悶。”《廢都》是現實題材,難把握,容易觸犯一些人。要是再晚幾年出版,就沒事了。當時的社會價值觀,性是敏感的話題,只要說性就被誣為流氓。
“陝軍東征”震動了中國文壇。
肖雲儒評價:“一個省在不長的時間裡,如此集中地推出了一批水平如此整齊的優秀藝術品,的確是陝軍文學實力的一次集中顯示,它表明在全國文學格局中,陝西創作力量作為一支重要方面軍存在的無可爭議的事實。陝軍東征’是被列入文學史冊的大事,如果用一句話概括30年中國文學,那就是‘療治傷痕,走出廢都,面向煩惱人生’。‘陝軍東征’是一個文學現象,當許多時髦作家相聚於賓館,旅遊於勝地‘玩文學’、‘侃文學’、炒知名度時,陝西作家有點落落寡合,但正是他們用盡心力寫出的作品,使新時期陝西文學有了和世界對話的基礎。
《“陝軍東征”的說法是誰最先提出的?》
這是一篇當事人對於“陝軍東征”出現爭議后的解釋,文章詳述了“陝軍東征”的來龍去脈,並將當時出現的爭議發表出來,有助於文學愛好者了解真相的意義是不消說的。
極其偶然的情況下,我於1998年10月24日才讀到7月24日的《陝西日報·周末版》,上有高建群的文章《我勸天公重抖擻》。讀罷第二小節《“陝軍東征”說法由來》,不禁瞠目結舌:不敢相信一個作家竟有如此“勇氣”,敢在當事人全部健在的情況下,大言不慚地說謊至此!
高文稱“陝軍東征”說法的由來,是1993年5月19日在京召開《最後一個匈奴》研討會後,“韓小蕙在徵求我如何寫會議消息時,我說,不要光寫《最後一個匈奴》,賈平凹先生的《廢都》,陳忠實先生的《白鹿原》,京夫先生的《八里情仇》,程海先生的《熱愛命運》,都即將出版或已先期在刊物上發表,建議小蕙也將這些都說上,給人一種陝西整體陣容的感覺。小蕙的報道名字叫《陝軍東征》,先在《光明日報》發表,後由王巨才同志批示在陝報轉載。新時期文學中所謂的‘陝軍東征’現象,稱謂緣由此起。”
這簡直是比天方夜譚還神吹的一段謊話。我當即打電話,把高建群此語念給幾位當年參加了會議的評論家和記者們,有的人失聲大笑,有的人連稱“說謊!說謊!”,還有人說“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家一致的結論,讓我馬上寫一篇澄清事實的文章,因為“陝軍東征”確已成為新時期文學的一個現象,會在文學史上留下一筆,目前趁當事人還全部健在,人證物證俱全,一定要搞得清清白白,免得給將來留下後患。
那麼好吧,我就寫。動筆之際,我又想到,此前,無論“陝軍東征”炒得多麼熱的時候,因為一些原因,我還從未就“陝軍東征”現象發過言,現在,索性一併在此說個一清二白吧。
1993年5月19日早晨,我去北京空軍招待所參加《最後一個匈奴》研討會。上電梯的時候,記得當時裡面有閻綱、周明、陳駿濤諸先生,好像還有唐達成先生。不知誰跟閻綱和周明開了句玩笑,說“你們陝西人可真厲害,聽說都在寫長篇。好傢夥,是不是想來個揮馬東征呀?”
後來在會上發言時,有人提起電梯里的這句玩笑話,於是,發言者紛紛跳開《最後一個匈奴》這一本書的思路,爭說陝軍群體的文學成果與特色。當時明確提到的有《白鹿原》和《八里情仇》,也有人模模糊糊提到《廢都》,因為《廢都》的書和刊都還沒有出來,《十月》編輯部怕人盜版,誰也不給看,據說當時只給了一位評論家看清樣,是要約他寫評論。
那一天,我因有事,聽完會沒留下吃飯就走了。回家后翻了翻《最後一個匈奴》,感覺語言太鬆散平淡,後半部寫得完全沒了精氣神兒,全書水平很一般,也就明白了為什麼與會者紛紛跳開它而大談陝軍。那麼,我的報道怎麼寫呢?按流行的辦法寫三行簡訊,是最省事的,但似乎有點兒對不起出版社和那麼多與會者,而且聽了那麼多發言,裡面也的確有內容,我苦苦思索著。後來突然心裡一亮:何不就在“陝軍東征”四個字上作文章呢?
《白鹿原》當時已在《當代》刊出,《八里情仇》已經由文聯出版公司出書,都不難找。唯一找不到的是《廢都》,但也好辦,我與該書責編田珍穎女士是好朋友,就撥通了她家的電話。老田的回答還是非常原則:“書再過一個星期左右就出來了,現在誰也不能給看。”我就說明了我要寫一篇關於陝軍的整體報道,請老田介紹一下《廢都》的大體情況,她是這樣回答我的:《廢都》是賈平凹第一部城市題材之作,反映了急劇變革中的中國社會現實。“是賈平凹對他過去作品的總的否定總的思考總的開拓”。
田珍穎是我十分尊敬的一位資深編輯,她的特點是第一極為敬業,第二文學鑒賞水平非常高,我很相信她的判斷,於是就放心地引用了她的話。
說實在話,當時我之所以寫《陝軍東征》這篇報道,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已注意到全國文壇上發生的一種變化,即長篇小說開始繁榮——經過80年代末的深刻的社會變革,全國有許多作家都沉下心思考了很多問題,然後埋首把這些思考寫成長篇小說。至1993年,有一些寫得快的已經出版,記得上海有趙長天的《天命》、陸天明的《泥日》、俞天白的《大上海》等11部或13部,山西有張平的《天網》、李銳的《舊址》(即出),浙江還一部誰的很有影響(對不起,手邊沒查到資料,以上例舉可能有誤)。作為一個敬業的文學記者,1991年,我曾及時報道了我國散文創作熱潮來臨的消息,對散文的發展起了一點小小的推波助瀾作用(見拙文《太陽對著散文微笑》),這一回,我同樣認為經過四年多的沉首下心,我國的長篇小說創作也將迎來豐收時期,我計劃一個省一個省地寫一寫,再為長篇的繁榮起一點點推動作用。
《陝軍東征》的報道就是這麼寫出來的。
《陝軍東征》寫完后,我把它交給我報總編室,就又開始忙別的事了,說實在的,類似《最後一個匈奴》那樣的研討會,一年我要參加幾十個,類似《陝軍東征》那樣的報道,在我的報道文字當中,也是很普通的一篇。我完全沒有預料到後來竟發生了那麼多的事情。
5月25日,《光明日報》以二版頭條位置,刊發出《陝軍東征》一文,約有2000字左右,的確佔了不算小的一塊。但對於報社來說,這並不算什麼了不得的消息。後來過了些日子,好像是周明先生告訴我,說《陝西日報》轉載了我的文章,問我知道不知道?我不知道,陝報沒有任何人通知過我,也沒寄給我樣報與稿酬。能轉載我當然高興,但這也很普通,因為我有很多消息被各種報刊轉載,不新鮮。
新鮮的事可是陸續來了。一天,我家的電話突然響了,是一個來自陝西省的長途,對方說他名字叫程海,寫了《熱愛命運》,問陝西什麼人搞陰謀陷害他,不讓他的名字出現在《陝軍東征》一文里?我一聽這是哪兒和哪兒呀,趕緊告訴他誰也沒有陷害他,報道是我自己寫的,陝西方面事先誰也不知道我寫這篇報道,也沒有定過調子,不信請問問別的記者,參加那會的各報記者有一二十個,您問誰都行。《陝軍東征》一文里之所以沒寫他,是因為沒有人提起他(事後我才知道,《熱愛生命》當時根本就還沒有出版)。我說的絕對是事實,程海放下了電話。沒想到,過了兩天,他又來了電話,說是“我們省委宣傳部已經決定,陝軍東征要提五部書,要把我的《熱愛命運》加上。”我有點兒不高興,心想事情早已過去了,怎麼還沒完沒了,就不客氣地回答說“怎麼提是你們省里的事,我的報道已經發了,跟我沒關係了。”(現在看來,我當時態度不好,不該說那麼硬的話。但後來我被告之,陝西省委宣傳部並不曾作出這一決定。)
又過了些日子,喝,可是不得了了,只見街上一些報紙上、書攤上出現了很多“陝軍東征”的標題、口號和宣傳字樣,到處都在“炒”陝軍。果真就賣了很多書,最明顯的是《八里情仇》,從第一版的6750冊,直線上升到十多萬冊(最後達到多少冊我也不知道)。《最後一個匈奴》也得到好處,一版再版不說,作者也聲名大噪。程海的《熱愛命運》也真的加進來了。後來還有許多搭車的書,都自稱是東征的“陝軍”,一時陝軍真是大大火爆,名揚天下。
這時再碰到陝西的或不是陝西的文友,多提到我為陝西“立了一功”,我心裡何嘗不明白,這有的是在諷刺我,暗指我瞎炒什麼陝軍。我只有暗暗叫苦:其實我的報道真的是一則很普通的消息,我寫的還真是比較實事求是的,瞎炒作的並不是我。更糟糕的是,報刊上竟然還出現了兩個省的兩個評論家打起筆墨官司,致使我原來一個省一個省地寫的計劃也泡湯了。後來聽說,還有人氣勢洶洶地到出版社去鬧稿費,揚言只要發現人家多印了一本也要罰款多少多少!出版社沒地方出氣,於是也只好罵我瞎炒,唉,我真是代人受過,心裡凄涼得很。
這也就是我為什麼一直不願出來說“陝軍”的主要原因。
說透了以上背景,似乎就不用理睬高建群的假話了,因為最明顯的一個事實,就是他把“陝軍東征”當作一個功勞往自己身上爭,我可是至今說不明白“陝軍東征”到底是功還是過?至少,還有待於時日的檢驗。
不過,事情還是應該說清楚好,免得像文友們說的,為以後留下後患。那麼,我就糾正高的這麼幾條謬誤:
1)、我至今根本不認識高建群,他也不認識我——我這裡“認識”的含義,是指有沒有私人交往。1993年我寫《陝軍東征》之前,陝西的作家裡只有劉成章、李佩芝、和谷和朱鴻認識我,因為他們幾個都是散文家,是我們“光明日報”文學副刊的作者,其餘,連陳忠實先生在內都不認識我,這不奇怪,我乃小記者小編輯一個。
迄今為止,除了一兩次公開的、有數十人參加的會議場合外,我沒有見過高建群,更不曾跟他說過話。
2)、當記者16年來,我寫過不計其數的消息,從來沒有一次“徵求”過當事人應該怎麼寫。如果說今天韓小蕙作為文學記者能為大家注意的話,恰正是因為我的每次報道都力求尋找到一個獨特的角度,不願人云亦云、一抄通稿了事。所以高建群說我徵求他“如何寫會議消息”,純屬子虛烏有。
3)、如前所述,《陝軍東征》一文中,並沒有提到程海先生的《熱愛命運》,這一個細節,高建群可是沒有注意到,所以,他說錯了。
4)、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細節,高建群至今還不知道的,就是“陝軍東征”字樣,當年並不是僅有我一個人使用,我記得賀紹俊先生在《文藝報》的報道中,也曾引用了這幾個字,只不過沒有用在大標題上,而是用在肩題里。所以,高建群怎麼也沒編出賀紹俊也去“徵求”他消息應該怎麼寫的假話,這可真是假的怎麼也是假的,總有破綻要露出來。
在寫本文的過程中,我曾一再地提醒自己,態度可別過激,語言一定要平和,把事情說清楚就行了,寬容一點,大度一點,給人家留一條可進可退的路。可是當我看到陝報上高建群的照片笑得那麼燦爛那麼從容,一點兒都沒有做了虧心事的樣子,又覺得義憤填膺——不糾正他,難道是我這麼多年來貪人之功地說了假話?!
我在想:為什麼在名利面前,有些人能夠眼都不眨一下,做得這樣厚顏無恥呢?智者莎尼蘭爾曾說過,“名譽是你的一封最有效的自薦信,你一生的前途都得依賴著它”,可是為什麼有些人還要為了爭名奪利,就不惜糟蹋自己的名譽呢?
在此,我只有一個要求,即請高建群正式做答:你說得究竟是真話還是假話?如果你記起確實是虛構了那一段情節,那麼就請公開予以糾正,我也不要求你做解釋或道歉;如果你堅持己說,那麼我將保留拿出人證物證,對薄公堂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