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找到2條詞條名為黃雨石的結果 展開
- 黃雨石
-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烈士
黃雨石
黃雨石
老黃名叫黃愛。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沉船、眾生之路、黑暗深處、虹、老婦還鄉、奧凱西戲劇集等等,都是用這個筆名翻譯發表的,2004年獲全國資深翻譯家稱號。老黃畢業於清華大學英文系,後來又考上了清華大學英文系的研究生,研究伯納德·蕭,一讀就是五六年。黃雨石是一個很平常的人,但做事卻要求自己盡量做到不平常。他退休前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英語編輯,編輯部許多審定、挖掘和校改的翻譯稿子,都是他一錘定音。算得上是不計名利的有功之臣。兒子黃宜思也是英語翻譯。
50年代初,老黃剛參加工作就參與英譯《毛澤東選集》。是不是錢鍾書帶他去的,不得而知。
50年代初是老黃大展宏圖的年月。當時,翻譯業面臨百廢待興的局面。儘管當時俄語十分吃香,但中國的近代翻譯事業無疑是從英語開始的。無論林紓的翻譯,還是嚴復的翻譯理論,都是依英語為“根”的。英譯中的翻譯事業有光榮的傳統,也不乏混亂的標準。由於老黃學英語的特殊經歷,對這樣的局面有清醒的認識,但老黃當時還只是個“小字輩”,幸運的是他遇上了一個好領導,當時負責外國文學的副總編鄭效洵,一位名副其實的出版家。他對解放前的出版狀況了如指掌,如什麼書是哪家出版社出版,誰寫誰譯,什麼刊本,他都能準確地說出來。他需要的是幾個具有真才實學的幹將,把新的局面打開。當時出版文學翻譯作品的只有人民文學出版社一家,上海譯文出版社的前身,也只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分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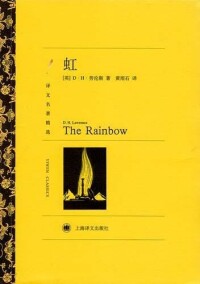
黃雨石譯作
雖然當時深受蘇聯那一套影響,但據老黃說,周揚當時對譯介外國文學有一個很藝術的指示:我們無產階級是在完成中國資產階級沒有完成的任務。這話今天聽來不倫不類,但當時可是金科玉律。大約在1958年,人文社出台了一個出版選題規劃,成千個選題,外文佔了4/5,單本、文集、選集、全集和叢書,樣樣俱全。這個選題計劃雄心勃勃,5年計劃的選題,如今四十年過去了也沒有完成。然而,它的影響相當大,至今全國各出版社出版的外國文學作品乍看五花八門,細細分析,基本沒有跳出它的框架。
把好譯著修訂出版的“關”。這項工作遇到的最大阻力是人們的頭腦發熱。據老黃說,大多數人的口號是“破舊立新”,要用“我們的新手譯出新的作品”。可翻譯是一門科學,應該實事求是。但具體的度掌握起來很難,稍不慎就有人說你是復古。老黃在這項工作中最大的功勞就是留住了朱生豪譯的《莎士比亞戲劇集》。當初編輯室多半人否定朱生豪的譯本,但老黃通過仔細閱讀,發現朱的翻譯十分難得。為了說服同事,老黃列舉了許多具體的例子,在辦公室里大聲朗誦,評析得失,曆數精妙,以理服人。人文版《莎士比亞全集》就是以朱生豪的譯本為基礎整理而成的。
這是最難做的一項工作。老黃與之打交道的都是活人。翻譯標準再寬鬆也是死的。翻譯本來就有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有時,你如果採用某人某部譯作,大家皆大歡喜;你如果質疑或否定某部作品,就得舉出大量的例子說服對方,而對方還必須是一個明白人。老黃講起這樣一個例子:雲南大學李從弼教授寄來了他的譯作《棄兒湯姆·瓊斯的歷史》。這是英國18世紀著名作家菲爾丁的代表作,全書八十餘萬字,故事情節生動曲折,但文字較難譯。李從弼的譯文質量不夠,經研究,退回去了。事隔不久,當時的社長王任叔去雲南採風,又把這部稿子"采"回來了。“采”來的稿子和投來的稿子畢竟不同,再退回去顯然棘手。後來老黃提出校訂的辦法,很有彈性地解決了這個棘手的問題,也為解決譯文粗糙的大部頭譯稿開了個好頭。這部譯作指定由蕭乾校訂,由於種種原因,一直拖到80年代中才出版,譯者李從弼已經作古,如今的譯者署名為“蕭乾、李從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