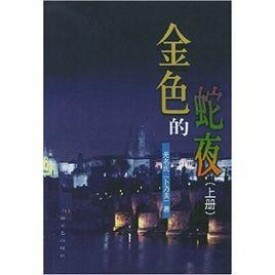金色的蛇夜
金色的蛇夜
無名氏,原名卜寶南,后改名卜乃夫,又名卜寧。原籍江蘇揚州,1917年1月1日生於江蘇南京。40年代,他的愛情小說《北極風情畫》、《塔里的女人》風靡一時,令萬千青年灑淚。書籍一版再版,生命力久而不衰。40年代開始創作代表作《無名書》。其他作品還有青春愛情自傳《綠色的回聲》,散文集《塔里·塔外·女人》隨想錄《淡水魚冥思》等數十種。80年代初定居台灣。
《無名書》總序
1998年我曾在拙作《無名氏傳奇》一書中這樣寫道:
……《無名書稿》複雜深邃的內容和巨大的藝術探索的獨創性工作,是需要時間讓人們慢慢認識和消化的。當然,這個時間是可以預期的。 .
這個時間終於等到了——在新世紀的第一春,這部巨著由上海文藝出版社第一次在中國大陸全文出版了。
自1960年5月3日無名氏為《無名書》畫下最後一個句號,到在大陸全文出版,這期間竟然長達四十一年之久。而伴隨著這漫長等待的,是這部書的傳奇式失而復得的遭遇以及作者的傳奇式隱而復出的經歷。這裡面充滿了“左”的肆虐,意的堅守,心的追求,愛的纏綿,僅此一點就足以寫出一幕幕令人迴腸盪氣、唏噓不已的話劇來。而這一切我都在《無名氏傳奇》一書中做過介紹,這裡就不贅述了。
然而這種等待又並非毫無補償——即使在中國大陸根本無法看到《無名書》的情況下,過去大陸出版的許多文學史就已屢屢提及此書且做出很高的評價,儘管這些文學史家並不諱言自
己未能一窺全豹的事實。我想,一個評論家在未看完作品前就貿然發表意見,這在文學評論上《無名書》也可算是創下了一項“吉尼斯記錄”。至於在域外,這部書用“久已享有盛名”來形容,我想也並不為過了。
這部書之所以引起人們高度的重視,我以為至少有下列幾點原因:
第一,《無名書》是一部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不論內容與形式都十分獨特的作品。它不屬於現實主義的範疇,而是一部現代主義的力作。眾所周知,在全世界的範圍內,現代主義實際上已成為20世紀文學與藝術的普遍潮流,然而在中國,由於社會發展階段相對於世界工業文明總趨勢的滯后,以及20世紀中國低位文化對於高位文化不停地征服,現代主義文學僅僅在20世紀之初,由魯迅發軔,綿延至三四十年代,陸陸續續綻開過星星點點的絢麗的小花,以後則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處在被打壓的地位,直到世紀之末,才又長出一些仿現代主義的四不象一類的東西來。這樣,20世紀的中國文學與世界先進民族文學相比。就無法產生出平等的對話關係。
我這裡絕不想把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做高下優劣之分,創作方法本無優劣。問題在於,我們的現實主義文學到底為全人類的思想寶庫提供了哪些前人所沒有的思想財富?除了魯迅等那幾位數得過來的真正大師級人物外,整個20世紀的中國文學所能供人言說之處實在是少得很。或者不如說,20世紀中國文學的優勢並不在這方面,而是主要集中在提供一整套培育“宣傳文學”的經驗及範本上。也許它們對於眼下的中國政治現實是必不可少的,但這對於現實主義的真正要求,似乎有點錯位。
另一方面,20世紀自然科學思想體系的重大發現,引發西方哲學思想的層出不窮的變革,對人們的觀念產生巨大的衝擊,一些過去人們常認為是理所當然的觀念發生了根本的動搖。比如說“造反”吧,過去人們總習慣地認為,社會出現了不公,人們活不下去了,唯一的辦法只能是“造反”,搞改朝換代,認為這可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然而事實是,中國的歷史上,“革命”也好,“造反”也好,都是相當多的,然而不管怎樣“革”,也無法創造出一個公正的社會來,所謂“革命”、“造反”的結果無非是克隆一個原先的自我。這就迫使人們不得不從人性的本質高度來重新認識自己,承認人性惡與人性善同是人類與生俱來的秉性,與隸屬於什麼階級根本毫無關係。為了創造公正合理的社會,人們應把智慧集中在創造科學公正的社會運作的遊戲規則上來。而對人性惡的發現與刻畫顯然是現代主義文學藝術對於世界文學寶庫所作的重大貢獻之一。這也就是說,當中國現當代文學連篇累牘、喋喋不休地探索、暴露中國社會制度的弊端時,現代主義的文學卻已經在更高的層面上解讀了這個問題。這兒出現的差距顯然並不是創作方法上的差距,而是哲學思想的差距。也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我們對於本國的現代主義的作品才應該給以更多一點的關注。
……
劉:大陸讀者一般容易將無名氏和他的兩本暢銷書《北極風情畫》、《塔里的女人》聯繫起來,也因此很容易僅僅把他當作一個通俗作家,但實際上,無名氏的創作有嚴肅重要得多的內容,他的生命大書《無名書初稿》全六卷,包括《野獸·野獸·野獸》、《海艷》、《金色的蛇夜》(上下冊)、《死的岩層》、《開花在星雲之外》、《創世紀大菩提》,洋洋數百萬字,創作時間從40年代中期一直到60年代初期,延續有十五年時間,在20世紀文學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在此,我想請您先談談對《無名書初稿》整體上的感受和評價。
陳:十多年前,我在寫《中國新文學整體觀》時曾通讀過無名氏在四十年代出版的創作,《無名書》當時只讀到了印出的前三種。我當時以法國夏朵勃利昂的浪漫主義創作流派為參照,認為他在很多地方“都流露出那位法國大師的藝術韻味”。一晃十年過去,又一次重新讀了《無名書》六卷,我覺得還是應該從浪漫主義思潮的角度來討論無名氏的文學史定位,讀其後期創作,以完整的六卷《無名書》為代表,藝術境界當在夏朵勃利昂的《阿達拉》以上,更讓人想起的是歌德創作的《浮士德》。雖然《浮士德》在中國有多種譯本,但這一西方知識分子永無止境的追求精神的象徵,在中國的非學術領域從來沒有受到過分青睞。對照中國讀者在二十年代熱烈歡迎少年維特;四十年代歡迎約翰·克里斯朵夫,這是一個十分耐人尋味的接受美學現象。究其根源,不但有東西方文化的傳統上的隔閡,也與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現實處境和廣場意識、啟蒙立場所形成的思維形態的制約有關。我在十年前的研究論文里就指出過這一現象,西方的浪漫主義只有被改造為抒情傳統才能在中國得以傳播,郁達夫的抒情小說正好成為這種改造的潤滑劑,而《無名書》從夏朵勃利昂式的傷感向浮士德式的探索的過渡,則註定它的寂寞與失寵。以郁達夫為始,以無名氏為終,這就是浪漫主義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命運。但正是這樣一種歷史性的空白才能顯現出《無名書》得天獨厚的價值,無名氏恰恰是跳出上述思維形態的窠臼而別開生面。他的藝術空間不在現實世界而在另一層面,即想象的空間,這也是浪漫主義者世襲的藝術空間。
在印蒂眼裡,這並不是一個女人,只是一大堆腐蝕。她有著日蝕時一般動物的恐怖情緒。為了反抗這過度喘息性的恐怖,她才有意放縱自己的本能幻想。在她身上,有沙也有金,金子竟然腐蝕了,也變成沙了。她那種情意蘊,是離奇的,該是維也納心理大師實驗室內的好對象,放在他面前,只引起一份多刺的重壓。但他並不驚訝。這份壓力是歷史的,並不是他個人的。只由於一個偶然,她此刻才替歷史發言、打手勢。她和他之間,現在比她和誰還更溝通。人類從沒有像他們此刻這麼了解過。她那份罌粟花型,較之五年前,光彩香味並沒有散佚太多,且由精神上更濃的毒素彌補了,而這份濃度,也正是她目前吸引他的主要因素。她的話、她的動作、她的線條與構圖,全部是一種氛圍,這片富於蛇的色彩的氛圍,五年前,他味同嚼蠟,這會兒卻當蜂蜜啜飲了。因為,他目前心靈深處,也正瀰漫著同樣氛圍。她胴體的豐腴,由懶散裝飾,比什麼珠寶都好。沒有某種自負決心,產生不出這派纏綿的懶散。
……
書摘1
海洋大風暴中舟子臉上的奇異沉默,被印蒂徹底理解透,那是許多年後的事。人必須經過一百次暴風雨後,才能徹骨瞭然這種面孔。在此後十年中,印蒂每遭遇深刻心靈悲劇時,就忍不住想起洪老大這張臉,這雙眼睛,幾條深鎖的皺紋,一張緊閉的嘴巴。它們補給他一千本哲學聖書所遺漏的,而且是最重要的遺漏。其實,一隻緊閉的嘴巴,不只在暴風雨中如此凸起,凡在海上跑過十年八年的,平時也如此凸起,不過,大風暴中凸得特別顯著而已。海上水手,少有好脾氣,那種雞尾酒會中的嫻雅、圓滑,對他們來說是另一個星球上的鏡頭。他們很少有女性的或陰性的言語,字與句全是從鍊鋼爐內錇鑄出來的。假如外交場合、人的態度常是弧形的、拋物線式的,水手場合的風度、就是多角形的了。他們精神幾何學里,似從未出現過圓周或圓錐體。像一些因暴風雨而深藏於洞窟中的獸,經常默默不響。一響,就是一頓咆哮,一個猛衝或狂撲。在靜止與猛衝之間,似無中間性動作。如果把一個老水手的背景和他自身姿態擴大了,人就較易了解我們這個世界,和這個“人間”。文明常是一層色彩、金粉,塗抹在原始獸的雕像上。暴風雨捲來一次、兩次,色彩和金粉不過被衝去一層、兩層。但捲來十次二十次以後,我們所看見的,只剩下那頭並不美麗的原始獸了。獸原是天然的,彩色與金粉卻是外來的。一天比一天,印蒂愈益了解這種獸式的大靜和大動,這兩者其實是同一原素的兩面。
嘴巴是一隻翻雲覆雨的怪物。每個人身上都蹲著它,每個人都殫精竭慮,把它作高度玩弄。但你玩得太久了,總有一天,死於自己的玩弄。起先,你想說很多很多話,你說、說、說,似乎說三年零六個月,也說不完,這個怪物是只萬能魔杖,任何時候,只要你一舞弄,它就會點石成金,點陸為海,點地獄為天堂,給你帶來圓潔的希臘石柱,熱帶的花,非洲的蝴蝶,威尼斯的月,西湖的柳,你要什麼,它點什麼,你說、說、說,稍後,你漸漸感到,這怪物有時也不大柔順了,它的萬能宮殿缺了幾個口,有時也點不出什麼了。你覺得三年零六個月也說不了的話,是永遠說不了了;你不說,是說不了;說了,也說不了,而三天並不比三年少說什麼。再后,即在三天內,你也聽見友人的呵欠聲,以及你自己的呵欠聲,而三小時也比三天不少說什麼。你還是說、說、說,終於有一天,你突然不想說了,而不說一句,和說三年零六個月是一樣的,可能,前者還說得更多一點。在怪物外層,一個厚厚的硬殼已結成了。你覺得,躲在殼殼里,不讓怪物衝出去,比衝出去好。從這時起,怪物是真正死了。上帝所賦予的嘴巴機能也死了,於是天下太平,而只有這一次,才真正天下太平。於是,一張古舟子的臉便成宇宙萬象的最後結論。不認識的,以為是一片麻痹,能洞透的,從它後面,可以辨識無數風暴的殘剩疤痕痂結。
大風也好,大浪也好,海殘酷也好,舟子臉上殘酷也好,生活兩腳規既已畫定一個圓周,他們就得在它裡面活動。印蒂他們這次從海上回來不久,就“出”掉所有貨物,又“進”了一批新貨。約莫三星期後,他和甄佘兩個,第三次飄揚起三角帆。這次航行,因為駕輕就熟,一切迅速順利,來回只不過二十天左右。返S市后,他們決定,在第四次航行以前,好好休息一下。好好歹歹,這本“淘金記”總算抒寫得很像樣子,而一本好“淘金記”的作者,是不會忘記續寫一本好“拋金記”的。因此,他們決定擇一個周末舉行一個別出心裁的冶遊會,盡情歡樂一番,好實現印蒂在上次航行遭遇大風暴后的提議。
大約是在這次冶遊會的前一星期,那是一個傍晚,印蒂正在公司里,他接到林郁電話,約他和庄隱去吃晚飯。
“有什麼事嗎?”
“沒有什麼。一個老朋友在我這裡。”
“誰?”
“暫不宣布。你來了就知道。你們快點來吧!”
半小時后,印蒂與庄隱才走進客廳,一張架著克羅米白邊眼鏡的白俊面孑乙,就晃在他們眼睛里,接著是一陣嘻嘻哈哈的笑聲。
“沒有想到是我吧?哈哈哈哈!”
印蒂怔住了。“哦!惟實!真沒有想到是一一”
“想到的,偏不來。想不到的,偏偏來了。哈哈哈哈!”
一點不錯,這正是范惟實。薄薄克羅克斯鏡片後面,依然是那雙幽默的小眼睛。神態依然是那副上海白相人調調兒,帶點油油滑滑的。
“你什麼時候出來的?”庄隱急切而關懷的問。
“該進去時,就進去了。該出來時,就出來了。我們這個國家,一切都是活見鬼。嗯?你知道么,一切全是活見鬼!”
“去年,我記得林郁曾告訴我,說你放出來了。可是,誰也不知道你在哪裡。”印蒂微微興奮的說。
“放是放出來了。不久又被捉進去了。活見鬼,送到什麼反省院。現在,我算‘反省’竣工,可以送到曲阜,陪侍孔孟了,於是從頭到腳OK,又可以在光天化日下見人了。真正是活見鬼!活見鬼!”停了停,帶點沉思。“其實,這隻怪我自己不好。”
他解釋:“九·一八”后,政局的擺畫出另一種弧線,蔣介石下野,一切動蕩,他的兩個政界親戚四齣活動,把他保釋出來。“一.二八”后,蔣又出山,政治的擺又回歸老旋律。因為他曾與左獅、賈強山他們有所往還,不久又被捕,送到浙江反省院,做了一年“人手足刀尺”的小學生,一些油漆匠式的“導師”們,成天到晚,用大板刷子把“孔孟之道”刷到他腦膜上、耳輪邊。
“反正活見鬼。活見鬼。我們這個國家的歷史,不折不扣,已變成一部‘聊齋志異’,成天鬧鬼。結果把我弄得很倒楣,如此而已。”
“怎麼,你出來后,見到左獅他們么?是怎麼一回事?”印蒂急匆匆的問。
“我的事情,你們還不知道么?”
印蒂搖搖頭。
“哦,你問林郁吧,我也懶得說了。反正又是一部新聊齋。哈哈哈哈!”
林郁於是略說了個輪廓。范出獄不久,迎接他的,並不是同志的熱情的手或擁抱,而是一張悔過書,罪名大體和印蒂當年一樣。
“真的么?”庄隱氣憤的問道。
“這就叫做革命的新陳代謝。老細胞已榨過了,燈盡油幹了,應該清除乾淨,換上嶄新細胞。好在火山般的青年萬萬千千,到處有的是,我們活該被淘汰。被打人冷宮。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