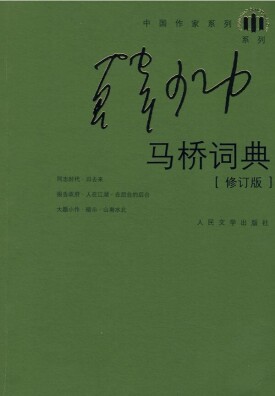馬橋詞典
韓少功所著小說
《馬橋詞典》,是中國作家韓少功1996年出版的一部小說,按照詞典的形式,收錄了一個虛構的湖南村莊馬橋弓人的115個詞條,最早發表於上海文藝出版社的《小說界》雜誌1996年第2期,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單行本。
《馬橋詞典》,最早發表於上海文藝出版社的《小說界》雜誌1996年第2期,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單行本。1999年被《亞洲周刊》評為“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之一。2003年8月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英譯本“A Dictionary of ”。
《馬橋詞典》出版后,有人批評該書抄襲了米洛拉德·帕維奇的《哈扎爾辭典》。作者韓少功因此起訴評論者侵犯其名譽權,並獲得勝訴。
《馬橋詞典》集錄了湖南汨羅縣馬橋人日常用詞,《馬橋詞典》計一百一十五個詞條。它以這些詞條為引子,講述了古往今來一個個豐富生動的故事,引人入勝,回味無窮。
《馬橋詞典》是韓少功的一部力作。它內容嚴肅,筆法獨特,不愧為一部優秀的長篇小說。《馬橋詞典》以詞典的形式搜集了中國南方一個小村寨里流行的方言。這本詞典從純詞典的形式迅速過渡為一個個故事。其中講述了“文革”時期被下放到邊遠地區的“知青”的生活的點點滴滴。
| 《馬橋詞典》條目首字筆畫索引 |
| 一畫一九四八年(續) |
| 二畫九袋 |
| 三畫三毛三月三三秒虧元馬同意馬橋弓馬疤子(以及1948年)馬疤子(續)小哥(以及其它)鄉氣下(以及穿山鏡) |
| 四畫天安門不和氣不和氣(續)開眼月口公地(以及母田)公家雙獅滾繡球火焰 |
| 五畫龍龍(續)打車子打玄講打起發打醮民主倉(囚犯的用法)白話台灣漢奸歸元(歸完)發歌 |
| 六畫老表夷邊壓字同鍋紅花爹爹紅娘子朱牙土企屍江軍頭蚊問書 |
| 七畫走鬼親呀哇嘴巴你老人家(以及其它) |
| 八畫現楓鬼肯羅江官路話份憐相怪器放轉生放藤放鍋寶氣寶氣(續)泡皮 |
| 九畫科學茹飯梔子花茉莉花掛欄背釘貴生賤荊界瓜結草箍狠神神仙府(以及爛杆子覺洪老闆覺覺佬津巴佬 |
| 十畫萵瑋根格破腦(以及其它)哩咯啷暈街豺猛子流逝漿冤頭罷園 |
| 十一畫夢婆黃皮黃茅瘴甜清明雨 |
| 十二畫散發黑相公黑相公(續)隔鍋兄弟蠻子(以及羅家蠻)渠道學 |
| 十三畫碘酊嗯煞 |
| 十四畫以上模範滿天紅撞紅顏茶嬲飄魂嘴煞(以及翻腳板的)磨咒懈懶(男人的用法)醒 |
1968年,出生於中國湖南省的韓少功在15周歲時被下放到一個偏僻的村子“馬橋”。楚國詩人屈原投江的汨羅江就在這個村子旁流淌。當時文革正在轟轟烈烈地進行。中國共產黨把大批知識份子下放到農村或工廠從事體力勞動。韓少功在馬橋生活了6年。
作者韓少功在湖南師範大學畢業、成為中國著名作家后編寫這部小說,按照詞典的形式,收錄了一個虛構的湖南村莊馬橋的115個詞條。既有外部世界從不使用的獨特詞條,也有外界廣泛使用的詞條,但在馬橋,有些詞條的意義稍有不同。僻如說“暈街”,這是只在偏僻農村才有的單詞,指人到城裡才會出現的臉發綠、失眠等現象。相反,“醒”在外面的世界中是指從“夢或酒醉狀態醒來”,具有積極的一面。但這個詞在馬橋卻用來表示“愚昧”。
“世人皆醉我獨醒”來自屈原的詩在馬橋人聽來已完全別有體會。韓少功從這簡短的趣聞中解讀出了(一直受中央政權壓迫和漠視)的馬橋人享有的獨特歷史和思維。
雖然一段一段的文字看上去簡短精緻,但卻是貫穿於馬橋人的歷史和苦難。《紐約時報》評價說“讀者會在不知不覺中沉浸在馬橋人奇異的思維之中,這是一部像抽象派美術作品一樣的小說。作品通過馬橋方言展現了文革期間發生的各種微妙的精神失落感和可笑的衝突。”
小說的主線不可以概括為“主人公A遇到主人公B,作了一件事C。”韓少功寫道“我開始逐漸不喜歡有主導性人物或主線或主流情緒的小說。相比之下,由2、3、4個的因果關係交錯複雜的線索組成的群體故事頗為好感。”
從這一點看,這部小說與塞爾維亞詩人米洛拉德-帕維奇的小說《哈扎爾辭典》結構相似。帕維奇也是藉助辭典的形式描寫了古代和中世紀生活在黑海沿岸繼后被滅亡的哈扎爾民族的歷史。
素材來源
故事的大部分素材來源於韓少功的親身經歷,這部佳作捍衛了獨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同時向千篇一律的泛國際化趨勢吹響了反抗的號角。
對韓少功而言,故事稱做詞典本身就是把這個詞的含義延伸了。每個詞的含義得到了充分的註釋,同時他們又作為引子引出詞語背後看似散亂的作者的思緒,這貌似不經意的思緒將一個個詞語連成完整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這些詞不是按照西方的字母順序排列的。
例如“江”這個詞條後面列出了具體的江名以及江名的由來——不知不覺你就會置身於知青們的故事中:如何與船夫賴賬,如何丟掉他們所窩藏的槍支。讀了幾頁后,故事中的人物一一呈現,他們的市井生活構成了故事的點點滴滴
《馬橋詞典》遴選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後期以來成就突出、風格鮮明、有廣泛影響力的作家,對他們的作品進行全面的梳理、歸納和擇取;每位作家的作品為一系列,各系列卷數不等,每卷以其中某篇作品的標題(長篇作品以書名)命名。《馬橋詞典》是該系列叢書的其中一本,供讀者閱讀賞析。
作品分析
《馬橋詞典》這部長篇小說沒有採取傳統的創作手法,而是巧妙地糅合了文化人類學、語言社會學、思想隨筆、經典小說等諸種寫作方式,用詞、典構造了馬橋的文化和歷史,使讀者在享受到小說的巨大魅力的同時,領略到每個詞語和詞條後面的歷史、貧困、奮鬥和文明,看到了中國的“馬橋”、世界的中國。小說主體從歷史走到當代,從精神走到物質,從豐富走到單調,無不向人們揭示出深邃的思想內涵。
韓少功在《馬橋詞典•編撰者序》中說:“任何特定的人生,總有特定的語言表現。”每一種語言,都反映著特定生存狀態、民俗文化、以至更深層的生存哲學和思想理念。而作家對語言的這種特性和功能有深刻而切身的體會,所以他編成了這樣一部大詞典,用語言的故事講述著社會、生活、文化與哲理。
例如,在“馬疤子(以及1948年)”和“1948年(續)”中馬橋人用“長沙人會戰那年”、“茂公當維持會長那年”、“張家坊竹子開花那年”、“光復在龍家灘發矇那年”等不同說法來表明公元紀年1948年,反映了馬橋人奇特的時間觀念和歷史觀。也揭示了一種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時間的歧義性”。而“蠻子、羅家蠻”的詞條里,追溯著歷史的淵源;“撞紅”的詞條里,由現存的習俗追溯到人類文明史中原始而野蠻的時代。這裡,語言體現人類追溯家族淵源的主題。
有些詞,更在作家簡潔精要的議論中折射著生存的文化與哲學。如馬橋人用“同鍋兄弟”代替同胞兄弟的說話,相應地,女子出嫁叫“放鍋”前妻稱“前鍋婆娘”,後妻稱“后鍋婆娘”。作家在這裡說:“可以看出,他們對血緣的重視,比不上對鍋的重視,也就是對吃飯的重視。”正所謂“勞者歌其事,飢者歌其食。”這正反映了艱難的生存狀態下人們樸實而簡單得令人心酸的生活追求,這種追求世世代代流傳下來,積澱成了一種語言習慣、一種文化、一種思想觀念。這裡包含著一種辛酸,也包含著對這種原始的生存追求的敬意和信仰。
有些詞反映了馬橋人的文化生活,也反映了馬橋人,以至作者的文化觀念。在老百姓艱苦單調的日子中,唱歌、斗歌是他們唯一的娛樂與消遣。而唱男女情事的歌更是對他們人性慾望的一點滿足。萬玉因為唱不慣迎合政策的春耕頌歌而放棄逛縣城的美差、出風頭得榮譽的機會,臨陣逃脫。作者說:“他簡直有藝術殉道者的勁頭。”這裡包含立刻作者對藝術與政治意識形態關係的反思。
作品導讀
結構
開創詞典式的小說
幾乎所有的讀者,在看過《馬橋詞典》之後,都驚訝於其特異的文本結構:傳統中對於小說的定義於它是不合適的,沒有主要的人物,沒有一條一以貫之的線索,也沒有所謂的情感衝突作為故事推進的動力,有的,是一個個詞條的羅列,是每個詞條後用或者是作出的標誌,是詞條后的娓娓道來,以至於不少人認為,這是一部先鋒小說。事實上,《馬橋詞典》也一直被認為是先鋒小說的代表作之一。但在王族看來,這種有意放棄了小說敘事功能的寫法,並非一句先鋒小說可以定義,“《馬橋詞典》是力圖走一個相反的方向,努力尋找不那麼歐化、或者說比較接近中國傳統的方式”,言下之意,《馬橋詞典》沒有像其他的先鋒小說一樣,玩一些後現代,它更多關照的,還是中國的傳統文化。
《馬橋詞典》上世紀末發表時,因其文本結構的奇異,還引來爭議,有評論者認為,這是抄襲了塞爾維亞作家米洛拉德﹒帕維奇的《哈扎爾辭典》,雖然韓少功起訴評論者侵犯其名譽權並最終勝訴,但對於這部小說的寫作方式依然爭議不下,直到最後,王蒙出面說道:《馬橋詞典》是開創性的,它的意義在於開創了一個新的小說創作模式,即詞典小說,算是有了定論。對王蒙的評論,王族的理解是,“這裡面有幫韓少功定義的意思,同時也阻絕了後來者對這種形式的模仿,因為太容易模仿,也就太容易被人看出而加以詬病。”
這種詞條式的寫作,雖然具有開創性的意義,但仍有不少人擔心,這種小說儘管好看,但容易散。王族並不同意這種看法,他說,這些看似獨立的詞條,實際上是具有內在的錯綜複雜的聯繫的,“詞條之間最終完整而又混沌地構築起了馬橋這個虛構的地域”。
文本
將語言作為研究對象
韓少功在解釋為何會創作《馬橋詞典》時曾表示,“我願意與讀者共同考察一下具象符號在人生中的地位和作用,包括它是怎樣介入了我們的記憶、感覺、情感、性格以及命運;我們還可以考察一下具象符號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看它是怎樣介入了我們的教育、政治、經濟、暴力、都市化以及文明傳統。
最後,我將回過頭來探討一下語言與具象怎樣相互生成和相互控制,並且從這一角度來理解現代知識的危機”。或者,在讀者看來,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命題:詞條,或者說語言本身,成了被重新研究、另類解構的對象,並且,這些“具象符號”被作者上升到一個社會學的高度,這樣的研究結果,是否有其必然性及合理性呢?
對此,王族表示,《馬橋詞典》以“詞典”的方式,在紙面上復活了一個陌生的“馬橋世界”,本身就是在提醒人們,語言本身具有足夠的力量,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構築起社會本身:“一個來自偶然的詞語可以漸漸固化成為社會生活的一部分,一句話、幾個詞語的組合也可以在有意無意間改變一個人的生活。”
這個觀點其實並不新鮮,現代語言學的奠基者、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就曾論斷,語言存在於個人意志之外,是社會每個成員共同具有的,是一種社會心理現象。
就在“韓少功發現海南的漁民在脫離了他們本身所有的方言以後,只能用‘大魚’‘海魚’這樣簡單空洞的詞語來表達本該是漁民生活中最富於表達的內容,語言或者說,被具象化后的詞條、句子,顯示出了對人生活的深刻影響”。韓少功甚至說,“一旦離開語言,我並不比一條狗或一個小孩更具有智能的優勢”,在王族看來,韓少功的這種說法,實際上是在強調他的創作目的與指向———人,只能生活在語言中。
筆法
近散文化的寫作
儘管被定義為詞典小說,還是有不少讀者認為,《馬橋詞典》幾乎可以算得上是一部散文集。在王族的眼裡,他也不曾將《馬橋詞典》當作小說來對待。“多年來,我沒有把它當小說來看,而是當散文來看”,王族說,“如果它是一部20萬字的小說,我可以一口氣看完,但它是這樣一章章獨立成篇的,而且它的每個單篇都特別有魅力,可以反覆去閱讀”。
有讀者表示,將《馬橋詞典》中單獨成篇的短文拆開來,除了少部分篇章,比如“甜”、“白話”、“虧元”、“打車子”以及部分關於人物的詞條,其水準並不比韓少功的《月蘭》、《爸爸爸》、《女女女》之類的單篇更高。但王族認為,《馬橋詞典》不失為一部成功的作品,文字沒有多餘的修飾,很利落,而且讀來意蘊悠長。“很多人寫作不自覺地運用大量形容詞,以突出文字華麗美,《馬橋詞典》里有句:‘忽然覺得眼睛里有濕潤的一旋……幸好一場秋雨落下來’,他的文字不動聲色,不直接寫眼淚,卻又讓人感覺分明是在寫眼淚,卻又就此打住,不再延伸,特別美妙”,“韓少功的書無論是開篇還是中間隨便一頁,都經得起反覆閱讀,這樣一本書用十年時間去看,還覺得它有很大影響力,我就覺得非常成功了”。
更讓王族感到興味盎然的還有韓少功本人,“有時候我就很奇怪,韓少功的文學作品很柔軟,很少有激烈的東西,很隱約,很藝術性,但是你看韓少功的訪談,看他談一些文學作品,包括他經常作一些學術性的東西,非常縝密,你會感覺他是一個學者。就是一個柔軟一個堅硬,讓人感覺他是一個多面性的人物。後來我就發現,擺在作家面前實際上是兩條路。一條路,是怎麼樣去寫,另一條路,是怎麼樣去學習。”王族說。
比較
一個外來者的“發現”
上世紀九十年代,先鋒小說作家重新審視歷史、社會、現實,湧現出了很多優秀的作品,王族將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與《馬橋詞典》一起比較,他認為前者有意將血淋淋的現實極端化,而後者卻是唯美,“很多地方的描寫看上去很美。”在他眼裡,唯一可與《馬橋詞典》媲比的同期先鋒小說,只有張承志的《心靈史》。
但在記者看來,王族關於《馬橋詞典》與《許三觀賣血記》的比照是有些牽強的。《馬橋詞典》看來叫人感動,不在於敘述了某些血腥的事實,而在於,對很多詞語的認識,的確是立在一個進入了原始人視角的知青的身份上,包括“前鍋婆娘”、“后鍋婆娘”,把“鍋”當成一種衡量事物的最重要的標準,甚至超越了法律,這就是他們生活的真實的狀態。這種娓娓講述的辛酸,是真正深入人心的。見了血,只會覺得很暴力,很血腥,但這種痛苦是神經綳了一下的痛苦,不像《馬橋詞典》里,那種慢慢的浸潤折磨。就像是少林神功和武當綿掌,少林功夫固然猛烈,但是屬皮外傷,武當綿掌看似柔軟,但它是內傷———這種內傷能引起人們更深遠的痛苦和共鳴。
記者認為,提起《馬橋詞典》,一個湖南鄉村的背景,鄉土化的語言,最應該提及的,應該是湖南作家沈從文和他的代表作《邊城》。而他們的區別,亦不在於文字的優美與否,而在於作者所處的創作視角。《馬橋詞典》在文本模式的創新上,更先鋒,採取很多西方小說技法。但地域形成了個人氣質,韓少功是城裡下鄉的知青,呆的時間長了,固然對鄉下人的行為、思維、精神、語言慢慢熟悉、接受,但於鄉土的文化深處,他終究是個“外來人”,所以他只能“發現”並試圖理解鄉土文明以及鄉土上的人與事,而沈從文以一個土生土長的“湘西人”,站在鄉下人的立場向大山之外的人介紹邊城,他筆下的邊城是形神兼備的。
編輯推薦
同志時代·歸去來,報告政府·人在江湖·在後台的後台,大題小作·暗示·山南水北。
語言與事實的關係是一個非常危險的遊戲,也是一個非常美麗的遊戲。小說的長與短,成與敗,都在這裡。小說不接受科學家給定的世界圖景,而要刨造另-種世臁,包括在女人和鮮花間,在什麼與什麼之閭,重新編定邏關係。
——韓少功
《馬橋詞典》入選《亞洲周刊》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
《馬橋詞典》集錄了湖南汨羅縣馬橋人日常用詞,計一百一十五個詞條,它以這些詞條為引子,講述了一個個豐富生動的故事。
這部長篇小說糅合了文化人類學,語言社會學.信息傳播學、文藝學諸種寫作元素,用詞典形式構造了馬橋的文化和歷史,使讀者在享受到小說的巨大魅力時,領略到每個詞語和詞條後面的歷史和文明,看到了中國的“馬橋”、世界的中國,這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重要收穫。
創作風格
《馬橋詞典》在許多方面都延續了韓少功以往的創作風格,但在小說的敘事文體上卻開創了一種新的小說敘事文體--用詞典的語言來寫小說。“馬橋”是個地理上的名詞,據小說的敘事者介紹,“馬橋”是古代羅國所在地,就在楚國大夫屈原流放和投河的汨羅江旁。故事以敘事者下鄉當知青的年代為主體,向上追溯到各個歷史時期的生活片段,向下也延伸到改革開放以後,著重講的是70年代馬橋鄉的各色人物與風俗情景。但這些故事的文學性被包容在詞典的敘事形式裡面,作家首先以完整的藝術構思提供了一個“馬橋”王國,將其歷史、地理、風俗、物產、傳說、人物等等,以馬橋土語為符號,彙編成一部名副其實的鄉土詞典;
然後敘事者才以詞典編撰者與當年插隊知青的身份,對這些詞條作詮釋,引申出一個個文學性的故事。韓少功把作為詞條展開形態的敘事方式推向極致,並且用小說形式固定下來,從而豐富了小說的形態品種,即在通常意義上的“日記體小說”“書信體小說”之外又多了“詞典體小說”.這部小說在語言上的探索更加成功些。在以往小說家那裡,語言作為一種工具被用來表達小說的世界,而在《馬橋詞典》里,語言成了小說展示的對象,小說世界被包含在語言的展示中,也就是說,馬橋活在馬橋話里。
韓少功把描述語言和描述對象統一起來,通過開掘長期被公眾語言所遮蔽的民間詞語,來展示同樣被遮蔽的民間生活。儘管他在講解這些詞語時仍不得不藉助某些公眾話語,但小說突出的是馬橋的民間語言,文本里的語詞解釋部分構成了小說最有趣的敘事。如對“醒”的解釋,在馬橋人看來,醒即糊塗,他們從屈原的悲慘遭遇中看到了“眾人皆醉,唯我獨醒”的格言背後所包含的殘酷現實,這與魯迅筆下的“狂人”意象一樣,既是對先驅者的祭奠,又是對國民性的嘲諷,也包含了民間以自己的方式對三閭大夫的同情……所有這些,不是通過人物形象,不是通過抒發感情,甚至也不是通過語言的修辭,
它是通過對某個詞所作的歷史的、民俗的、文化的以及文學性的解釋而得到的。即使在一些故事性較強的詞條里,它主要的魅力仍然來自構成故事的關鍵詞。象“貴生”一詞的解釋里敘述了“雄獅之死”,雄獅本是個極有個性的農民孩子,他誤遭炸彈慘死後,小說重點闡釋了一個民間詞“貴生”的含意,即指男子18歲、女子16歲以前的生活。在農民看來,人在18歲以前的生活是珍貴而幸福的,再往上就要成家立業,越來越苦惱,到了男子36歲女子32歲,就稱“滿生”,意思是活滿、活夠了,再往上就被稱作“賤生”了。所以,鄉親們對雄獅的誤死並不煩惱,他們用“貴生”的相關語言來安慰死者父母,數說了人一旦成年後就如何如何的痛苦,讓人讀之動容的正是這些語詞里透露出來的農民對貧困無望生活的極度厭倦,雄獅之死僅僅成了民間語言的一個註腳。
《馬橋詞典》是對傳統小說文體的一次成功顛覆,而它真正的獨創性,是運用民間方言顛覆了人們的日常語言,從而揭示出一個在日常生活中不被人們意識到的民間世界。馬橋的人物故事大致分作三類:一類是政治故事,如馬疤子、鹽早的故事;一類是民間風俗故事,講的是鄉間日常生活,如志煌的故事;還有一類是即使在鄉間世界也找不到正常話語來解釋和講述的,如鐵香、萬玉、方鳴等人的故事。
第一類故事是政治性的,含有歷史的慘痛教訓。如對隨馬疤子起義的土匪的鎮壓、地主的兒子鹽早所過的悲慘生活,都是讓人慾哭無淚的動人篇章,閃爍著作家正義的良知之光。比較有意思的是第二、三類,馬橋本身是國家權力意識和民間文化形態混合的現實社會縮影,各種意識形態在這裡構成了一個藏污納垢的世界,權力通過話語及對話語的解釋,壓抑了民間世界的生命力,第二類民間風俗故事正反映出被壓抑的民間如何以自己的方式拒絕來自社會規範和倫理形態的權力,如志煌的故事,是通過對“寶氣”一民間詞的的解釋來展開的,在其前面有“豺猛子”的詞條,介紹了民間有一種平時蟄伏不動、一旦發作起來卻十分兇猛的魚,暗示了志煌的性格,而“寶氣”作傻子解,這個詞語背後隱藏了民間正道和對權力的不屈反抗,最後又設“三毛”詞條,解釋一頭牛與志煌的情感。
通過這一組詞條的詮釋,把極度壓抑下的中國農民的所恨所愛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第三類被遮蔽的民間故事更加有意思,像萬玉、鐵香、馬鳴等人,他們的慾望、悲愴、甚至生活方式,就連鄉間村裡的人們也無法理解,也就是說,在權力制度與民間同構的正常社會秩序里,無法容忍民間世界的真正生命力的自由生長,這些人只能在黑暗的空間表達和生長自己,在正常世界的眼光里他們乖戾無度不可理解,但在屬於他們自己的空間里,他們同樣活得元氣充沛可歌可泣。這種含義複雜的民間悲劇也許光靠幾個語焉不詳詞條和不完整的詮釋是無法說清楚的,但這些語詞背後的黑暗空間卻給人提供了深邃的想象力。
成功因素
《馬橋詞典》1996年出版,當時因為一樁公案,分散了人們的閱讀注意力。實際上它是一部很有趣味的小說。它以“詞典體”為體例,分為150個詞條,對馬橋這一湖南汩羅縣的小村落作了詳盡描寫,構築起一座立體的“馬橋世界”。促使作品成功主要有兩個因素:獨特的敘事方式和方言的框架。
首先,作品採用了獨特的文體方式。韓少功將這部小說寫成一部詞典,是頗具匠心的大創新。作者本意在於構建一座立體的民俗世界,因而拋棄了傳統的以主要線索和人物貫穿、推動情節發展的小說模式,而採用“詞條”的方式,創作一部“馬橋人的簡明百科全書”(韓少功)。以往的小說是縱向的,一維的,至多是分幾條線索交替並進;而《馬橋詞典》(下簡稱《馬》)是立體的,三維的,它的150個詞條縱橫聯繫,交織成立體的網路,歷史傳說,方言土語,鳥獸蟲魚,各式人物,無不包括在內。
描寫農村生活,蕭紅的《生死場》是頗為成功的一部。與《馬》進行對比,就可看出兩者的區別。《生死場》採用傳統的敘述方式,以抗戰前後的東北某鄉村為背景,描寫其村民混沌悲慘的生活。它以時間為線索,縱向展開一個個人物的故事。王婆、金枝、月英、二里半、李青山……諸多人物的悲歡離合、命運際遇,構成小說的主體。而《馬》既展開諸人物的故事,又全面地展示馬橋的風土人情,物產傳說,它的各個詞條,看似獨立,實則前後常有內在聯繫,可分可合,既不影響描述某一人物的諸多細節,又可以自由地介紹馬橋各種事物。如書中“漢奸”、“冤頭”、“紅娘子”、“渠”、“道學”四個聯繫排列的詞條,既是分別介紹了馬橋的風俗物產,又集中描述了鹽早這一人物及“我”與他交往的故事,線索清晰,明白易懂;而像“漿”、“軍頭蚊”、“顏茶”、“賤”等與前後聯繫不大的詞條,也不顯突兀,易於為讀者接受。可以說《生死場》描繪的是一個鄉村的許多故事,而《馬》描繪的是一個有許多故事的鄉村。
其次,《馬》一書以方言辭彙作為其主體框架,也是使作品成功的重要一點。《馬》是馬橋話的詞典,以馬橋方言辭彙為詞條,每個辭彙都包含其特有的內涵,具有在馬橋地區的普遍意義。而每個詞條引伸出來的人物、故事,一定程度上是為了詮釋這一詞義服務的。一這150個詞條為框架構成的語言系統,表達了馬橋人獨特的文化背景、思維觀念。換成別的語言,是難以準確而簡練地表達出來的。比如“夷邊”,是馬橋人對除馬橋外其它地方的稱呼,頗有輕蔑之意。這一稱呼流露出馬橋人自居“中央”的觀念和對其它任何事物的輕蔑和漠視。又如“貴生”,以志煌兒子雄師慘死的故事,引出馬橋人關於人生的看法:男子十八歲以前,女子十六歲以前,是有福氣的,稱“貴生”;男子三十六歲、女子三十二歲以前,是“滿生”;活過這一段,是活滿了,以後就是“賤生”了。這反映出馬橋人生活條件的惡劣和他們對生活的超然、知足的心態。還有“飄魂”、“科學”、“暈街”等等,都是獨特承載馬橋人思想的詞語,無法用其它語言辭彙替代。馬橋世界與馬橋話是魚和水的關係,如果將這條魚從水裡撈出來晾著展示,必會失去其生命力。用馬橋話描繪馬橋,才還其真實的本來面貌。
《馬橋詞典》成功地塑造出“馬橋”這樣一個立體的民俗世界。“詞典體”的敘事方式,以方言辭彙為框架結構,是作品成功的重要兩點。
品讀感悟
《馬橋詞典》被定義為當代名家長篇小說代表作,但我覺著更像隨筆,邏輯性很強的隨筆。它不像傳統的小說,有兩三個主人公,整個故事情節都是圍繞主人公開展。它也不像外國小說,結尾講究饒有餘味。一般說來,小說要表達的主題思想需要讀者去猜去歸納總結,而韓少功的《馬橋詞典》似乎不需要讀者這般費心,如果說它真的讓我們費心了,也只是讓我們開闊得更遠。正因為它用不著我去猜,隨意翻書都可以不顧前因後果地讀下去,所以我覺得它像隨筆。後來查閱了資料才知道這叫辭典體小說,很新鮮的小說。文本結構這樣的小說,我還真是第一次遇到。
跳過說明,映入眼帘的就是主要人物表。接著是目錄,每一個題目的後面還附帶著實心或者空心的三角。目錄完了還有一張詞條首字筆畫索引。多新鮮的書,一打開我就看得不明不白,後來是明明白白。讀過《馬橋詞典》的人一定繞不開它的語言,不得不提到韓少功的語言功夫。通俗絕對是韓少功的一大特色,這可能與他的寫作定位有關。他能用簡單的詞語,生猛的寫法,活靈活現地在讀者面前展露人物的形象。例如多年後他重訪馬橋再遇神仙府的馬鳴時,寫到“他臉上每一道皺褶里都有肥沃的污泥,卻居然一點也沒見老,紅光滿面,聲氣硬朗,還像以前那樣,身上套著一件油污污的棉襖,兩隻手籠進袖子”。馬鳴帶著肥沃的污泥的臉一下子在我的腦海里再次出現。他的文章里沒有華麗的詞語,也沒有太過優美的句子,卻俗而不庸,通俗中帶著理性,閃爍著智慧。
他在篇目《肯》里寫到“我既希望自己強大,也希望自己一次又一次回到弱小的童年,回到樹根的夢和森林的陰謀”。這句話俗嗎?很通俗,我們每個人都能讀懂,甚至還能寫,更重要的是韓少功喚起了社會普通人物的矛盾心裡,讓人們思考無限。俗而不庸,是韓少功“尋根”文學的底色。他就是想通過這種通俗的語言,啟發或曰引導我們普通大眾去思考生活背後的東西,讓我們不至於在這個發展飛速物慾橫流的社會裡迷失自己。篇目《肯》里,他通過小時候的無知而發出的奇想與強大後用物理化學知識解釋同一個問題作比較后發出一系列的疑問引導我們思考。“強者的思想就是正確的思想么?列強帝國比殖民地強大,帝國的思想是否就正確?如果在外星空間存在著一個比人類高級得多也強大得多的生類,它們的思想是否就應該用來消滅和替代人類的思想”?這就是我讀完《馬橋詞典》后感觸最深的三點:新穎的小說結構、通俗的語言、“尋根”的思想。
後記
人是有語言能力的生物,但人說話其實很難。
一九八八年我移居中國的南方之南,最南端的海南島。我不會說海南后,而且覺得這種話很難學。有一天,我與朋友到菜市場買菜,見到不知名的魚,便向本地的賣主打聽。他說這是魚。我說我知道是魚,請問是什麼魚?他瞪大眼睛說,“海魚么。”我笑了,我說我知道是海魚,請問是“什、么、海、魚?”對方的眼睛瞪得更大了,顯得有些不耐煩。“大魚么?”
我和朋友事後想起這一段對話,忍不住大笑。
海南人有全國最大的海域,有數不盡數的漁村,歷史悠久的漁業。我後來才知道,他們關於魚的辭彙量應該說是最大的。真正的漁民,對幾百種自以及魚的每個部位以及魚的冬種狀態,都有特定的語詞,都有細緻、準確的表達和描述、足可以編出一本厚厚的詞典。但這些絕大部分無法進人普通話。即使是收集詞條最多的《康熙字典》,四萬多漢字也離這個海島太遙遠,把這裡大量深切而豐富的感受排除在視野之外,排除在學士們御制的筆硯之外。當我同這裡的人說起普通話時,當我迫使他們使用他們不太熟悉的語言時,他們就只可能用“海魚”或“大魚”來含糊。
我差一點嘲笑他們,差一點以為他們可憐地語言貧乏。我當然錯了。對於我來說,他們並不是我見到的他們,並不是我在談論的他們,他們嘲瞅嘔啞鞏哩哇啦,很大程度上還隱匿在我無法進人的語言屏障之後,深藏在中文普通話無法照亮的暗夜裡。他們接受了這種暗夜。
這使我想起了自己的家鄉。我多年來一直學習普通話。我明白這是必要的,是我被鄰居、同事、售貨員、警察、官員接受的必需,是我與電視、報紙溝通的必需,是我進人現代的必需。我在菜市場買魚的經歷,只是使我突然震驚:我已經普通話化了。這同時意味著,我記憶中的故鄉也普通話化了,正在一天天被異生的語言濾洗——它在這種濾洗之下,正在變成簡單的“大魚”和“海魚”,簡略而粗糙,正在譯語的沙漠里一點點乾枯。
這並不是說故鄉不可談論。不,它還可以用普通話談論,也可以用越語、粵語、閩語、藏語、維語以及各種外國語來談論,但是用京胡拉出來的《命運交響曲》還是《命運交響曲》嗎?一隻已經離開了士地的蘋果,一隻已經被蒸熟了腌制了的蘋果,還算不算一隻蘋果?
方言當然不是唯一的語言障礙,地域性也不是語言的唯一屬性。在地域性之外,語言起碼還有時代性的維度。幾天前,我與朋友交談,感慨交通和通訊手段的發達,使人類越來越強化了橫的聯繫,越來越加速了文化更新的進程,在不久的將來。可能基本上剷除和融化文化的地域差別,倒是可能擴大和加劇時代差別。地球村的同代人吃著同樣的食品,穿著同樣的衣服,住著同樣的房子,流行著同樣的觀念,甚至說著同樣的語言,但到那個時候,五十年代的人了解三十年代的人,二0二0年出生的人了解二O0O年出生的人,有可能就像現在湖南人要了解海南文化,中國人要了解英國文化一樣困難。
事實上,這個過程已經開始。在同一種方言內,所謂“代溝”不僅表現在音樂、文學、服裝、從業、政治等等方面的觀念上,也開始表現在語言上——要一個老子完全聽懂兒子的詞語,常常得出一把老力,已成為我們周圍常見的事實。“三結合”、“豆豉票”、“老插”、“成分”……一批辭彙迅速變成類似古語的東西,並沒有沉澱於古籍,沒有退出日常生活,仍然在某些特定的交際圈子裡流通,就像方言在老鄉圈子裡流通一樣。不是地域而是時代,不是空間而是時間,還在造就出各種新的語言群落。
這個問題還可以再往深里說。即使人們超越了地域和時代的障礙,是否就可以找到一種共同的語言呢?有一個語言教授做過一次試驗,在課堂上說出一個詞,比方“革命”,讓學生們說出各自聽到這個詞時腦子裡一閃而過的形象。答案竟然是多種多樣的;有紅旗,有領袖,有風暴,有父親,有酒宴,有監獄,有政治課老師,有報紙,有菜市場,有手風琴……學生們用完全不同的個人生命體驗,對“革命”這個詞作出了完全不同的下意識栓釋。當然,他們一旦進人公共的交流,就不得不服從權威的規範,比方服從一本大詞典。這是個人對社會的妥協,是生命感受對文化傳統的妥協。但是誰能肯定,那些在妥協中悄悄遺漏了的一閃而過的形象,不會在意識的暗層里積累成可以隨時爆發的語言篡改事件呢?誰能肯定,人們在尋找和運用一種廣義普通話的時候,在克服各種語言障礙以求心靈溝通的時候,新的歧音、歧形、歧義、歧規現象不正在層出不窮呢?一個非普通化或者逆普通化的過程不正在人們內心中同時推進呢?
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所謂“共同的語言”,永遠是人類一個遙遠的目標。如果我們不希望交流成為一種互相抵銷,互相磨滅,我們就必須對交流保持警覺和抗拒,在妥協中守護自己某種頑強的表達——這正是一種良性交流的前提。這就意味著,人們在說話的時候,如果可能的話,每個人都需要一本自己特有的詞典。
詞是有生命的東西。它們密密繁殖,頻頻蛻變,聚散無常,沉浮不定,有遷移和婚合,有疾病和遺傳,有性格和情感,有興旺有衰竭還有死亡。它們在特定的事實情境里度過或長或短的生命,一段時間以來,我的筆記本里就捕捉和囚禁了這樣一些詞。我反覆端詳揣度,審訊和調查,力圖像一個偵探,發現隱藏在這些詞後面的故事,於是就有了這一本書。
這當然只是我個人的一部詞典,對於他人來說,不具有任何規範的意義。這只是語言學教授試驗課里各種各樣的答案中的一種,人們一旦下課就可以把它忘記。
羅傑·蓋茨曼(Roger Gathman)(德克薩斯州的一名作家)在該書出版時給《舊金山之窗》撰文評論說:如果不熟悉中國文學的讀者單看前15頁就可能看不下去,韓少功在作品開始時給人一種該書是部專題論著的印象。然而,故事不久就開始了,其中裡面有四個人的故事是不朽的:一個是住在將要坍塌的屋子裡靠蚯蚓和草維持生命的瘋子的故事,另一個是鄉村優秀歌手被認為是淫蕩者實際上是一個閹人的故事,還有一個是這個地方的丐幫幫主的故事,最後一個是這個地方最為著名的強盜的故事。每個故事中都浸透著韓少功特有的沉思風格。
彼得·戈登(Peter Gordon)在《亞洲書評》中寫道:作品缺乏明顯的情節,不過他採用的依然是敘述的方式。作者對作品的處理方式是迷人的和非常有技巧的。作品處展示出敘述者對哲學、社會學、歷史學的沉思,這些沉思並沒有打斷其中的敘述。作者描述了馬橋這個地方傳統文化與現代思想共存,馬克思主義與鄉下人信仰的衝突,書中栩栩如生的場景幾乎讓你可以觸摸得到。
戈登認為讀這樣的書如同觀賞牆上的壁畫,儘管每篇是獨立存在的,你只有看到相當多內容的時候,才能搞清楚這部書寫的是什麼。《馬橋詞典》在語言上非常有趣,它探索了語言影響文化和思想的方法。事實上,《馬橋詞典》不僅可以用來作為研究民族語言學的材料,它也可以用來作為研究人類學方面的材料。它的價值遠遠超出了小說的意義。戈登說:當然,我希望他描述的東西是真實和精確的。
本·海倫瑞齊(Ben Ehrenreich)在紐約的《鄉村之聲》中寫道:韓少功大膽創新的小說採用解構的方式來演義中國鄉村的歷史。中國近半個世紀以來的鄉村歷史,被作者熟練地來來回回地反覆刻畫,手法顯得遊刃有餘。作品描述的是世界的一個小角落,是中國南部的一個小村莊。這裡既有宗族間的械鬥,又有男女混亂的性愛關係,還有徘徊很久不願離去的幽靈。這本書如同書名所暗示的,材料以字典的形式組織起來。讀者既可以從詞條中看到當地歷史的變遷,也可以看到馬橋人身上的傳統烙印。有的條目是一些長段落,有的甚至長達幾頁,作者就此將有關鄉村及它居民的傳說、逸事編織在裡面。有的條目是一些簡短語言學方面的思索。馬橋人的語言只有在馬橋這個地方才會有特殊的含義。馬橋人的語言反映出他們獨特的思維方式與生活方式。當時的政治氛圍是:說話不小心就有可能被關進監獄。作者在作品中說:語言只是語言,不是其他什麼東西,它的重要性不應該被誇大。毫無疑問,這本書是一部傑作。
錢希騰(QIAN XI TENG)(《哥倫比亞觀察家》的專欄作家)在《哥倫比亞觀察家》上撰文說:當朱莉婭·洛弗爾給韓少功寫信想要翻譯《馬橋詞典》時,韓少功同意了並補充說:我擔心翻譯可能會很困難的。因為《馬橋詞典》本身就是中國南方鄉村馬橋這個地方雜的方言詞語的彙編。
這個地方曾是韓少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下鄉接受再教育的地方。遠離家鄉,在偏遠貧窮的地方同農民一起勞動,韓少功努力適應當地的習慣和當地的方言。中國的語言,儘管漢字相同,但不同的地方,語法、發音甚至意義都大不一樣。在《馬橋詞典》中,作者以敘述的方式來解釋他的條目,從村民到這個地方的特殊環境再到這個地方獨有的習慣,作者既注重當地語言的形成又注重語言所反映出的馬橋人的價值觀。貫穿作品始終的,是作者對當地方言在官方語言影響下所發生變遷的分析。韓少功用詞條羅列的方式,串聯著歷史事件,活靈活現地描繪出了馬橋這個鄉村世界的風土人情。在傳統意義上,它很難算得上一部小說,因為裡面沒有鮮明的以一貫之的中心人物,沒有起承轉合的故事。作者在創作中,追求文體置換,不拘泥於傳統,作品拋棄了固有的小說模式,給人的感覺多是片段性的,既像小說又像詞典,然而這本書卻充盈著豐富的時代精神和深刻的批判內涵。
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的評論家斯朱威拉(sjwillard)評論說:對美國或英國小說感到厭倦了的讀者應該讀一讀中國的這本小說。它無疑是一部傑作,韓少功在作品中娓娓道來的方式給人的印象是深刻的。作品的內容並沒有局限於“文化大革命”這段時間,講述者也描述了毛澤東時代之後馬橋所發生的巨大變革。講述者解釋說他原先打算給馬橋的每樣東西都寫一下傳記。他是無法做到那一點的,但是他在作品中還是極力保持著給每樣東西作傳的興趣。
斯朱威拉認為,這部作品由於沒有清晰的年表,導致作者在時間上前後來回跳躍,這樣容易讓讀者搞混,同時,韓少功沒有把講述者、作者、詞典編撰者明確區分開來,這也是讓人有疑問的。然而,它仍不失為一部非常有趣而又偉大的書。
俄克拉荷馬大學美中關係研究所所長葛小偉表示:“韓少功獲得第二屆紐曼華語文學獎是件非常激動人心的事。來自美國、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的五名專家組成的評選小組最終選擇了韓少功和他的《馬橋詞典》,是因為這本書是創新的。因此,它符合紐曼華語文學獎的目標:最好地詮釋人類生存條件的傑出的散文或詩歌。”《馬橋詞典》2003劍橋英文版譯者Julia
Lovell評論道:“韓少功是一個交織了卓越的藝術性和獨創性、本地與全球的人性觀點的中國作家。他的職業生涯體現了自1976年以來在他寫作的地方發生的創造性的革命。混合了小說、回憶錄,以及散文,《馬橋詞典》是一本不平凡的書:它結合了幽默和人性化的故事敘述,它不動感情地敘述了貧困農民的生活,它用輕巧的技能講述現代中國的悲劇,它的實驗形式,以及作者對中華文化、語言和整個社會的複雜見解。”
《馬橋詞典》是先鋒小說的代表作品之一。曾榮獲“上海市第四屆中、長篇小說優秀大獎”中的長篇小說一等獎。
2010年10月,作家韓少功長篇小說《馬橋詞典》獲得美國第二屆紐曼華語文學獎。

韓少功
曾獲境內外獎項:1980年、1981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2002年法國文化部頒發的“法蘭西文藝騎士獎章”;2007年第五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之“傑出作家獎”;第四屆魯迅文學獎;美國第二屆紐曼華語文學獎等。作品分別以十多種外國文字共三十多種在境外出版。另有譯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昆德拉著)、《惶然錄》(佩索阿著)等數種出版。
曾任第一屆、二屆海南省政協常委(兼),第三屆省人大代表,第三屆海南省文聯主席、省文聯作協黨組成員、書記。2011年卸任以上職務。現兼職中國作協主席團委員、全委會委員,海南省文聯名譽主席,湖南師範大學“瀟湘學者“講座教授。
2019年9月23日,韓少功長篇小說《馬橋詞典》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