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亞特里·斯皮瓦克
佳亞特里·斯皮瓦克
佳亞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1942- ),出生於印度。是當今世界首屈一指的文學理論家和文化批評家,西方后殖民理論思潮的主要代表,早年師承美國解構批評大師保羅·德曼,獲得康奈爾大學博士學位,在20世紀70年代曾以將解構大師德里達的De la grammatologie引入英語世界而蜚聲北美理論界,后又以演講的雄辯和批評文風的犀利而馳騁於80、90年的英語文化理論界。斯皮瓦克現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阿維龍基金會人文學科講座教授,比較文學與社會中心主任。由於斯皮瓦克對當代人文社會科學做出的突出貢獻和巨大影響,清華大學聘請她為外語系客座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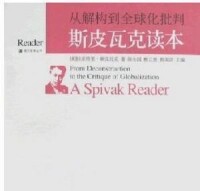
佳亞特里·斯皮瓦克
斯皮瓦克書中各章都針對一個不同的學科,但是各章所體現的研究方法卻大致如一:在每一章所體現的論斷都集中在對具體文本的細讀上,並且她還不斷提醒讀者她自身所處的境域,以及她能得出這些結論的偶發性因素。的確,斯皮瓦克的修辭風格也是一條貫穿全書的中心線索,她始終在和她先前的意見進行對話;同時也是在和她自己在寫作此書時那些最終被賦予了表述形式的種種想法進行對話。這種對話形式貫穿文本,在許多情況下也決定了註腳與文本之間的關係。
與當代其他幾乎所有的理論家不同,斯皮瓦克將她的的作品引向了對教育方法的思考(她思考如何使學生們受到啟發,並超越那些固有的思維限制進行思考,這些限制是由於他們的教育環境推崇邏輯推導而產生的),這一思路體現在其文本的構架之中——這不是一種目的論的、而是散亂但卻詳盡深邃的文本。在本書名為的簡短附言中,得出了她的結論。這一附言追溯並解釋了從1965年到90年代期,德里達在其作品中對解構這一術語的使用。這是一本恰切的摘要,但卻不能當作是對德里達的介紹,因為它假定讀者對其所評論的文本相當熟悉。
1、德里達譯者前言(1976)
2、(1985)
3、《底層研究:解構歷史編撰學》 (1985)
4、 (1987)
5、《后結構主義、邊緣性、后殖民性和價值》 (1990)
6、 (1992)
7、 (1994)
8、 (1996)
9、 (1999)
10、 (1999)
11、 (2002)
12、《底層人能說話嗎?——2006年清華大學講演》 (2006)

佳亞特里·斯皮瓦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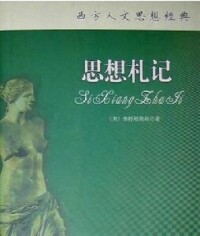
佳亞特里·斯皮瓦克
這種直言不諱的自白倒是真實地描述了她本人不斷變化的學術興趣和理論專長,而她也確實因此而頗受第三世界學者的批評和攻擊。此外,從她本人對第三世界學者的高傲態度來看,很難認可她作為一位第三世界批評家或后殖民地知識分子的文化身份。她所進行的反后殖民嘗試實際上是為了吸引西方主流學術界的注意,以便實現其從邊緣步入中心最後消解中心的“反俄狄浦斯式”的事業。一但她完成了這一過程,她便暴露出其本來的有著第三世界背景和血統的文化精英的真實身份。也許這正是以斯皮瓦克為代表的不少后殖民理論家的獨特意義和價值:一方面他們有著東方血統和文化背景,另一方面卻又有著更為厚實的西方教育和理論素養。既然他們在西方世界接受了多年的教育,那麼他們的西方文化基礎也就大大超過了本民族的文化素養和理論基礎。他們在西方卻總是因其固有的東方民族血統而以“他者”的身份出現;而當他們來到東方時,卻又無法擺脫他們所深深置身其中的西方文化的影響。因此他們在東方也就自然而然地被當作了“他者”來看待。也許這正是大多數后殖民批評家所不得不面臨的兩難。
這些后殖民理論家有著如此複雜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在理論方向上又有著如此相似和差異交織一體的特徵,那麼對他們的研究和批判性分析就決不能採取簡單化的態度。應該看到他們所面臨的一種無法迴避的兩難:一方面,他們總是通過不斷地從自己的獨特的(東方或第三世界)角度批判西方文化和理論達到推進自己學術研究之目的,但是另一方面,既然他們生活在西方世界,使用著西方的語言(英語),那麼他們便無法擺脫西方話語的陰影和西方文化的影響,而且他們所使用的英語也與真正的東方和第三世界知識分子所使用的帶有當地土音的“英語”有著一定的差別。
由於他們在文化身份上的特殊性,他們與非西方學術界也無法在同一理論層面上進行真正平等的交流和對話。因此對於廣大第三世界知識分子來說,他們實際上也扮演了雙重角色:西方殖民主義的批評者和之於東方的一種新殖民主義的鼓吹者。他們對西方文化的批判只不過是一種解構的策略而已,而一種新的殖民話語就在這一過程中逐步地被建構了出來。他們的非殖民化嘗試“往往發生在邊緣地帶,但也發生在中心乃至核心地帶”,或者說更多地是在第一世界而非第三世界。但畢竟,后殖民主義已經進入了中國文化和文學批評的語境中,並且對我們的文化策略和寫作話語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當代西方重要學者佳亞特里··斯皮瓦克教授的文學思想,在生活形態和文學樣式發生巨大變化之時。人們開始重新追問原有的文學觀念並在此基礎上提出新的理論主張。通過對其主要論著的解讀,簡要地論述了斯皮瓦克在這一領域展開的考察。斯皮瓦克並不能簡單歸於后殖民理論家,而是人文思想家。.她通過文化表象的剖析深入到文化政治的背景分析中,致力於清理原有的文學觀念。以解構主義方式審視真理及知識的構成,關注主流話語、體制和第三世界的問題。在此基礎上將女性主義和邊緣群體置於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和后結構主義的互證關係中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批判。這些方式對業已形成的理解和分析模式形成了衝擊,對文學理論外在的走向和內在的思路提供了清理的入口和言說的平台。其研究範式和文學思想對於人們在全球化時期認識文化政治和多元文化批評有著深刻的啟迪。在當前中國學界清理文學遺產和消化吸收異域成果時,其觀點和方法論作為一種資源值得人們認真思考和借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