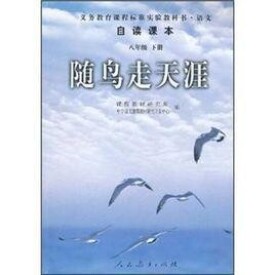隨鳥走天涯
隨鳥走天涯
劉克襄以“鳥人”“漂鳥詩人”聞名於台灣文壇。他數十年如一日地遍游台灣的山山水水,從事鳥類的觀察、攝影和報道。《隨鳥走天涯》記述了作者在關渡沼澤地觀察、拍攝水鳥的情形,最初作者只是以觀賞的態度看待鳥,後來在辛普遜船長的影響下,開始有意識地關注水鳥被捕殺、沼澤受到污染、鳥兒失去家園的狀況,並主動去解救水鳥,表達了作者對自然遭到破壞的深深憂慮。
【作品名稱】隨鳥走天涯
【作品年代】現代
【作者姓名】劉克襄
【文學體裁】散文
辛普遜船長和我的認識十分偶然。前年我仍在海軍服役時,有一次戰艦換防到基隆,趁假日時,我在港口附近的街道溜達。結果遇到他,手裡也拿著一副雙筒望遠鏡,我們相互知道對方都在注視上空的老鷹,因了這層關係,彼此間的心靈似乎有種默契,於是我們認識了,變成熱絡的朋友。待在基隆的一段時間裡,我們不是坐在咖啡館大談鳥事,就是相偕到附近的山上觀鳥。一直到我隨戰艦回到離島,他也跟著船繼續飄泊的日子。
辛普遜船長是美國人,行船生涯已有二十年,他為何會在大海中選擇賞鳥的嗜好?同樣的行船的人,不分國籍,航海時寂寞孤單的心情,我是能了解的。他也告訴我,如果不是有隨處旅行賞鳥的嗜好,他不可能將這一生耗在海上。然而賞鳥仍是寂寞的,要不,他在基隆港時,就不會與我認識,急於交換賞鳥的經驗。
雖然我也在海上開始賞鳥的興趣,不久卻下船退役了。幸好興趣並未減低,繼續跟著輾轉的職業生活,走到哪裡,跟到哪裡。
辛普遜船長來的正是時候,因為他已經有十餘年的賞鳥經驗。
我們一進入關渡沼澤區,我就直接帶他走到水鳥群集的淺灘。這些水鳥剛剛從北方南下,我想辛普遜船長必然在日本見過,也急於看到它們。
果然,他高興地叫嚷,一一念出每一種水鳥的名字,他說上個月在瀨戶內海時,也遇到過它們。我又想,這大概也算是他鄉遇故知了,只是他遇見的是鳥朋友。
可是他快樂的表情一下子卻變得怏怏不悅。原來他看到水鳥聚集的淺灘,架立著好幾對竹竿。他問我那是什麼,我知道那是鳥網。
本來我腦筋一轉,覺得這事與他無關,想打馬虎眼過去,又想他也不會那麼笨,就據實說了。
沒有想到真的那麼笨,連鳥網都沒見過。他生氣地說:“我從來沒有在別的國家發現這個東西,難道你們連管的人都沒有?”
望著他,我真是無言以對,也不曉得應該如何解釋。
後來他又抱怨了這個沼澤區的缺點,什麼噪音、污染、廢土等,通通指了出來,好像都是我的錯。
我心裡想,你又不是生活在這裡的,憑什麼指責。心頭是這麼生氣,我還是婉轉地回答,告訴他因為這些問題,我們已有一個生態保護區的構想。這裡便可能成為台灣第一個水鳥保護區。
辛普遜船長卻反問我:
“為什麼以前沒有呢?”
對這個問題,我實在難以解釋,而且有理也講不清的,只好說:
“在我們這裡,有許多事情可能比建立保護區還迫切。”
當然,這種說法,辛普遜船長也不同意,他直覺地認為建立保護區比什麼都重要,管他什麼天下大事,二三十年前就該設立了。
也許他是對的。總之我慶幸他不是中國人。
辛普遜船長離開台灣以後,我繼續在關渡沼澤區旅行。往昔我對鳥網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也不知是否受到他的影響,旅行的次數增多以後,看到水鳥陷入鳥網,我已變得無法忍受。
我再也不管那些鳥網設在多深多髒的沼澤,一定涉水下去搶救。原來水鳥們南來北往,依靠的就是堅強的羽翼。而它們一陷進鳥網,就拚命掙扎,羽翼陷入鳥網的糾纏,羽毛紛紛脫落,身體變得扭曲痛苦,毫無反抗的能力。我每次釋放一隻,都需要花費五六分鐘的時間,一一將它們的羽翼從混雜的鳥網中擺脫。它們被我抓住時,也不知道我的企圖,經常嚇得拉屎。有些水鳥從網中獲釋以後,也不見得能再飛行,不是羽翼受傷,便是腿扭斷了。幸好還能生存,總比架在烤鳥攤好多了。從拯救水鳥中,我也漸漸體會辛普遜生氣的原因,這種生氣應該是出於沉痛的心情。
從旅行的經驗里,我也發覺捉鳥的人有時比賞鳥的人懂得鳥性,以前在中央山脈時,我曾經看到捉鳥人的獵捕方法。他們懂得利用放鞭炮、敲銅鑼驚嚇山鳥,將山鳥趕到溪谷空曠的地區。他們就在該處架起鳥網,讓山鳥盲目地飛撞,陷進去。不過兩三個鐘點,整座山的鳥都捉空了。
他們在沼澤區卻改變方式。因為海水漲潮時,水鳥會從淡水河飛進,落腳沼澤區。於是他們在每處可能棲息的地方擺設鳥網,連途中飛行的路徑也架立,整得水鳥飛進來無處可去。剛開始時,水鳥紛紛落網,時日一久,它們便轉往他處。於是10月以後,沼澤區的水鳥漸漸減少。
那時,為了維護這些水鳥的生存,我也跑到派出所控告。結果警察先生告訴我,關渡隸屬於北投管轄,北投那麼大,風化場所的事一大堆都管不完了,誰顧得了什麼水鳥。說的也是。後來我才知道他們只有一個人管轄關渡,他也不可能整天待在沼澤區,等捉鳥的人。何況關渡不只是沼澤區,與沼澤區相鄰的關渡宮,香火鼎盛,每天有上千的遊客出入,上廟還願。捉水鳥的問題,警察先生自然認為不重要。
控告不成,鋌而走險,我只好回到沼澤區,自己行動了。我只要發現鳥網,察看四下無人,隨即偷偷取出小刀,從中割掉。結果成績斐然,整個沼澤區三十幾具鳥網,我去掉了三分之一。
夜路走多了,終於碰到鬼。有一次我正在割網,被人發現了,從遠遠的水田又吼又叫,一路追過來。我做賊心虛,嚇得拔腿就跑,騎上摩托車匆匆跑回台北。然而我仍不死心,第二天,又跑到關渡去,沒想到他們已經派人看守。不過,我不相信他能夠每天來此,我卻能隨時出現。他們後來可能也猜到是我乾的,心裡雖悶不吭聲,我一抵達沼澤區,也小心地監視我的行動。
結果我們都沒有得逞,因為天氣越來越冷,水鳥多半過境,而且鳥網也時常被厲風吹垮,他們只好放棄捕鳥。我不曉得他們去哪裡了。我的旅行次數卻與日俱增,而且轉而專心拍照鳥類。
鳥性怕人。拍鳥也跟釣魚一樣,只有一個方法:等。我剛開始拍鳥時,挫折感非常大,還未接近,它們已經飛離。經過幾次接觸后,我就學乖了,懂得去選隱蔽的樹林、草叢躲起來,等候鳥出現。這種守株待兔的方式,後來也覺得不智。我經常枯坐一個上午,未看到鳥從我四周經過,可是開始決定這個位置時,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考慮到這裡經常有鳥出現,我想那些鳥一定知道我躲在裡頭,於是我放棄了。
我改采主動的方式,看到鳥時,從離它十來米外的地方爬行接近,這種方式也只持續了一段時日。後來有幾次,我在沼澤區拍水鳥時,不惜趴在爛泥巴上匍匐,結果每次花了半個多時辰,停停爬爬,好不容易接近到四五米,舉起相機時,它們卻拍翅驚飛,氣得我站在淺灘發愣。弄得滿身爛泥巴的代價是如此,我只好也放棄了。
幸好我又想到另一個方法,我在附近找到一堵竹籬笆,在籬笆上插上樹枝,將自己裝扮成野戰特遣隊的士兵,整日躲在籬笆後面。哪裡有鳥就推著籬笆前進。
有一天,我就這樣裝扮前往淡水河口,攜著相機在沙灘行動,未料到,神不知鬼不覺,後面尾隨著一位海防士兵。我對準鳥準備按快門時,他也舉著槍瞄準著我。
他在我背後大喊:“不準動!”
我聽到背後有聲音,嚇了一跳,急忙站起來,一看前面的鳥也被嚇跑了,氣得直跺腳。
我回頭一看,發現他大概是看見我的裝備十分特殊,以為逮到什麼人物,端著步槍一步一趨地逼向我。這時,我才感覺事態不對,急忙改作笑臉狀。
“你在做什麼?”他仍然緊繃著臉問我,步槍繼續對著我的胸膛。
我也慌張地舉起手,跟他解釋:“我在照鳥啊!”
“照鳥?鳥在哪裡?”他睜大眼瞄四周,一無所有,儘是沙灘。
“跑了。”我口上這麼說,心裡卻想:“你這個獃子,鳥都被你嚇跑了,你怎麼看得到?”
這位士兵實在盡責,看到我的打扮,又在地上鬼鬼祟祟,他自然不相信我的說詞,槍押著,就將我帶回營部。幸好我帶了鳥會證件,底片也還未使用,費了一番口舌,他們才放我一馬。
這次教訓以後,我再到海邊或者回內陸拍鳥時變得異常小心。我也不是顧忌上述的事情,而是怕被人吵到,失去攝取一個寶貴鏡頭的機會。因為過路人看我的打扮,又躲在草叢摸索,總會好奇地停下腳步,有時也會走到我的身邊,鳥就會被嚇飛了。
由於長期在沼澤區拍攝水鳥,我對於當地的環境自然熟稔,也非常關心它的變化。
春天時,我看到每天都有卡車載滿廢土駛進來,然後將廢土傾倒入沼澤。我感覺他們每倒一次廢土,都像拿一把刀在刺我。沼澤區的面積不過十幾塊水田大小的總和。卡車每天填塞,不到一年,遲早會將沼澤鋪滿。沼澤一失,哪來的水鳥?更遑論將來有什麼生態保育區的計劃。
冬末時,卡車載運進來的廢土已將沼澤一分為二,而且在廢土上築起違建的豬舍。如今再運入,據當地人說,也是要建立更龐大的豬宅。違建怎可擴張工程?何況是即將成立的生態保育區?執法的人呢?我只有一個人又如何去阻止?
我想等水鳥生態保育區的計劃擬定,準備實施時,沼澤區一定已經消失了。難怪連外國人辛普遜船長也替我們難過、急躁。我後來想起他臨行離去時留下的話:“反正你們這塊地已無可救藥,還不如跟我出去,咱們到處看鳥去。
話是這樣說也沒錯,何況我也是行船的人,心裡難免動搖。只是對這裡的鳥,心裡有一份說不出的感情,牽掛的也多了點。我還是不敢太早遠行,真的,再也不敢奢言說要到哪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