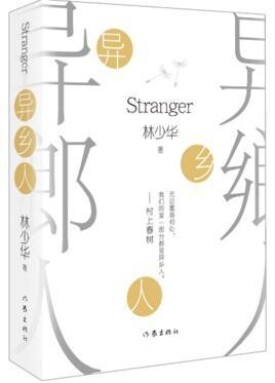共找到22條詞條名為異鄉人的結果 展開
異鄉人
林少華散文集
“無論置身何處,我們的某一部分都是異鄉人(strangers)”。本書是著名文學翻譯家、學者林少華先生的散文集,是他近年對當下社會生活的思考和感悟。誰又不是異鄉人呢?也許你身在異鄉,漂泊無依;也許你感到孤獨,即便置身人群之中,心靈的異鄉人無處不在。林少華老師的文字抒情意味濃厚,充滿智慧與禪意,無處不在暗示著我們——你,要如何才能獲得身心安頓?
幸福,其實並不遙遠。
林少華,著名文學翻譯家,學者,中國海洋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兼任中國日本文學研究會副會長、青島市作家協會副主席。著有《落花之美》《為了靈魂的自由》《鄉愁與良知》《高牆與雞蛋》《夜雨燈》《林少華看村上:村上文學35年》。譯有《挪威的森林》《海邊的卡夫卡》《奇鳥行狀錄》等村上春樹系列作品,以及《心》《羅生門》《雪國》《金閣寺》《在世界中心呼喚愛》等日本名家作品凡七十餘部,廣為流布,影響深遠。
看書的時候,一會兒哭,一會兒笑
也許流淚也許嘆息也許頓悟但你無法無動於衷。
你從哪裡出發?又要到哪裡去?
身心安頓處,即是故鄉。
ChapterI大地上的異鄉人
01 那片有螢火蟲的山坡/002
02 地球上最倒霉的蒲公英/007
03 故鄉中的“異鄉人”/011
04 買車還是買葡萄架/015
05 山樑的那邊/019
06 開往火燒雲的火車/023
07 被廢棄的鐵路/027
08 牽牛花和城鎮化/031
09 我愛鄉下/035
10 那個格外冷的冬天/039
11 想必鞋也哭了/043
12 消失的老屋/047
13 青春:修辭與異性之間/052
14 我和副廳級/057
15 鄉下人:鋤頭與麻將/061
16 背叛家風得來的《千家詩》/065
17 爺爺的“林沖”和奶奶的燒土豆/069
18 三十九年前的童話/073
ChapterⅡ莫言的幽默與村上的幽默
01 莫言的第一步,村上的第一步/078
02 莫言的幽默與村上的幽默/083
03 莫言與村上在台灣/088
04 高密東北鄉與諾貝爾文學獎/093
05 村上為什麼沒獲諾貝爾文學獎/097
06 諾獎視野中的村上春樹:“挖洞”與“撞牆”/101
07 就諾貝爾文學獎寫給村上春樹/110
08 莫言爺爺講的故事和我爺爺講的故事/116
09 我和村上:認同與影響之間/120
10 莫言獲諾獎:翻譯和翻譯以外/124
11 村上春樹:“我不認識漢字”/130
12 村上筆下的人生最後24小時/134
13 村上譯者的無奈/138
ChapterⅢ舌尖上的大雁與槐花
01 文化,更是一種守護/144
02 旅遊:尋找失落的故鄉/148
03 落葉的文學性/152
04 慢美學或美學意義上的慢/156
05 水仙花為什麼六瓣/160
06 書房夜雨思鐵生/164
07 生命消失的悲傷/168
08 文學與文學女孩的來訪/172
09 《小小十年》和小小少年/176
10 當農人不再熱愛土地/180
11 舌尖上的大雁與槐花/184
12 三江源,“我愛她們”/188
13 美的前提是乾淨……/192
14 貴賓廳里的“遭遇”/196
15 我的“開門弟子”/200
16 血壓與《逍遙遊》/204
17 昏睡的“土豪金”/209
18 中年心境的終結/213
19 “土豪”與“大丈夫”/217
20 “大丈夫”是精神性別/221
ChapterⅣ“副教授兼系主任”
01 美好的開學第一天/226
02 三十一年,我如何當老師/230
03 一個半小時的“二級教授”/235
04 我能當博導嗎/240
05 大師之大 大在哪裡/244
06 清華教授何以絕食/249
07 苟且:這個可怕的社會病症/253
08 “副教授兼系主任”/258
09 普林斯頓大學和賣報的劉隊長/262
10 大學人士與啤酒/267
11 教授為什麼寫不出教授/271
12 電腦上課和“蒙娜麗莎”/275
13 女博士:第三性?/279
14 西方人咬了“蘋果”,“蘋果”咬了我們/283
15 瓜田小屋和北外女生/288
16 高中:只為那一個三位數?/292
17 來自高考狀元的禮物/295
18 兩個上海,兩個我/299
19 演講:抗拒衰老/303
永遠的異鄉人
家鄉,故鄉。他鄉,異鄉,異鄉人。
家鄉、故鄉談得多了,這回說說異鄉、異鄉人。
我是在半山區長大的。無日不見山,無山不見我。自不待言,我見的山或見我的山,大多是山的這邊,山那邊平時是看不見的。於是我常想山那邊有什麼呢?尤其遠處一條沙石路從兩座山頭之間的低凹處爬過去的時候,或者一條田間小路蜿蜒伸向坡勢徐緩的山岡的時候,我往往產生一股衝動,很想很想順著那條路一直走去看看山那邊到底有什麼:杏花環繞的村落?垂柳依依的清溪?村姑嬉鬧的田野?抑或牛羊滿坡的牧場?這種山那邊情結促成了我對遠方最初的想象和希冀,悄然喚醒了我身上蟄伏的異鄉人因子,使我成為故鄉中一個潛在的異鄉人。
後來我果然奔走異鄉,成了實際上的異鄉人。迄今為止的人生歲月,有三分之二流逝在異鄉的街頭。那是毫不含糊的異鄉。不是從A鄉到B鄉、從甲縣到乙縣,而是差不多從中國最北端的白山黑水一下子跑到幾近中國最南端的天涯海角。你恐怕很難想見四十幾年前一個東北鄉間出身的年輕人初到廣州的驚異。舉目無親,話語不通。“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此乃地理上、地域上的異鄉人。
若干年後我去了日本。不瞞你說,較之當初的廣州,異國日本的違和感反倒沒那麼強烈。這是因為,粵語我全然聽不懂,日語則大體聽得懂。甚至五官長相,日本人也不像廣東人那樣讓我感到陌生。然而日本人終究是日本人。語言我固然聽得懂,書報讀得懂,但對於他們的心和語言背後的信息我基本沒辦法弄懂。五官長相固然讓我有親近感,但表情及其生成的氣氛則分明提醒我內外有別。何況,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日本的主流媒體就已傾向於數落中國的種種所謂不是了。對此我能怎麼樣呢?我能拍案而起或拂袖而去嗎?於是,當對方希望我作為專任大學教員留下來時,我婉言謝絕,決意回國。挪用古人張季鷹之語:“人生貴得適意耳,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此乃族別上、國別上的異鄉人。
返回故國的廣州,繼續在原來的大學任教。也許受日本教授的影響——日本教授上課遲到一二十分鐘屢見不鮮——和教授治校環境的潛移默化,回國上課第一天我就滿不在乎地提前五分鐘釋放學生跑去食堂。不巧給主管教學的系副主任逮個正著,聲稱要上報學校有關部門,以“教學事故”論處,我當即拍案而起,和他高聲爭執。加之此後發生的種種事情,我的心緒漸趨悲涼,最後離開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廣州,北上青島任教。青島所在的山東半島是我的祖籍所在地。儘管如此,我也似乎並未被身邊許多人所接受。就其程度而言,未必在廣州之下。這讓我不時想起自己譯的村上春樹隨筆集《終究悲哀的外國語》中的話:“無論置身何處,我們的某一部分都是異鄉人(stranger)”。換言之,在外國講外國語的我們當然是異鄉人,而在母國講母語的我們也未必不是異鄉人。當著老外講外國語終究感到悲哀,而當著同胞講母語也未必多麼歡欣鼓舞。在這個意義上,我可能又是個超越地域以至國別的體制上、精神上的異鄉人。
現在,我剛從文章開頭說的我的生身故鄉回來不久。也是因為年紀大了,近五六年來,年年回故鄉度暑假。那麼,回到故鄉我就是故鄉人了嗎?未必。舉個不一定多麼恰當的例子。某日早上,我悲哀地發現大弟用名叫“百草枯”的除草劑把院落一角紅磚上的青苔噴得焦黃一片,牆角的牽牛花被藥味兒熏得蔫頭耷腦。問之,他說青苔有什麼用,牽牛花有什麼用,吃不能吃,看不好看!悲哀之餘,為了讓他領悟青苔和牽牛花的美,為了讓他體味“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的詩境,我特意找書打開有關圖片,像講課那樣興奮地講了不止一個小時。不料過了一些時日,他來園子鏟草時,還是把籬笆上開得正艷的牽牛花利利索索連根剷除。我還能說什麼呢?這裡不是日本,不是廣州,不是青島,而是生我養我的故鄉……還是村上說得對——恕我重複——“無論置身何處,我們的某一部分都是異鄉人”,縱然置身於生身故鄉!換言之,不僅語言,就連“故鄉”這一現場也具有不確定性,或者莫如說我們本以為不言自明的所謂自明之理,其實未必自明。
但另一方面,這種故鄉與異鄉、故鄉人與異鄉人之間的重合與錯位,這種若明若暗的地帶,或許正是我們許多現代人出發的地方,也是我出發的地方。我從那裡出發,並將最終返回那裡。返回那裡對著可能再生的青苔和牽牛花回首異鄉往事,或感嘆故鄉弱小生命的美。
其實,我為這本小書取的名字就叫“牽牛花開”,並為之沾沾自喜。不料編輯宋迎秋女士看稿時敏銳地嗅出了牽牛花和非牽牛花背後的某種疏離性,並將疏離性視同異鄉人元素,建議改為“異鄉人”。妙!於是我趁機寫出上面這些或許多餘的話來。至於這本小書中是否真有一個“異鄉人”隱約出沒其間,那隻能由各位讀者朋友判斷了。但無論如何,作為書的作者,我都要由衷感謝您肯把這本小書拿在手裡。不但我,責編迎秋——我的故鄉人——想必也會感謝。
村上筆下的人生最後24小時
假如人生只剩24小時,假如你我將在24小時后從這個桃紅柳綠鶯歌燕舞的世界上消失,那麼你想做什麼呢?這裡說的當然不是卧病在床昏迷不醒的24小時,而是活蹦亂跳能做一切好事也能幹所有壞事狀態下的24小時——你打算如何度過這寶貝得不得了的24小時?
忽然冒出如此荒誕而又痛切的念頭,是因為最近為在上海出精裝本而重校村上春樹《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當中遇到了相關情境。那是具有某種暗示性和啟示性的情境,同時含有不無英雄末路意味的悲涼和孤獨感。容我概述如下以供參考。
主人公“我”是一位精通電腦技術的35歲男士。由於無比複雜的原因,他的人生只剩下24小時。跨度大約是10月2日3p.m.—10月3日3p.m.。季節自然是秋天。不知何故,一個即將走到生命盡頭之人卻對天氣十分關注,幾個比喻極見特色。例如,晴:“天空晴得如被尖刀深深剜開一般深邃而透徹”,晴得“竟如今晨剛剛生成一般”,晴得“彷彿是不容任何人懷疑的絕對觀念”。並且感嘆“作為結束人生的最後一天,場景似乎不錯”。
實際他最後24小時的人生場景也似乎不錯,至少盡情飽餐了一頓,做愛也做得相當盡興。同一個胖女孩從地下“冷酷仙境”逃到地面的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給打過交道的圖書館女孩打電話,約定當天傍晚6∶00一起吃義大利風味餐。女孩是“胃擴張”,他餓得“螺絲釘好像都能吃進去”,兩人旗鼓相當,頓時吃得天昏地暗。生牡蠣、意式牛肝醬、燉墨魚、奶油茄瓜、醋漬公魚、巴旦豆燜鱸魚、菠菜色拉,主食有意麵、通心粉、蘑菇飯和意式番茄炒飯。加之男侍應生“以御用接骨醫為皇太子校正脫臼的姿勢畢恭畢敬地拔下葡萄酒瓶軟木塞斟酒入杯”,結果所有吃喝一掃而光。之後又去女孩家受用冷凍比薩餅和帝王牌威士忌。吃罷淋浴上床,三次大動干戈。干罷一起裹著毛毯聽平·克勞斯貝的唱片,“心情暢快至極”。
翌日晴空萬里,他同女孩開車去公園——“星期一早上的公園猶如飛機全部起飛后的航空母艦甲板一般空曠而靜謐”——歪在草坪上喝冰涼冰涼的易拉罐啤酒,談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女孩走後,他繼續喝啤酒。當生存時間僅剩一小時多一點點的時候,他從錢夾里抽出兩張信用卡燒了——兩張現金支票昨天已經折成四折扔進煙灰缸——“我首先燒的是美國運通卡,繼而把維薩卡也燒了。信用卡怡然自得地在煙灰缸中化為灰燼。我很想把保羅·斯圖爾特牌領帶也付之一炬,但想了想作罷,一來過於惹人注目,二來實在多此一舉。”最後,他把車開到港口空無人影的倉庫旁,在鮑勃·迪倫唱的《驟雨》聲中進入沉沉的夢鄉……24小時至此結束。
放下書,我不由得返回本文開頭那個假定:假如自己的人生只剩24小時,自己會做什麼呢?能效法上面的主人公嗎?基本不大可能。作為人生壓軸戲誠然聲情並茂可圈可點,但問題首先是年齡不同。他35歲,我則至少要把這兩個數字顛倒過來。有哪個圖書館女孩——儘管我平生最愛圖書館——肯同一個半大老頭兒吃哪家子義大利風味餐呢?至於餐後去女孩住處共度良宵,更是痴心妄想。其次,身份不同。小說主人公是自由職業者,IC個體戶。我則有單位有組織有領導,而且是據說多少名聲在外的大學教授。倘在人生最後關頭弄出桃色新聞,來個晚節不保,一世英名從此休矣。這可使不得,萬萬使不得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現實不可能由心情說了算。那麼此外呢?扔存款折燒信用卡?這也絕無可能。人家是金牌王老五,一人吃飽全家不餓,身外之物留下也無用。我則是有老婆孩子之人。再說那東西也不在我身上,想燒也找不到。領帶?領帶倒是偶爾系在脖子上,可是把領帶付之一炬又有什麼可“酷”的呢?“一來過於惹人注目,二來實在多此一舉”,信哉斯言。
思來想去,能效法主人公的只有兩條:一是欣賞萬里無雲的晴空,二是躺在公園草坪上喝啤酒。非我自吹,我對萬里晴空的鑒賞和描寫絕對不在小說主人公或村上君之下。啤酒雖然喝不過他(他喝了六罐!),但喝啤酒這一行為本身並無差別。
不過,當務之急是必須把《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的最後幾頁校完,兩個半小時差不多。再往下,作為補償我想領老婆孩子外出旅遊。問題是21.5個小時能去哪裡呢?去義大利吃意式番茄炒飯倒是不賴……
故鄉中的“異鄉人”
一年一度的高考又快到了。不用說,考上北大、清華是許多考生的夢:北大夢、清華夢。而我前不久去了北大,去了清華。當然不是在夢中——我早已過了做夢的年齡。
其實,校園未必多麼漂亮,一樣的月季,一樣的垂柳,一樣的草坪和蒲公英。學生也是隨處可見的男孩女孩,一樣的衣著,一樣的步履,一樣的笑聲。既沒多生一隻眼睛,又沒增加半個腦門兒。但細看之下,眼神或許略有不同。如未名湖,沉靜,而又不失靈動;清澈,卻又不時掠過孤獨的陰影。於是,應邀前來演講的我首先從孤獨講起。李白的孤獨:“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杜甫的孤獨:“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辛棄疾的孤獨:“把吳鉤看了,欄桿拍遍,無人會,登臨意。”魯迅的孤獨:“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陳寅恪的孤獨:“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以及當代人、當代作家莫言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后的孤獨:“我看到那個得獎人身上落滿了花朵,也被擲上了石塊、潑上了污水。”
當然,作為日本文學教授和村上作品譯者,我講得多的還是村上春樹的孤獨:“不錯,人人都是孤獨的。但不能因為孤獨而切斷同眾人的聯繫,徹底把自己孤立起來,而應該深深挖洞。只要一個勁兒往下深挖,就會在某處同別人連在一起。”一句話,孤獨是聯繫的紐帶。為此必須深深挖洞。而我的北大清華之行,未嘗不可以說是“挖洞”之旅,“挖洞”作業。換言之,挖洞挖到一定程度,孤獨便不復存在,甚至得到升華。用北大一位女生的話說:“因孤獨而清醒,因孤獨而聚集力量,因孤獨而產生智慧。”
最後經久不息的掌聲也說明“挖洞”獲得了成功。說實話,清華大學西階報告廳里的掌聲是我歷次演講中持續時間最長的掌聲。如果我是歌手,勢必加唱一首;如果我是鋼琴家,肯定加彈一曲。在這點上,我非常羨慕北大清華的老師同行——儘管他們的收入未必有多麼高——因為這裡匯聚了全國眾多極為優秀的青年。毫無疑問,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是每一個教師最大的渴望和快慰。不過總的說來,我也還是幸運的。至少,在這裡講孤獨的我,實際上一點兒也不孤獨——孤獨這條紐帶把我和北大清華學子連在了一起。
演講完后,正趕上五一小長假,我就從北京直接回到鄉下老家。今年東北氣溫回升得快。去年五一我回來的時候,到處一片荒涼,而今年已經滿目新綠了。鄰院幾株一人多高的李子樹、櫻桃樹正在開花。未葉先花,開得密密麻麻,白白嫩嫩,雪人似的排列在木籬的另一側。自家院內去年移栽的海棠也見花了。一朵朵,一簇簇,有的含苞欲放,有的整個綻開。白色,粉色,或白里透粉,或粉里透白。潔凈,洗鍊,矜持,卻又顧盼生輝,楚楚動人。難怪古人謂“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還有,同是去年移栽的一棵山梨樹也開花了,只開一簇。數數,有四五朵。白色,純白。白得那麼溫潤,那麼高潔,那麼嬌貴。為什麼只開一簇呢?而且開在樹的正中,開在嫩葉初生的枝條頂端。“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古人對花、對梨花之美的感悟和表達真是細膩入微,出神入化。
弟弟妹妹們來了,來見我這個大哥。多少沾親帶故的鄉親們也來了,來見我這個遠方遊子。大半年沒見了,見了當然高興。聊天,吃飯,喝酒,抽煙,聊天。一人問我北大清華演講有什麼收穫。於是我講起那裡的男孩女孩對我講的內容多麼感興趣,反響多麼熱烈,多麼讓我感動……講著講著,我陡然發現他們完全心不在焉。怎麼回事呢?不是問我有什麼收穫嗎?一個妹妹開口了:“大哥,人家問你收穫多少鈔票,你看你……”
接下去,他們索性把我晾在一邊,開始談麻將,誰誰贏了多少,某某輸了多少,誰誰腦梗後腦袋轉動不靈輸了四五千,某某輸了又不認賬結果不歡而散……忽然,我湧起一股孤獨感。我悄然離席,獨自面對海棠花、面對蒲公英久久注視……
或許還是村上春樹說的對:“無論置身何處,我們的某一部分都是異鄉人(stranger)”。是的,我有可能正在成為之於故鄉的“異鄉人”,成為親人中的孤獨者。抑或,故鄉的某一部分正在化為“異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