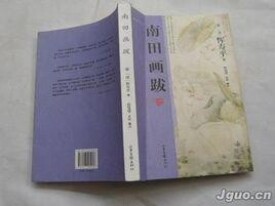南田畫跋
南田畫跋
《南田畫跋》是一部繪畫論著,又名《甌香館畫跋》,因是格題跋輯成之作,難成完整的體系,但仍能窺見其頗富創造精神的繪畫思想。由於惲格徠的父兄是忠於明朝的抗清義土,惲格也立志不應科舉,他對繪畫創作不似古人那樣只主張寄託高雅之情,而取“攝情”說,寄寓民族感情,但由於生活在清初的高壓時期,所說 入未免隱晦。他對畫中逸格最為推崇,研討亦多,在前人論“逸”的基礎上另有創穫。關於繪畫的風格,他最推荒寒幽淡一類,並有頗多論述。總之,惲格不僅以徐崇嗣的沒骨法為宗,創常州畫派,他的畫論對清初及其後的畫壇也有相當影響。
惲格(1633——1690年)字壽平,后以字行,改字正叔,號南田,別號雲溪外史、東園草衣、白雲外史等。武進(今屬江蘇)人。兼工詩、書、圓,時稱“三絕”。家貧,不應科舉,賣畫為生。初工山水,與王翠交往後自度不及,轉作花鳥,水墨淡彩,清潤明麗,自成一家,而山水亦得元人冷澹幽雋之致。後人將其與王時敏、王鑒、王暈、王原祁、吳歷合稱“清六家”。有詩文《甌香館集》。
徠“攝情”是惲格論畫的核心。他說:“筆墨本無情,不可使運筆墨者無情。作畫在攝情,不可使鑒畫者不生情。”他將“情”溝通創作者與鑒賞者的兩方面,堪稱繪畫領域中“,主情”論的代表。由於“攝情”,情充沛而移注於物,故在他看來,物亦含情,故人當以情寫之:“春山如笑,夏山如怒,秋山如妝,冬山如睡。四山之意,山不能言,人能言之。秋令人悲,又能令人思,寫秋者必得可悲可思之意,而後能寫之,不然不若聽寒蟬與蟋蟀鳴也。”處在清初文網嚴酷、政治高壓的情況下,他既以仲長統《昌言》所說的“清如水碧,潔如霜露。輕賤世俗,獨立高步”明志,稱“余謂畫亦當時作此想”,讚美“喬阿古干”的“昂霄之姿,含霜傲風,挺立不懼,可以況君子”;自雲“雪霽后,寫得天寒木落,石齒出輪,以贈賞音,聊志我輩浩蕩堅潔”。又難以壓抑地直言:“寫此雲山綿邈,代致相思,筆端絲絲,皆清淚也。”可以認為,惲格繼承了宋遺民鄭思肖以墨蘭寄寓情志的傳統,其“攝情”說與朱耷的寄託亡國之痛是同中有異。當然,“情”的範圍可不拘於此,較之“四王”的主於摹仿古人,惲格的“攝情”說接觸到文藝創作的真正動力,無疑更值得肯定。
惲格對繪畫的風格探討頗多,而偏嗜逸格與幽寂荒寒之境。如下跋語可看作他的理論總綱:“不落畦徑,謂之士氣。不入時趨,謂之逸格”,“稱其筆墨,則以逸宕為上。咀其風味,則以幽澹為工。雖離方遁圓,而極妍盡態。”他認為“高逸”就是“脫盡縱橫習氣,.澹然天真”,在創作中,“以瀟灑之筆,發蒼渾之氣,游趣天真,復追茂古,斯為得意”,“瀟散歷落,荒荒寂寂。有此山川,無此筆墨。運斥非巧,規矩獨拙。非曰讓能,聊行吾逸”。關於風格,他推崇簡貴,尤其稱道倪瓚的天真澹簡,“一木一石,自有千岩萬壑之趣”。繼而又崇尚荒寒幽寂,曾云:“風雨江干,隨筆零亂,飄緲天倪,往往於此中出沒。”稱道“凄寒將別,筆筆俱有寒鴉暮色外,對老樹荒溪、危崖瀑泉、半壑松風、一灘流水等景色最為欣賞,尤對倪瓚的幽澹、黃公望的荒率傾心不已。既屢贊元人幽秀之筆,幽亭秀木,又雲“寂寞無可奈何之境,最宜人想,亟宜著筆”。可以認為,惲格不將郭熙的調和“君親之心”與“林泉之志”引為- 同道,而極推逸格和荒寒幽寂之境,以元人為榜樣,是與他的經歷、思想、所處時代有關,誠如他所讚歎的元人繪畫“其品若天際冥鴻”,“非大地歡樂場中,可得而擬議者也”,實關係著他作為明遺民的情懷。
有《畫論叢刊》、《美術叢書》本,及民國五年(1916年)保粹堂據光緒中翠琅玕館版重編印的《藝術叢書》本,又有嘉慶時張海鵬輯《借月山房匯鈔》本、道光時陳璜校刊的《澤古齋重鈔》本、《叢書集成初編》等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