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文學
1978年推出的文學體制
中國自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便開始了自上而下的全國性經濟體制改革。與此同時,許多作家開始把創作目光由歷史拉到現實,一邊關注著現實中的改革發展,一邊在文學中發表自己關於祖國發展的種種思考和設想。這就是風騷一時的“改革文學”,其開篇之作,是蔣子龍的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改革文學也可以理解為改革開放時期特有的文學。
改革文學在它的發展初期,側重揭示舊體制的種種弊端,強調改革的歷史必然性。感應著時代的節奏,改革的每一步進展都在文學中得到了及時的反映。叱吒風雲、大刀闊斧地“開拓者”與保守勢力的尖銳衝突,構成了這一時期改革文學作品的基本框架。隨著改革的深化,作家們反映改革的視野更加闊大、眼光也日益深入;在反映社會政治經濟變革的同時,作品更注重剖析在改革中日益顯露出來的國民身上的落後的文化因襲,表現改革對人的傳統價值尺度的衝擊,揭示商品經濟衝擊下舊有生活方式的逐漸瓦解,以及所有這些在人的心靈上產生的強烈震動。這既是改革文學的深化、也是文學使自己不再附庸於政治的一種努力。張潔的《沉重的翅膀》,賈平凹的《臘月·正月》、《浮躁》,蔣子龍的《開拓者》,路遙的《平凡的世界》等是改革文學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在這期間,農村改革小說的代表作如:高曉聲的“陳奐生系列”、何士光的短篇小說《鄉場上》、張一弓的短篇小說《黑娃照像》、張煒的中篇小說《秋天的憤怒》、蔣子龍的中篇小說《燕趙悲歌》、賈平凹的中篇小說《臘月.正月》、《雞窩窪的人家》等。
如早期出現的短篇小說《鄉場上》(1980,8)講述不再靠借貸度日的農民馮幺爸,終於挺直了彎了多年的脊樑、《黑娃照像》(1981,7)表現有了一定經濟能力的農民對精神地位的追求;其後出現的一些作品則開始展現改革的阻力,如《秋天的憤怒》塑造了儼然一方宗主的農村幹部肖萬昌的形象、《燕趙悲歌》在農民改革家武耕新頭頂上設置了重重關卡;在賈平凹的小說中,改革的阻力則不僅來自於國家政體的一些弊端,農民在幾千年傳統文化的積澱下自身形成的頑固惰性也是阻礙改革的重要原因,如《臘月正月》中描述了鄉儒韓玄子對“致富“后的王才不可理喻的百般刁難--前者與後者從前並無任何矛盾,他之刁難後者表面上看來只是出於對“奸商”發財的不滿與嫉妒,對自己地位受到侵犯的擔憂而已,但實際上則反映出中國長期以來宗法制社會殘留下來的傳統文化心理,在面對新的社會體制時因感受到強烈的衝擊。
所謂“改革文學”,堪稱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座紀念碑。比如“傷痕文學”、“知青文學”、“朦朧詩”、“先鋒文學”等,它或許不是最顯眼的,但它同改革的關係是最直接的。之所以稱其為紀念碑,是因為就文學創作而言,它已成為歷史———使命與野心達成,意義歸於歷史。
1979年前後,得意識形態的長期倚重,文字的分量一直很重(或者叫文學的分量),在那個時候,它意味著能“說話”,它是政治生活中的一員。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敏感的作家們站出來發言了。
以1979年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為先聲,一般文學史上稱之為“改革文學”的寫作拉開了序幕。之後,李國文的《花園街五號》、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張潔《沉重的翅膀》、賈平凹的《雞窩窪人家》,柯雲路的《新星》等小說發表,影視再發力,“改革文學”引起鬨動,自不待言。
“改革文學”的路數基本一致:雖然官僚主義問題很大,但是英明的主人公基本上能克服重重困難,並取得階段性勝利,即使要面臨更大的風雨,也要強調主人公那種打不倒的頑強精神。小說對“勝利”基本上充滿了不屈不撓的熱情。這與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社會情緒,基本吻合。
應前文所說,文學也充當了判斷責任的角色,它認定官僚主義應該對社會挫敗負上主要責任,它熱烈擁護行政資源的再分配。當然,也可以理解,狂喜與謹慎是政策解凍下的本能反應。
“改革文學”在創作手法上,無疑也受這種基本判斷的左右,仍然是大眾文學的路子,比如打造喬廠長、李向南等典型人物時,注意插科打諢,並突出了他們的英明果斷,處理不合作、搗蛋人士時,仍然有臉譜化的毛病。他們小心地不脫離群眾,謹守“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訓令,有選擇地批判過去。由整體用詞布局來看,“改革文學”的寫作者仍然偏愛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有些文史家稱之為現實主義創作手法。
應該說,“改革文學”,其思維方式是陳舊的,但其所含的“希望”是新鮮大膽的,儘管這種希望仍然由樂觀歷史進化論所催生,但它至少表明了與過去決裂的勇氣與決心,它能安慰那些劫後餘生的心靈,它對官僚制度的批判也不無道理,它為打破體制僵局營造了強大而積極的輿論。“改革文學”的作者與過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但他們仍然當得起勇士的稱號。
三十年過去了,中國的體制改革仍舊需要探索,但最起碼,它已不再需要由文學來引路或突圍。情緒讓步、理性登場———這對社會文明的進程來講,無疑是一種進步。
改革文學的尷尬之一表現在如何塑造人物方面。既然是弘揚主旋律的主流文學,就必須遵守一條“潛規則”:作品要歌頌的主要人物不能有所閃失。所以《大風起兮》中的幾位主要人物都是一身正氣、兩袖清風,不僅沒有腐敗行為,在人格、道德方面幾乎也沒有任何可挑剔之處。連在文革之前就已赴港、后又回鄉創業的工業區副老總楊飛翔,也不僅一改過去的金錢觀,在經濟的大潮中穩守自己的節操,而且連好追逐女人的毛病也改掉了,對一位風流女子阿笑(在楊之前已和多位男士有過關係)一往情深起來。這又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改革開放所帶來的人們在金錢、情慾方面的道德滑坡是人所共知的,何以這個開發區的人們個個如聖人般不受污染?二十世紀之末,還在中國的一部長篇小說中出現這種“高大全”群像。

蔣子龍
單憑作家個人的主觀努力是無法做到的。因為此類文學既然不願離開主旋律,就必須有明確的政治規範,因而必須在特定的思想框架內進行構思和語言運作,作者唯一可靈活處理的地方只是書寫策略問題。《大風起兮》的策略性清晰可見,作者在策略選擇的過程中已經儘力留下了可供“真實”棲身的語言空間,但最終不盡如人意,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正如書中多次寫道“大風起於青萍之末”,作者意欲向讀者展現一幅波瀾壯闊、高昂宏偉的改革交響詩,並為此做了所能做的巨大努力(筆者身在廣東,對陳國凱先生艱苦寫作的事迹有所耳聞,也至為敬佩),但畢竟大風何以“起”、又何以“變”而為席捲一切的颶風之內在動因,作者多次欲言又止。這是不能全怪作家的,最終有賴於外部書寫環境,尤其是政治環境的進一步改善。
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改革中的個體人物也許或多或少存在著精神和人格的缺陷,但改革的二十多年實踐已經給中國帶來巨大變化,總體成就是難以估量的。廣東作家敢於在複雜的外部環境中,抒寫當代改革的大文章(如陳國凱的《大風起兮》,呂雷、趙洪的《大江沉重》),即使存在著不盡人意之處,但也顯示了某種勇氣和文學理想,這是廣東這片改革的熱土向本土作家們提出的要求。這較之許多內地作家根本不寫當代生活,而紛紛去挖掘那些封建時代或民國時期的墳墓里的殭屍,並不見得就低人一等,從而又低文一等。
在紀念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日子裡,讀潘強恩先生的長篇小說《大潮》,別有一番感慨。這是一部厚重而具有親歷性的作品。作者通過描述新豐村農民自發探索股份制的故事,表現了改革開放時代中國農民的精神風貌。作者曾是在改革的風口浪尖上的農村黨支部書記,自己就是小說主人公的原型。可以說,這部小說具有自傳體的色彩,當然小說並沒有拘泥於自傳,而是描寫中國農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歷史進程中所扮演的歷史角色。

改革文學--《花園街五號》
很顯然,這部作品與中國改革文學一脈相承。改革文學發展到一個重要階段,以長篇小說《新星》為標誌。李向南的形象帶有濃厚的理想化色彩。他的改革模式與現實的真實有相當大的距離。隨著改革的深入發展,我們越來越認識到李向南模式的虛幻性、不可操作性,甚至與歷史進程完全不同。我們不能對作家求全責備,當時的實踐只能向作家提供這樣的認識。讀《大潮》,我們發現這種虛幻不可操作的色彩已經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真實的可信和可操作的模式。我們知道,《大潮》中的姬振盛模式,有著曾引起改革者關注的“萬豐模式”的堅實基礎。“萬豐模式”當年曾引發了姓“資”姓“社”的大討論,現在則可以看做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勇敢探索——股份制在今天已被普遍採用。我們願意說《大潮》也是中國改革文學的一次深化開拓。
在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進程中,廣大文學工作者先後創作出一大批反映改革開放火熱生活的文學作品,以文學的形式記錄下近三十年中國社會所發生的深刻變革,許多作品在廣大讀者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產生了強烈的社會影響。
在這期間,農村改革小說的代表作如:高曉聲的'陳奐生系列'、何士光的短篇小說《鄉場上》、張一弓的短篇小說《黑娃照像》、張煒的中篇小說《秋天的憤怒》、蔣子龍的中篇小說《燕趙悲歌》、賈平凹的中篇小說《臘月.正月》、《雞窩窪的人家》等。
縱觀農村題材的改革小說,可以發現初期作品往往是簡單的'一片光明',隨後一些作家開始致力於揭示農村改革中所受阻力並剖析其產生的原因,一些優秀之作甚至觸及到在改革中發生變異的中國農民的'傳統文化心理'層面。這一過程,是不斷深化的。
如早期出現的短篇小說《鄉場上》(1980,8)講述不再靠借貸度日的農民馮幺爸,終於挺直了彎了多年的脊樑、《黑娃照像》(1981,7)表現有了一定經濟能力的農民對精神地位的追求;其後出現的一些作品則開始展現改革的阻力,如《秋天的憤怒》塑造了儼然一方宗主的農村幹部肖萬昌的形象、《燕趙悲歌》在農民改革家武耕新頭頂上設置了重重關卡;在賈平凹的小說中,改革的阻力則不僅來自於國家政體的一些弊端,農民在幾千年傳統文化的積澱下自身形成的頑固惰性也是阻礙改革的重要原因,如《臘月?正月》中描述了鄉儒韓玄子對'致富'后的王才不可理喻的百般刁難--前者與後者從前並無任何矛盾,他之刁難後者表面上看來只是出於對'奸商'發財的不滿與嫉妒,對自己地位受到侵犯的擔憂而已,但實際上則反映出中國長期以來宗法制社會殘留下來的傳統文化心理,在面對新的社會體制時因感受到強烈的衝擊
相對於農村來說,城市的改革更加繁雜艱難,因而作家們反映城市改革的小說作品也更為多樣、深刻。城市題材的改革小說涉及的領域上至國家的要害行政部門,下至街道小廠、普通人的內心世界,反映出作家對社會、時代的廣泛思索。
在這類作品中,張潔的《沉重的翅膀》、張賢亮的《男人的風格》、李國文的《花園街五號》等都較為優秀。其中柯雲路的長篇小說《新星》反響最大。這部小說以明朗的語言風格,描寫三十二歲的李向南受命到古陵縣擔任縣委書記后,採取的種種雷厲風行的改革手段及因此與反對派間產生的種種矛盾糾葛。小說主體上採用了現實主義創作手法,但作品中的主人公身上帶有明顯的英雄主義色彩。在小說結尾,當李向南在副書記顧榮千方百計的阻撓中陷入困境時,作者安排他到北京尋求幫助,這個開放式的結局給讀者留下許多聯想的餘地,也使李向南的改革避免直接陷入絕望,從而給小說增添了一點亮色。顯然,這部作品延續著傳統的革命浪漫主義的創作風格,而這種明朗的色調,的確給作品增添了極大的可讀性,由該作改編同名的電視連續劇因此在1984年創下了全國最高的收視率。
在關注城市改革題材的作家中,蔣子龍因其在獨特的經歷而創作出大量傑出的作品,從其作品的發展變化上看,他的創作可以說涵蓋了整個改革文學思潮的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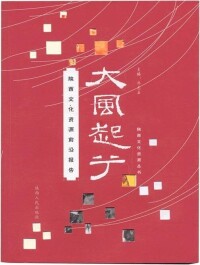
改革文學--《大風起兮》

改革文學--《大潮》
這是一部帶有調侃性質的中篇小說,陸文夫用詼諧幽默的語言,描寫了一個近乎鬧劇的故事,然而這個鬧劇卻又具有可悲的真實性:在現實生活中,“穩妥”確實“往往是緩慢的同義語”,而像馬而立這樣因工作中的幹練與麻利被視為毛毛燥燥、辦事不穩的人又何在少數?人們的精神被異化,人們心目中判斷事物的價值尺度已經顛倒。陸文夫說過:“我造牆的目的在於拆牆;造一堵有形的牆,拆一堵無形的牆,即拆掉那些緊緊困住我們的陳規陋習和那奧秘無窮的推拉扯皮。若干年來,我覺得到處都會碰上這堵無形的牆,弄得人一籌莫展,啼笑皆非。”在這篇小說中陸文夫就是試圖以嘲諷的方式,揭示現實生活中已經被人們習以為常的一些弊端,如臃腫機構中的慢性綜合症、誇誇其談的惡習、以貌取人的世俗偏見、無功請賞的鄙俗心理,并力圖根除它們。可以說陸文夫的改革矛頭是指向人們的社會文化心理層面的,與僅僅描寫保守阻力的改革作品相比,他的思索顯然要深入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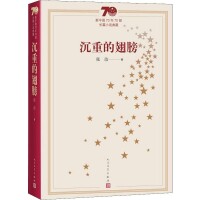
改革文學--《沉重的翅膀》
在這篇小說中,改革主要阻力已經不再來自傳統的保守派,而是同樣積極參加這場改革的新人物們,因從不同角度考慮利益問題而產生了種種矛盾。這裡已經很難簡單地判別善與惡、正義與卑下,而只能在紛繁的快節奏中,見出人們複雜多樣的思考與心態。
另外,陸天明發表於九十年代的長篇小說《蒼天在上》也是一部反映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作品,小說因被改編成電視連續劇而在全國產生很大影響,這一方面說明“反腐倡廉”口號的深入民心,另一方面也證明高科技媒體在當下社會的強大魅力。
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改革文學”曾是一個專有名詞,特指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一種文學現象。隨著農村實行聯產計酬、承包責任制,城市開始經濟改革,“改革文學”也應運而生。1983至1984年間,描寫社會改革的作品大量湧現,形成了一個創作高峰,在社會上頗為轟動。
1979年蔣子龍的小說《喬廠長上任記》是“改革文學”的發端,著力塑造了改革家喬光朴的英雄形象,“喬廠長”也成了改革者的代名詞。之後的改革小說中,出現了類似“喬廠長”的“開拓者系列”,如《改革者》(張鍥)、《跋涉者》(焦祖堯)、《禍起蕭牆》(水運憲)、《三千萬》(柯雲路)等等。還有一些作家對種種社會弊端予以批判和揭露,劇作家沙葉新與李守成、姚明德合作的戲劇《假如我是真的》就是這一類的代表。高曉聲的視角比較獨特,他一直關注著普通農民在新時代的變化。他筆下的李順大、陳奐生都是農村的小人物,作者為他們生活上的改善而欣慰,也對他們思想上因襲的落後的東西給予溫情的嘲諷。
1981年底張潔的長篇小說《沉重的翅膀》問世,標誌著“改革文學”進入第二階段。這一階段主要關注改革對整個社會尤其是人的思想、道德、倫理觀念帶來的變化。影響較大的有長篇小說《故土》(蘇叔陽)、《花園街五號》(李國文)、《男人的風格》(張賢亮)、《新星》(柯雲路)及中篇小說《老人倉》(矯健)、《魯班的子孫》(王潤滋)、《秋天的憤怒》(張煒)、《臘月·正月》(賈平凹)等。路遙的中篇小說《人生》以農村青年高加林的悲劇,深刻地寫出了商品經濟對傳統農村文化的衝擊。
1985年以後,“改革文學”在題材、視角上更加多元化,初期的理想主義色彩逐漸淡化,作為一種新思潮、新現象的“改革文學”已經結束。但是,以改革開放為主題的文學作品仍層出不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