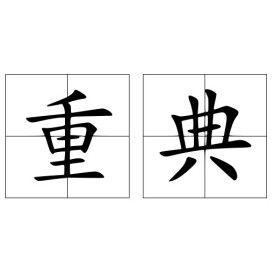重典
重典
徠重典之存,如果排除社會性因素而單獨從研究決策者入手,時常可以發現重典適用的軌跡與君主自身對外部環境的應激及心理狀態的描繪極其相符。傳統社會以降,歷代統治者依賴“以刑為主”的東方本土式法制路徑,而“重典治國”現象在各朝不同時期也備受青睞,似乎成為穩定政治經濟局面,實現長治久安慣用且重要的政治運行和法制工具。故而,由上可以簡單描繪出有關傳統社會重典的輪廓:即一種為實現統治目的服務,依據具體的政治經濟環境和理想化設置而架構的,以統治權治下所有社會群體、機構建築為施用對象,運用刑事法律為主體並結合特殊化制度工具所形成的全社會嚴密、靈活而具備相當彈性的法律制度體系。
1.[cruel torture; severe punishment]:嚴厲的刑律
如治亂國用重典
2.[important classics]:重要的典籍
1、指重法。
《周禮·秋官·大司寇》:“刑亂國用重典。”鄭玄 註:“‘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
明 沈德符 《野獲編·言事·疏語不倫》:“聞慈聖亦玉色不怡,將處重典。”
清 王士禛 《池北偶談·談故二·柳條邊》:“有私越者置重典,名柳條邊。”
梁啟超 《民約論》:“巴黎 議會命毀其書,且將拘而置諸重典。”
郭沫若 《中國史稿》第五編第一章第一節:“弛禁派則認為靠嚴刑重典不能禁止鴉片。”參見“重法”。
2、指重要典籍。
唐 李百葯 《賦》詩:“重典開環堵,至道軼金籝。”
“亂世用重典”,“亂世”是指中國古時各朝代社會出現凌亂及差劣局面的情況,與“盛世”相反;“重典”是指嚴苛的懲罰。全句指,為了整頓好社會上凌亂的局面,迫不得已唯有使用嚴苛的懲罰。而整體上,“亂世用重典”用於社會上的定義為,透過嚴苛的法律效果懲罰犯罪,來達到治理社會的目的。
基於應報思想,任何有同理心的人,對於犯罪者造成受害者和受害者的親人的傷害有所體會。當傷害是如此深刻難以磨滅時,為什麼反而對犯罪者如此寬大,難道不該給這些犯罪者應得的懲罰?
當 社會情勢混亂的時候,採用較重的刑罰比較容易達到威嚇的效果,進而降低犯罪的比率以實現穩定重建社會秩序的目的的。
從 技術層面:亂世用重典,強調透過威嚇的法律制度來解決所有社會問題,但是那不是唯一的解決方式而且過度地依賴法律制度,代表一廂情願地認為法律制度不會有缺失、不會有疏誤的可能,當 警察抓錯人、法官誤判、冤獄發生的時候,透過重典只不過是凸顯 政府治理社會的失責,並且使得冤獄變成難以挽回的遺憾。
從政府權利過大的流弊層面:受害者與其家屬固然值得同情,但是重典不是協助他們的合適方式。如果我們期待政府,可以效率地、有力地、明智地抓到真兇,但是給予政府過大權力,往往適得其反,並且反過來箝制人民 思想自由或是透過監控系統侵犯 個人隱私。
重典治國論
傳統社會以降,“重典治國”在各朝不同時期備受統治者青睞,似乎成為穩定政治經濟局面,實現長治久安慣用且重要的政治運行和法制工具。但重典治世在絕大多數的歷史時期往往難以完成統治者的決策預期,收效了了,最終難以逃脫成為歷史陳跡的命運。在認清辨明重典給傳統社會帶來諸多負面影響的同時,不應妄自斷言僅是法典之嚴苛性造成了社會動蕩,阻礙了社會進步的步伐。反之,應當透過制度體表剝離並審視導致重典失效的權力結構、社會文化氛圍、法文化為背景等要素群體,反思而進取,此乃是國人不可偏廢的重要任務。傳統社會以降,歷代統治者依賴“以刑為主”的東方本土式法制路徑,而“重典治國”現象在各朝不同時期也備受青睞,似乎成為穩定政治經濟局面,實現長治久安慣用且重要的政治運行和法制工具。而由中國特有的政治、法制土壤所孕育的“重典論”,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所具備的意蘊是有差別的,對社會的作用力也趨於殊途。剝離紛繁的表象,抽取各式重典背後承載的法文化,“重典論”思潮似乎也並沒有隨著中國法律的現代化更新換代而徹底消褪,卻成為隱性的法制因素,供給著目的論化的思維方式,深刻影響著國人今日的法治進程。故而,在不斷辯證借鑒、汲取中國傳統社會法律思想經驗,兼顧吸納國外優秀法律制度的今天,歸納、總結重典治世所發揮之效用,使之浮於水面,愈加明確化,繼而認清利弊,抽取其中的合理性因素,扶正法治化軌道,乃是國人不可偏廢、僭越的社會工程。
重典治國理論之解構
(一)重典論之源流概要 翻閱中國歷史,即可發現“重典治國”理論擁有厚重的人文底蘊。上古伊始,發端於禮、刑之中國法,在刑始於兵,刑、法並無二致的年代,實則反映著一部古人類社會群落逐步發展壯大的演化史。國家產生后,統治者為建立統治,維持秩序,啟用所謂“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之道:邢之目的即為樹立權威,使“民不敢犯”,“禁奸止過”以確保有條不紊。從人類演進學的角度審視法源於刑之事實,也能窺見人類發展史乃至法律制度發展史的諸多共性。但中國法之流變有其自身的軌跡。重刑亦非萬能,當鑒於史上因濫施刑罰適得其反,遭至民眾反抗而湮滅統治權的事例,統治者蹣跚般學會,應在可控的範圍內掌握權力行使的適當性,提出了以輕刑、仁政為表徵的“以德配天”、“德主刑輔”、“一準乎禮”“禮法合一”的施政方針,緩和了階級矛盾,為國家政治較為安定、經濟得以漸進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上升創造了有利的成長期,達到盛世。但是“約法省刑”之國策並非徹底遊離於重典論設置的框架之外獨立生存。於此相反,由於中央國家的形成從始便依靠著集權化的政府萬能主義,決定了盛世亦當在此框架項下適度發揮而變形、衍化——其始終不能也不願擺脫“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的行為範式,遵守“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之法則。看似重典論在法則中位居下位,然而其在較短時期內針對特定對象或為實現特定目標,從重從快,善於高速營建起“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的初始局面,在穩定秩序方面,擁有毋庸置疑的高效性和合目的性,以至於可作為實施其他後續統治行為的有力保障……這些均是輕、中二典在“運行——收益”坐標系中考察時間佔用、整體行為效率上無法比擬的。是故,重典治世絕非單純僅在“亂國”發生,而有著更廣大的作用空間和運行範疇。
(二)傳統社會重典治國理論之解構 在對重典治國理論進行實踐考察,剝除歷代對重典不一的執行理念或表達方式,尋找其中共性時,實則在明確兩個概念:重典面向的對象群體和“重典”概念本身。其一,重典面向的對象群體。學者指出,古中國所謂法,“一方面就是刑法,另一方面即官僚統治機構的組織法”,簡言之,系由公權力國家行政執法規則和相應治理罰則構成的制度體系。其始終難以超脫“法自君出”、“諸法合體,以刑為主”的模式,生長出如同西方那樣弱化集權條件下獨立完備的私法系統。造成此種局面,原因應當是多方面的,也自然非本文所研究的對象,但必定成為考察重典治世效用時不可或缺的歷史土壤和理論基石。中國法制結構決定了法制之鋒芒為“士制百姓於刑中”:通過對統治者治下的社會下層進行公法為主要形式的法律約束達到治世的目的。但這並不是說,國人不曾受到統治者施加的私法色彩法律準則的控制。自古便存在的“家族法”、民事習慣,為控制國家經濟命脈而推行的官辦、督辦經濟法律制度,經濟發達時期培育的民事法律大量出現,在推翻有學者認為中國“無私法”論斷的同時,確也說明這些法律措施相較刑事公法而言,不太能淋漓盡致的展現古中國法的特點。故而,“夫法,所以興功懼暴也”的“典民”結論即定,統治者所關注的刑控社會下層對象,自然為廣大的底層人民,以及為其所用的龐大行政官員機構、被皇權所棄不予保護的貴族群體等(在本文考察中可視為微量化特殊對象),而對最為底部百姓的操控,很多時候是在對官員的選拔和任用過程中完成的。易言之,高位統治集團以法治官,打造較為高效的官僚結構便能實現統治目的。若假設統治者單純要求重典在適用於底部群體時達到“禁暴止奸”之效果,而由於官僚實質上也應歸屬於統治集團,便在適用法律時會產生與適於民眾有別的效果,則對重刑結果的追求也會不再純粹。其二,重典之界定。傳統社會末期,統治者對封建法度的意義作有如下總結:“國家刑罰禁令之設,所以詰奸除暴,懲貪黜邪,以端風俗,以肅官方者也”。而其中“禁奸止過,莫若重刑”,可達到“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之功效。似乎重典所傳達出的意味僅停留於嚴刑峻法、用刑苛重,能夠從刑種的嚴酷和刑度的不著邊際來體會。實際上,要準確給“重典”下一個定義,應當首先建構於整個法律體系層面,顧及其應當具備的下列特徵:
1) 其體系嚴密,適用領域深廣,並經過歷代不斷修正而得到完善發展。以刑事法為例,不論上古,且從先秦戰國時代之始奴隸制五刑以降,經歷後世各代“輕刑”之改革而達成封建制五刑的確立,再到封建社會中後期部分苛刑的復興及至濫用、重新入律,形成了體制嚴謹、“疏而不漏”的宏觀體系,甚至甚多行政、民事法律責任都會被施以刑罰制裁,如唐律中有“凡負債違契不償,一匹以上,違二十日笞二十”的規文。後世欲了解各代法律制度及政治經濟環境,大致也可從所立刑罰和具體規文中窺視一二。
徠2) 其成文法範式呈現嚴苛性,同時存在大量特別“法”細胞,具有較大的靈活性和彈性。奴隸制五刑之嚴苛被逐步改良而更新為封建制五刑,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許多人類蠻荒時代具有的同態復仇、肉刑充斥的現象,代之以較為文明的刑罰,無疑具有歷史進步意義。但其中依舊保留了“罪人以族”、充軍、刺字、枷號等罪,明清時代更以凌遲入律,彰顯了傳統重典的嚴酷性特徵。同時,肉刑殘餘在一定時期以鎮壓、整肅、爭權為目的被濫用而肆虐興盛,但往往不存在成文的法律依據,被歸為法外酷刑。但因注意到法自君出,大體也可將其視作某種意味上的特別“法”,只是缺失了常規法律制度所應具備的穩定性和可預測性,被賦以較大的伸縮性和隨意性補充了重典實施的威力。其彈性還表現為,存在大量同罪異罰的情形構成重典體系中較為重要而特殊化的組成環節:按受罰主體待遇的迥異程度可將此環節作一二分:一方面被免除部分乃至全部的法律義務,諸如贖刑之適用;另一方面則可能承擔重於律文規定的刑罰,抑或被施以特別“法”所定的極端刑罰。
3) 其類型繁複,具有強烈的合君權目的性,決定在不同歷史時期分具不同的內涵,並伴有些許理想主義色彩。依據制定和運行重典的統治需要不同,區別出即如學者歸納的幾種模式:極端重典主義、重重輕輕主義、相對弱化重典主義及其他特殊化重典主義。極端重典主義以秦朝刑法為典型,以繁於秋荼而著名於史。重重輕輕主義以北宋中期頒行重法地法和“盜賊重法”、明代相較漢唐法制的“重其重法、輕其輕法”的刑法特點為代表。相對弱化主義則以主張“約法省刑”為代表,刑罰中正,多出現於國家初創或社會經濟遭受重大破壞,需要長久時期休養生息之時。至於特殊化的重典推行,不宜歸納為上述任何一列,多是統治者為達到某種目的、由個人好惡及注意力之轉移而發生,諸如明太祖時期頒行《大誥》、重典治吏,便具有強烈的政治整肅目的。同時,統治者通過施用重典欲達到社會秩序長治久安,萬世為君的目的在史上不乏個別,懲治奸黨、屠戮權臣,往往滲透了許多道德衍生的理想主義情調,而大多卻事與願違,此留待後文詳述。故而,由上可以簡單描繪出有關傳統社會重典的輪廓:即一種為實現統治目的服務,依據具體的政治經濟環境和理想化設置而架構的,以統治權治下所有社會群體、機構建築為施用對象,運用刑事法律為主體並結合特殊化制度工具所形成的全社會嚴密、靈活而具備相當彈性的法律制度體系。
重典治國理論之效用考察與合理性分析
(一)重典論之效用考察 本文給出的重典論之意義界定系以整個傳統社會法制結構的發展承繼為背景,就某個歷史時代為考量目標,由於統治者對重典的理解正如上文中學者給出的諸多分類方式那般所異,其欲施用達成的目的也有不同,從而在後世對重典論的績效考察過程中,需要略作抽樣區別。從較為狹隘的範疇入手,中國傳統社會傳承的人治氛圍里,歷來將開明專制主義奉為經典興國政策,重典適用也自是以較為低級化的工具姿態非獨立性存在於此制度土壤之中。故而,欲對重典制度的績效得出相較合理與理性的結論,必須首先區分出較為適合開明專制統治生長的政治經濟條件。作為既成事實,今日對重典的分類方式便在社會形態的選取中比作相應參照系。亦由此,上述分類中較為明顯的,如同有秦一代等典型的極端重刑主義在考量該理論效用時,予以參照似屬不妥。其次,相對弱化重典主義以使國家休養生息為立足點,多為修復脆弱的自然經濟而設立。統治者總結歷史,普遍考慮到暴刑荼重致使民眾反抗、社會動蕩,給統治帶來的毀滅性打擊后適度反省,能夠識知“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此環境中,重典用為上層建築,由其本身性質與較為脆弱的社會資源條件相左,決定了其不宜作為長久制度存在。於是乎當約法恤刑,弱化對廣大民眾適用的重典因素。此種政策多發於封建國家權力初創但保有較強的統治力,抑或公權力所能調配的社會資源數量尚處於上升趨勢中的時期,經濟政治制度本身還具有較強的生命力,通過法制變革易於釋放被前不合理桎梏所封閉的發展動力。此種重典制度的推行,一方面使得民生得以穩定,有利於社會生產的發展;另一方面易導致在重典治理對象中,可能對官僚群體的監控力度鬆散不足而日益滋生並加速此群體的潰爛。在此也應說明的是,在傳統社會中盛行的諸如“八議”、官當、請、減、贖、免等制度,並非統歸於相對弱化主義,正如上文所提及,是重典制中較特殊的同罪異罰環節的組成部分,它具有對重典制度的較強“離心力”,但囿於皇權權威的維護始終未能遊離,但確對重典所達之效用有抵銷之反作用。這樣一來,衡量重典治世績效較為上佳的樣本,即剩下區分對象的重重輕輕主義和特殊化重典主義。重重輕輕主義重典模式有著縱橫二向有別的不同意域:從縱向而言,以規範性法律文件傳承的角度,指出後世重典較前期規文在適用對象和程度上的區別,這是歷史差異的顯示,如有明一代較唐律所作出的改進;從橫向而言,是對當期使用法制時對象和程度的差別性規定。易言之,即同罪異罰環節中擴大受動主體承擔義務的可能性部分,即如宋代“盜賊重法”“重法地法”之推行。傳統社會篤信“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北宋時期,由於立國未經過大規模的土地兼并改革、外患深重、加強中央集權而形成的冗官弊政等因素,客觀上塑造了一個階級對立相對嚴重的時代,以至於統治中期便較早的開始顯現危機,盜賊之患即是表徵之一。對此,由北宋仁宗嘉佑6年始歷經英宗、神宗、哲宗三代以惡治惡、加重打擊賊盜力度而擴大施用的重法地法、盜賊重法等,依據今日傳世的大料史料,似乎其從未能有效發揮統治者預期的治理效果。不但如此,還引發了更為嚴重的社會混亂。如熙寧十年(1077年)二月,“京東、河北盜賊不禁,至白晝殺人於市,攻略鎮邑,執縛官吏”;元豐年間(1078-1085年),李常知齊州,“齊多盜,論報無虛日”,在其治下,“盜賊遂清”。而到哲宗末年(1086-1100年),齊地“群盜晝掠塗巷”……即便在京都附近,“盜賊充斥,劫掠公行”,作為執法主體的軍隊、官員多是“勢力怯弱,與賊不敵”,“縱能告捕入官,其餘徒黨輒行仇報,極肆慘毒,不可勝言”。特殊化重典模式之特異,在於其非但不能彰顯統治者所謂“審慎刑罰”,也不是出於如同北宋王朝那樣嚴酷的統治環境,導致統治集團“被迫”推行嚴酷的法度,整肅社會秩序——決策者在主客觀方面都未遭遇“窘境”。客觀上,其時常處於較為安定的統治時期,甚至萬象更新、盛世之狀初見端倪;主觀上,決策的制定並非外部因素推動的應激反應,而很大程度上是己身深思熟慮的結果。更確切地說,是依照自己的人格信仰和對自己利益的檢討。此種模式時常被篩選出的例子,即明太祖重典制貪之幾十年風雲歷程。親歷社會底層疾苦的明太祖,對元末官員貪瀆、政治腐敗而遭滅亡感觸頗深,故嚴厲法度,重典治貪,對封建官吏的嚴罰可稱空前絕後。最為重要的是,其空前的完成了將久已存在的、體現各代統治者嚴苛色彩的法外酷刑即特別“法”因素轉換為真正意義的制定法模式,使傳統社會的重典體制更加完備化,儘管這些成文法實際發生效力的時間極為短暫。但應看到,終洪武之世,其也未能助太祖達成事先所勾勒的清明政治的目標。凡舉一例即可:洪武十八年,吏部考核全國布政司及府、州、縣來京朝謁官員幾千,其中所謂稱職者僅435人。對此太祖晚年也認識道:“我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至成祖永樂初年廢建文仁政而沿用《大誥》收效不佳后束之高閣,《大誥》之刑漸漸棄用后數載,貪官污吏已遍布內外,顯示了掙脫重典之束縛后強勁的反彈力。
(二)適用重典之合理性分析 由上,傳統社會無論何種重典治世模式,收效均屬了了,呈現整體低效甚至無正效用但卻有長久活力的奇怪姿態。對此進行合理性解釋的角度可有多個,但欲以單向的、法律制度模型的路徑為切入點,應把握法文化、制度建構與發展史及其客觀運行評價作為突破關鍵。首先,重典發揮的階段性正效益對維護統治具有強吸引力,統治者可將其作為改變行使統治權不利局面,尋求優化時的博弈行為。中國古來之重典是成系統的,規範嚴密,且表現為某種封閉性的獨立發展結構,立法和策略之行具有強烈的路徑依賴特徵。同時中國自古而來較西方強烈甚多的集權型治理模式,也能將資源集中到足以確保由上而下執行某種制度初始階段所要求的嚴格性,甚至嚴苛、殘暴性。故而,重典推行在短期時間確實可如史料所描述的那樣“彰善癉惡,激濁揚清”。雖然只是違法者受到重懲造成社會相關主體感到自危后,所受規制的社會反常暫時停滯甚至隱蔽的反應。然重典的最初作用力越強,其受用波及越廣,影響便越深,停滯癥狀維持時間便較長久,雖然不乏孕育著更劇烈反彈的可能。但這不能不給統治者以想象的空間,繼續預期所深惡痛絕的受動主體自覺進行良性轉變,以至設想能秉承重法之效,最終消弭不安定因素,“以刑去刑”,長治久安。而在傳統社會後期,隨著商品經濟的高度發達,社會呈現多元化趨勢和統治者所欲維護的簡單生產基礎下社會治理手段產生衝突,更凸現了無法與時俱進的一般法典修正補充技術的落後地位。為擺脫此種不利局面,採用有別於一般法制制約力的重典,不能不說體現了封建社會後期統治者被迫放手一搏的無奈。其次,適用重典是統治者認可的,永葆國家機器運轉動力所必需賦加的“托賓稅”。在傳統社會這架巨型機器運轉二千餘年的過程中,官吏始終作為統治者實現統治效能,控制普通民眾不可缺失的組成利器。官吏集團與最高統治者之間本質上存在的是一種特殊雇傭關係:因為高度集權社會中權力之行使,實際亦是建立在地方權力為中央權力直接控制,卻也過分集中的情況下。故各級官僚機構在中央之下扮演的角色,即為僱員也為在局部受制的大領主,系一種具有人格化的工具。故“國家之敗,由官邪也”是古人對官之於國重要性的認識,於是堅守不放“治國莫大於懲貪”、“治天下首在懲貪治吏”之圭臬。時時用重法剔除國家機器中不合理因素,整肅行政紀律,即如在宏觀經濟運行過程中經濟學家所言為齒輪良好運轉而不時放入細沙般效果的課稅雷同,治理官員腐敗懈怠而致階級矛盾過分擴大化,促進行政效能的提升、實現社會秩序的穩定和生產的發展。再次,適用重典反映了傳統社會“禮法合一”條件下泛道德化的“和諧”行為預期。兩漢以降,法律道德化色彩逐步加強,隆禮重法成為中華法系一大特色。引禮入法,一方面為統治者鼓吹“惟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宣揚仁政和統治地位合法性提供理論支撐;另一方面,善用禮中豐富的道德規範培育發達的家法族規,使社會形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金字塔狀結構,也有利於減輕維護統治所需耗費的成本,“禮樂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藥石”,惟“以德化天下”,“明刑制以齊之”,國家可長久矣。應該說,決策者乃至國民均在一定程度上採納並預設了人性向善的儒學基點,努力以道德化行為範式來改造既定的不合理因子,其中一方通過隆禮以導民向善,減少不必要的統治開支;另一方則企盼上為政以德、匡扶正義——權力義務極不對稱兩方群體在社會構建中共享著基於不同認識形成的“和諧”雛形表徵之嚮往。但由於傳統社會局限性,社會矛盾無法消解,人們註定長久面對大同理想和嚴酷現實之衝突。於是乎統治者每每“痛下決心”,對人性論稍作一修正,試圖以滅除惡之人性的剛猛之法以惡治惡,樹立權威,瓦解法制運行不暢的阻礙;國民也時常希冀青天在世,向給自己帶來深重苦難的官僚腐敗集團表達失望和憤慨情緒之時,事實上也早已偏離了人性善之預期,復燃原始復仇主義之觀念,同時卻也清楚意識到民眾分散力量之孤立弱小,被迫對善治之論尚存遐想,有通過接受由上至下的重典洗禮來達到社會革新,重建“和諧”的心理準備和要求。作為傳統社會法文化的標誌之一,尚不能忽略法自君出、權尊於法的事實。重典之存,如果排除社會性因素而單獨從研究決策者入手,時常可以發現重典適用的軌跡與君主自身對外部環境的應激及心理狀態的描繪極其相符。正是統治者“口含天憲”,不受權力約束,決策之合法性歷來沒有適格的評價標準,而合理性則可在決策定立時由下而上反饋得以損益,但依舊無法擺脫深烙有統治者自身對歷史、社會現狀、皇族利益思考和抉擇之泥淖,甚至表達了其對以往自身經歷“辛酸”面的反思或抵觸、逆反情緒,重典的拋出也不外如是。